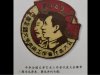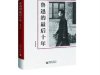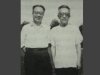很小的時候就讀過魯迅,記得小時候最早讀的是一本連環畫,講的是魯迅的故事。其中一個情節對小孩子來說印象非常深刻。這個情節是說,魯迅在日本學醫的時候,有一次看紀錄片,內容是中國人被砍頭,旁邊有一大群中國人圍觀。連環畫裡的場面,至今我還有印象。魯迅說他受不了國人的麻木和冷血,決定棄醫從文,要喚醒國民,要在黑屋子裡發出自己的聲音。從此以後,中國人麻木、冷血,喜歡看殺人等等,在一個孩子的腦海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又讀到了《狂人日記》,其中一段話成為了經典: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在我年輕的時候,《狂人日記》看過很多遍,它給我的印象是,中國歷史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吃人」的社會,中國人歷來就殘酷,從來就喜歡殘忍,這個觀念開始固定在我的記憶里。加上魯迅的另外一篇小說《藥》,主人公還拿烈士的鮮血蘸著饅頭給兒子吃下去治病,這種印象更加得到強化。通過魯迅的教誨,以及其他的一些言論的傳播,例如對凌遲的渲染等,我當時真的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從治國根本的「仁義道德」到愚昧無知的普通百姓,從來都嗜血,從來都草菅人命,中國人的殘忍似乎已成為徹底的定論。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但是,那時候好像沒想過,自己生於這樣一個社會,是否也天生帶著嗜血的基因?
與這種觀念相對照的,一是西方對中國的落後、野蠻所做的批評,二是國人對西方熱情洋溢的介紹。由此產生另一個關聯的觀念:西方社會是文明的代表,西方不管是制度還是老百姓的日常習慣都比中國先進多了。必須承認,有一段時間我確實是這麼認為的。因為那個時候,我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缺乏全面了解,中國的殘忍是別人告訴我的,外面的文明也是別人告訴我的。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個觀念不太對。比方說,圍觀死亡的熱情和嗜血的心理,並不是中國人的普遍現象。比較而言,歐洲人的這一愛好比中國人強烈得多。
古羅馬的競技場可以容納9萬觀眾,而這些觀眾最大的樂趣就是觀看死亡,甚至還參與死亡的決定。古羅馬競技場裡輪番上演的血腥場面,是整個民族嗜血心理的典型代表。後來我還知道,城市廣場是歐洲文化的特徵,中國古代城市沒有大型廣場,也沒有大型群眾集會的場所,歐洲古代展覽死刑是在廣場上,而中國古代一般是在城牆上。因此,中國古代執行死刑才會採取遊街的方式,而不是群眾集會。廣場集會和遊街相比,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
歐洲中世紀執行死刑和展覽死刑,都有大量的群眾圍觀,其人數遠遠超過中國。幾萬、幾千群眾圍觀死刑,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近代歐洲。而且,歐洲圍觀死刑的群眾還很激動。就在魯迅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吃人」之前不久,19世紀初,英國的一次絞刑有4000多群眾觀看。可能是廣場不夠大的緣故,也可能是沒有羅馬競技場那種梯形觀看台的緣故,也可能是一次殺人太少,群眾難以輪流看到的緣故,4000名狂熱的死亡看客競相擁擠。一個犯人的絞刑儀式完成後,廣場上又發現了100多具被踩死的群眾屍體。我才知道,原來歐洲人對於他人死亡的熱情遠遠超過中國人。
魯迅《藥》中的人血饅頭只是小說的描寫,具有特指的寓意。後來我發現,真實的群眾「吃人」的狂歡場面,也多次在歐洲出現。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砍頭後,很多民眾湧上前去,用手帕、領帶、衣服等容易吸收液體的物品,蘸取國王屍體上的鮮血,當場舔食。魯迅說的人血饅頭只是用來治「癆病」的特殊用途,而巴黎人舔食國王的鮮血,是想沾染貴族氣息,比治病更具普遍性。幸虧死者是國王,否則他很可能就被群眾當場吃掉。17世紀時,法國一個謀殺國王的刺客被公開以磔刑處死。這名刺客的身體被刑具撕裂後,民眾衝上去爭搶切割,有的就近燒烤,有的帶回家,有的當場生吃。記載說,有一名婦女當場吃掉了死者的心臟。這次行刑後,有人寫道,這名刺客是被巴黎「分享」了。我才知道,原來歐洲人比中國人更加殘忍,更加嗜血。
我並不想否認魯迅所說的中國傳統有殘忍的一面,但是,如果按照魯迅的引導就簡單得出結論說,中國人就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民族,我終於發現這個「既定」的觀念是錯的。中國人並不比西方人更殘忍,更喜歡殘忍,中國人絕不是世界上最殘忍、最野蠻的民族。我認為魯迅的這種做法造成了一個嚴重的誤導,使得我在年輕的時候,上了他的一個當。但是,這不能責怪魯迅,只能責怪那些用魯迅的這個觀念來教育孩子的人。我不明白,當初為何要拿這樣殘忍的內容來教育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