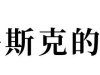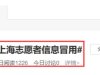神情嚴肅的警察,出現在面前,他們晃了晃手裡的證件:「請跟我們走一趟。」這是電影中常見的一幕,說明你已惹來了麻煩。 (
5月24日,當同樣的場景出現在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正在這裡忙碌的20多名志願者,被嚇了一跳。
這是位於成都市區的一棟辦公大樓,三室一廳。之前,一直是NGO「根與芽環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辦公室,它的國際總部負責人是著名的動物保護專家珍古道爾。地震之後,這裡成為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的指揮中心,包括50餘家核心NGO、還有超過100家NGO參與協作。
年輕的志願者們身著統一的紅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標誌:NGO。字母「O」被設計成震央,輻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個字母緊密串連在一起。除了表明他們與災區民眾團結一心,還志在說明,震後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間的NGO聯合在一起的這個臨時機構,不是烏合之眾。
當時,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的總協調人張國遠,正在協調前方物資的調配:廣東獅子會捐助的3台流動廁所,需緊急運往位於綿陽安縣的災民安置中心。另一個發起人、雲南發展培訓學院的院長刑陌將親自送貨上路。
張國遠的另一個身份,是紅棉市東區志願者協會的秘書長。地震次日,他就來到成都,被推薦為這個NGO聯合組織的總協調人。他發現,不速之客來自自己的家鄉。兩名紅棉東區警局的刑警,顯然衝著他而來。
警方接到舉報稱,紅棉東區志願者協會利用抗災,違規接受捐贈。根據有關規定,抗震救災接受捐贈的主體為中國紅十字會和中華慈善總會。而作為一個臨時成立的機構,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不光沒有來得及註冊,甚至連帳號也沒有。
「這是一個法律空白,專門對NGO如何接受捐贈的相關法規需要規範。」律師陳渡強說。
「我們沒有接受捐贈。我們只是接受人們的信任和委託,利用各自NGO的經驗和組織,把這些善心安全地送達需要的災民手裡。」張國遠小心翼翼地組織著字眼。他28歲,面對警察的問訊很鎮靜。他到成都後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看起來很勞累。
基於NGO組織之間的信任,一些對於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選擇和張國遠他們合作。廣東獅子會會長劉小剛表示,許多捐贈者沒有選擇紅十字會而是點名要求委託NGO代為向災區捐贈,就是因為這些NGO多年積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劉小剛在電話里說:「地震的形勢太緊急,根本不容許我們按照過去的流程工作。我基於對張國遠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錢撥付給了他本人。」
張國遠介紹,他們的運行,得到了來自廣東獅子會每天10萬-15萬元的預算支持,並相繼得到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2萬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曉燕5萬元支持。這些錢主要用來採購救災物資。
警察在辦公室檢查了帳目,並沒有發現這幾筆錢的異常。在經過2個小時的問訊和筆錄之後,他們還是奉命請張國遠一起回趟紅棉,給上級領導做更詳細的說明。
張國遠已經被這事困繞了好幾天,當地政法委、組織部、團委都不斷打電話來了解情況。張國遠無奈地說,「如果當時及時報告了我們的計劃,並且以依託政府的名義做,或許就不會有現在的麻煩了。」
劉小剛說,他們的合作是透明的。「我們歡迎監督,查得越清楚,我們越歡迎。」每一筆錢財的進出,都有詳細的帳目,張國遠並不擔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覺得中途離開災區太耽誤時間。他想坐飛機回紅棉,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們一起坐火車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許出現任何差錯」。離開夥伴們前,張國遠很有感慨地說。這個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時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時期的聯合
算起來,警察造訪之時,這個迄今最大規模的NGO合作組織,已在災區緊鑼密鼓運轉了11天。「一切良好。」「根與芽」辦公室主任羅丹這樣評價這個階段的團隊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時,張國遠正在北京開會。地震央斷了他正在參加的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成都方向電話無法接通,重大傷亡消息陸續傳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小時內飛到災區。他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NGO發展交流網負責人陸非聯繫各個NGO負責人:「我們這麼多NGO,是不是該為災區做點事情?」當晚,與會的100多個NGO負責人做出第一個決定:委派張國遠到成都實地了解災情,然後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中國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關注領域不同、行事風格不一,在張國遠印象中,他們還從來沒有為了同一個目標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發出聲明——「發揮民間組織力量,聯合做出反應,共同支援災區,關注災後重建」。
當天早上,張國遠乘飛機往成都趕。雙流機場關閉,直到中午飛機才降在重慶。剛打開手機,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電話和簡訊就追蹤而至。心急如焚的張國遠又換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時,在成都的NGO組織已經開始行動。
「根與芽」的羅丹一直在網絡上和其他NGO商討方案。餘震來了他們就跑下四樓,停了再跑上樓和大家在網上交流。很多人在問羅丹:我們能為四川做些什麼?
13日晚上,羅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來到四川團省委,表達了希望參與地震救災的想法。羅丹說,團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和方式,歡迎。但是,也只能以志願者的方式,僅此而已,其他方式並不提倡。
NGO們想的是以一種全面的姿態介入救災。「我們本身就是獨立的NGO,應該有自己的運作方式。」張國遠認為這種合作意義不大。他們決定自己單獨搞。陸非的這個提議得到了認可。5月14日,50多家NGO發起的「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誕生。地點就設在「根與芽」,因為這裡能上網,辦公室也足夠寬敞。
陸非坐鎮後方,負責搜集和編輯有關災區的信息。「抗震救災——民間公益在行動每日特刊」火線誕生。張國遠坐鎮前方,具體協調前方災區的信息收集、物資的收集、發送和調配。
與此同時,地震發生後23小時,5月13日中午1點半,另一個NGO愛白組織向外發布100個QQ群救災行動的簡報,並迅速與20多個以成都為基地的本土及國際NGO聯合,建立「五一二民間救助服務小組」。
五一二民間救助服務小組和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成為這次八級大地震救災工作中的兩大NGO平台。
奔赴災區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14日,幾個關鍵部門先後成立。首先是服務捐贈機構,NGO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時間迅速發動,一呼百應。14日,1.2萬噸大米抵達成都。24小時之內,這批大米就從張國遠手裡配送到災區。
而根據張國遠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過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資,堆積如山,但是因為需要層層審批和調撥,很多只能堆積在倉庫中,來不及發放到災民手裡。
此後這裡收到全國各地NGO募集捐贈的物資,以及其他單位捐贈並轉運的物資,平均每天在50萬-60萬元。為了臨時儲存這些物資,又成立了物資轉運中心,朋友免費提供了一處近200多平方米的倉庫,地點就在「根與芽」的樓下。大批救災物資,包括食品、藥品、衣物幾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們聲明不接受個人捐贈,因為沒有辦法有效管理和對個人捐款者負責。25日,根據前線的調查,災區的救災物資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贈也將告一段落,一個新的備災中心即將成為接下來的工作重心。
在災區前線,他們成立了7人組成的調查隊,利用獅子會在綿陽等地的救援人員和媒體記者,搜集災區信息,根據調查和災民需要,由物資轉運中心發放物資。運輸工具也是通過網絡或者志願者中徵集。30-35輛救災物資轉運車輛,全部是志願者車隊,有些汽油錢,都是志願者自己掏的。運輸費用基本為零。
5月24日,雲南發展培訓學院院長邢陌要運送一批藥品和棉被到綿竹的漢旺鎮。同車的還有雲南青少年發展中心的周蓉,司機是來自貴陽的女志願者魏薇。
這是一個臨時組合,此前都不認識。邢陌已經記不清在這條路上跑了多少次。經過近3個小時的顛簸,貨車到達漢旺,綿竹的救災物資中心就設在東汽的院子裡,約上萬平方米。邢陌把物資卸載,又通過當地負責接收的政府部門簽收。邢陌說,因為涉及到處方藥品,不能直接發送到災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處,都會向接收單位索要收條。除了回去入帳,還要給捐贈者一個交代,「保證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這個救災物資中心的總指揮、綿竹市副市長張滔聽說邢陌是NGO組織,很感興趣地說,這次地震,你們NGO發揮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無法做到的。他說,等抗災結束以後,一定要去成都拜訪這些NGO組織。
從物資中心出來,車又開到了漢旺鎮武都村11組。前天邢陌來運送物資,這裡的災民告訴他,因為還沒有恢復供電,很多人是摸黑吃飯,有些小孩沒法讀書。政府送來了糧食和衣服,還沒有顧得上這些細節。這天邢陌專門送來了一箱蠟燭。村民聞訊,都從帳篷里跑了出來,有的要了2支還想繼續要。維持秩序的當地幹部不得不大聲勸說:「不要重複領取了!需要的人還很多,請大家表現出素質來。」
晚上7點,行動結束,他們沒有停頓,立馬往成都趕。晚上還要回去開會,討論一天的工作,並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計劃。
這些志願者最大的本錢,就是熱情和專業技能。邢陌的雲南發展培訓學院專門從事國際培訓,對管理和協調十分熟稔。貴陽的魏薇已經來了一星期,她在貴陽一家汽車4S店工作,請假來這裡。她的丈夫是貴陽消防隊員,兩人前後腳來抗災。魏薇開車是一把好手,自稱只聽發動機就能判斷出不同車輛的型號,這次一輛小貨車別人開不了,她自告奮勇,雖然中途兩次迷路,但是基本沒耽誤事。周蓉主要開展災區兒童心理干預,每到一處,都去災區兒童安置點收集信息。來自紅棉的志願者劉紅斌主要負責看管倉庫,到成都後哪裡都沒去過,他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和其他志願者晚上就睡在倉庫外面的帳篷里,但是他並不介意。「這裡一樣是前線,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間表達
除了五一二民間救助服務小組和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還有為數眾多的NGO在災區單獨活動。綠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綠色江河是典型的國產「草根」NGO。負責人楊欣上世紀80年代曾參與長江漂流,後來成立了旨在關注可可西里環境保護的綠色江河。
地震發生後,楊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開著私家車拉著救災物品奔赴災區,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貨物卸載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這是中國民間第一次如此大規模釋放慈善情懷,但是很可惜,沒有得到有力的疏導。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楊欣說。
綠色江河的一個大本營是在深圳。當天,深圳的企業、市民就把捐贈的物品送到了他們手裡。但是綠色江河一開始就沒有公布帳號接受捐款。楊欣顯然對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雙刃劍,不能傷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麼漂亮,事後總是有人質疑。」
地震次日,綠色江河緊急動員各地誌願者。「挖人肯定不是綠色江河這類環保組織的強項。」他們能做的,就是利用一個NGO的組織和目標管理經驗,救助災民。
NGO靈活快速的反應速度,在這次抗災中表現出來。楊欣認為,「NGO是一個補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組織的挖掘和搶救工作,個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關注宏觀層面上的居多,但總有滯後的點。而我們則關注冷點,以及沒有被關注到的鄉鎮和邊遠角落。」
在具體的救助過程中,楊欣發現,政府機構為維護災區穩定,在發放救災物資時基本會平均發放,有些鄉鎮幹部因為物資不夠,怕引起災民不滿,甚至就不敢發放了;綠色江河卻更側重於幫助那些恢復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還沒有精力顧及的災民。
比如綿竹的興隆鎮靈橋村。這是一個志願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央,基層政府遭受重創。村鎮幹部也成為災民。
志願者楊礁記得,14日,他們第一次驅車來到靈橋村,政府的救援隊伍還沒有觸及這個角落。因為這個地方的災情不是最嚴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當時主要顧及重災區。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車輛經過,災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攔在道路中央。
根據先期搜集的信息,他們帶去了麵包等食品。深圳志願者熊楊得知災區斷水斷電,缺乏乾淨的飲用水,立刻聯繫了深圳的一個淨水器廠家,改裝生產了一種不需要電力就可以操作的淨水設備,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來。
興隆鎮的譚鎮長感激地說:「綠色江河是最早到我們這裡的救援力量,給了我們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綠色江河第二次去靈橋村,發現災民的秩序已經開始有序,政府救援隊伍是15日抵達這裡的。他們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樣的賑災
綠色江河決定把靈橋村作為自己長期幫扶的一個固定村子。他們採用的方式,是實地考察再決定捐贈。比如政府部門也向這裡的災民發放了很多救災物資,但一些災民覺得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比如方便麵,因為缺水停電沒法吃。
楊礁發現,因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災民家存放的糧食,面臨遭受雨水侵蝕的威脅。此外,一些受災家庭沒有做飯的地方。於是他們採購募集了一批用於遮雨的塑料彩條布,以及熟饅頭、食用油、蚊香、蠟燭等救災物資。
志願者聽到這個村村民在傳言:另一個村子的災民將襲擊這裡搶糧。他們了解到這是一種因為信息不暢引發的恐慌,於是專門採購了100台收音機發放給災民。
一次,一個鎮衛生院的醫護人員悄悄地問楊礁,很多天沒有洗澡換內衣褲,能不能給我們帶一些一次性內褲?鎮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難處:他們臨時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個,但是安插了30多個人住,能否提供一個布簾,把男女擱開。這些細小的要求,綠色江河一一滿足。
楊欣比喻說,就好比一個瓶子,光把石頭扔進去,看著好像填滿了。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滿空隙的這些沙子,就是民間的力量。
他認為,政府的優勢,是統一指揮,信息一級一級匯報,物資是一級一級配發,包括採集信息和調配。但是體形巨大,所以轉身困難。而NGO的優勢是靈活。用楊欣的話,就是直銷。靈橋村缺棚布,一個電話打過來,就可以去採購,具體到多少米,幾個人使用,都有詳細的信息。
5月26日,綠色江河一行再次驅車趕往靈橋村。地震後,他們平均一兩天就來運送一次物資。
3小時後,車隊開進靈橋村,這裡傷亡數量不大,但是超過90%的房屋受損,村民都露宿臨時帳篷。看到綠色江河,他們都很熱情。靈巧村的村長景正榮介紹,這個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戶,是過去兩個村子合併而來。因為受災普遍,救災形式很嚴峻,而綠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對於「NGO」,村民一直沒弄懂是啥意思,景正榮也說不清。但靈橋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運抵這個村子的救災物品中,NGO組織「綠色江河」發送來的物資就占到了一半。
當天村民清理廢墟的時候,意外發現一個88歲的已經死亡的老人。半個月後才發現屍體,村民很恐慌,雖然消毒多次,大家紛紛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連帳篷也不願意呆了。
綠色江河此行,就是運送剛剛從深圳運來的70多頂帳篷,來給災民安置臨時住所。在分發帳篷時,他們還特別注意公平,首先發給老弱病殘。
熊楊還從深圳捎來了深圳荔園小學的同學李致安給災區孩子的問候,這個家境並不富裕的孩子郵寄來自己的111元壓歲錢,還親手製作了一個心形的平安符,熊楊把這個物品轉送給了興隆小學的一個學生。學生激動得小臉通紅,在一張紙上寫下感激的話和自己的聯繫方式。
熊楊表示,即使是小學生委託他們送到災區的東西,他們也要儘可能讓接收者出具收條,每一個捐贈人的物品到達什麼地方都必須有交代。
「我們是透明的。NGO應該脫光了讓人監督。這是我們的立身之本。」楊欣說。
另一邊,身在紅棉的張國遠則打來電話稱,28日他原本計劃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調查」仍在繼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