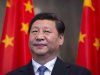余英時:談談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
第一個是很好的一面。因為他在「六四」學生被鎮壓的時候,站在學生一面,支持學生。但是慢慢就變掉了,被共產黨攻心之法攻下來了,變成歌功頌德的人了,專門提倡中國民族主義,所以他晚年這十幾年,就被共產黨不但捧為「國學大師」,而且還成了「國寶」。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寫《泰山頌》,歌頌泰山,其實歌頌的主要就是共產黨。說共產黨來了以後,現在天地都變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間許多冷嘲熱諷。
同時,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這古印度文字、跟東南亞文字、中亞文字,與中國毫無關係,怎麼可以變成「國學大師」?所以又在網上引起很多批評。
他也聽到這些不大好聽的話,有一次就公開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師」,尤其不是「國學大師」。以為這樣子就能平息閒話,可是事實上沒有用。共產黨官方已經把他封定為「大師」了,因為他們需要有這樣一個好象德高望重的人來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變掉了,從最初這個抗議天安門屠殺,到後來歌功頌德。寫書,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來的,叫做《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這裡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寫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較算是學術研究的,後來就沒有了。後來反右啊種種,跟其他人一樣,也不能怪他。總而言之,這個人也是一個讀書人,也是讀出相當成績的人。可是因為政治上的反覆,變成這樣一個「大師」,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個任繼愈先生,我個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學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繼愈跟我也算是同門。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時候,他那時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他還特別到旅館來看我。後來,到美國來,還在我家住過一陣子,我們有些私交。他當然也算是「大師」級的,年齡比季羨林小不了多少,這兩位都是念書人,原本都應該還是不錯的。可是任繼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權力、勢力範圍之內了。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學問,他寫過佛教史的論集,也是跟季羨林一樣,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後來就沒見到有什麼新的工作了。這是環境使然。
這兩位先生現在都已變成「大師」,也可以這樣說。可是我們要看看古代的「大師」,遠的不說,象清朝的戴震、錢大昕,更早一點的顧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師」。到民國初年、清朝末年,有孫詒讓、周里德等;再下來,章太炎(章炳麟),還有康有為,這些都是「大師」,那是真正的「大師」,是大家公認的。這些人跟政府的關係,都可以說並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時候支持政府,有時候反對政府,能說出話來,都是獨立的、獨立發言的,在社會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後一代,象胡適,也變成「大師」了,也是負國家重望,說出每一句話來,都受到重視。他批評政府也很嚴格,從大陸一直到台灣,都是如此。蔣介石一方面非常討厭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動他的手。
所以過去的「大師」至少可以發揮中國學術界對政府一種監督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因為這種監督和批判力量,才長久地獲得學術界的尊敬。而學術界也因為有這樣的「大師」,也慢慢地得到一種應有的地位。
這個地位本來有它的尊嚴,學術界不是給政府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一變成「歌德派」,學術界的人就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過去,「歌德派」的人,絕不會成為「大師」。而在共產黨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為「大師」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學術界沒有獨立的力量,這是中國最近六十年來,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這個不幸的事情,當然跟它的政治制度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在共產黨底下,不會讓你跟黨的基本的教義、或者基本的意識形態相抵制而存在。現在雖然不堅持馬列主義這一套,可是還有一點是一定堅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維現在的政府,說現在的執政黨是偉大的、中國前途完全靠它這個黨、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學界大師,象楊振寧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大師」,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點是跟過去絕對不同的。因為以前的「大師」是監督政府的,或者說是批判政府的。這種力量是獨立的,政治領袖沒辦法在過去的時代製造出「大師」來,就是從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師」來。 「大師」是社會上、從底下念書人心裡頭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長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來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別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這是所謂中國未來要擔心的地方。如果社會不能製造獨立的學術界、沒有一個獨立的是非標準,使得學術界、精神界出現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一種「大師」、一種精神領袖的話,那最後就只有歌功頌德的人,就象寫這個《泰山頌》的季羨林先生一樣的「大師」了,季羨林先生也不是一個什麼不好的人、也不是什麼壞人,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後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盪,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所以我想這是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很大的危機。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旅美國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的有關評論,從中國歷史上的國學大師談他對季羨林和任繼愈學術地位及品格的看法。
責任編輯: 沈波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09/0805/138202.html
相關新聞
 孫立平:2024:中國經濟決定性的一年
孫立平:2024:中國經濟決定性的一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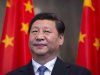






 未普:沒有思想自由 中國就出不了大師
未普:沒有思想自由 中國就出不了大師


 潘光旦其人其事
潘光旦其人其事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