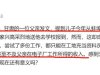余協中
余英時先生大名鼎鼎,但是余英時的父親,世界史學者余協中卻不為人所熟知,據《晚年定居美國的學者余協中》一文介紹,余協中生於一八九九年,三歲的時候喪父,由母親吳氏撫養成人,十七歲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一九二一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評》。一九二六年入美國卡拉格大學(Colgate College)就讀,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繼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但是沒有讀完博士課程便返回北平,任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一九二九年春天余協中和張韻清結婚。
余協中的處女作是一九二三年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幾句關於女子參藝的話》,余協中針對的是當時報紙上關於女性是否應該參加藝術活動的問題,認為女性應該參與藝術活動,同時余協中認為討論問題應該具有點取善去惡的道理,不能吹毛求疵,專找別人的錯誤,那就未免失去批評和討論的意義。文章最後注有餘協中的地址,西城半壁街,應該是余協中當時的住處。
過了兩周,余協中又以「協中」的筆名發表了一篇名為《我看了「純陽性的討論」的感觸》,主要針對的是八月十九日蕭度致孫伏園的信,蕭度在信中認為五四以來雖然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女性的很多議論是淺薄的,余協中認為這與時代有關,許多女學生在讀書時還知道「解放」「自覺」等等觀念,但是最後都不知不覺的陷入到了「賢妻良母」的泥淖中,在結尾余協中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夠參與到社會的種種活動中去。
沒過多久,一位名為松雪女士的作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讀〈純陽性的討論〉答協中君子》的整版文章,對余協中進行批評,認為余協中所言「女性做了太太之後大半被賢妻良母主義征服」,等於直接坦白男性妨礙了女性的獨立與發展,同時作者認為新文化運動乃至文學革命,甚至是晚清的政治革命,都不乏女性的身影。從全文來看,松雪女士不僅誤解了余協中文章的原意,而且火氣極大,很明顯缺乏討論問題的心平氣和。
在此之後,余協中很長時間沒有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直到一九二六年,余協中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新式婚姻制度下的危險性》一文,這篇文章當時隨處可見,影響也很大,引起了徐志摩的注意,當時徐志摩是《晨報副刊》的主編,將這篇文章在《晨報副刊》上轉載,徐志摩還不忘調侃余協中,在按語中徐志摩說:「出娘胎來做人本人就是危險性的事業……就比是絕海里行舟,海是反正有波浪的,就看你把的穩還是把不穩,我們該注重的,按我說,不是跟海去商量要它減小她波浪的危險,我們該研究的是怎樣才能練成功我們航海的本領。」
一九二七年夏天,當時余協中轉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西洋通史,並且出版了同題的著作,由世界書局印行,一九三三年出版,一共有三冊,余協中在此書的序言中說:「數年來歷在各大學教授歷史課程,講稿屢經修改,迄無暇整理付梓。今夏世界主人迭函約為該局撰《歐洲外交史》,旋復為應目前的急需,囑先編《西洋通史》,情意懇致,不得已勉為擔任。」
余協中在該書的導言《歷史的研究》中,除了分析世界歷史上各朝各代的變遷之外,還頗有興致的談到了辛亥革命:「歷史包括範圍太廣,其變遷也是逐漸的,單是政治,或宗教或經濟的重要事端,絕不能忽然改變整個的歷史,譬如一九一一年清代滅亡了,一九一二年便屬民國史的範圍,試問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除了把政府制度改變以外,其他經濟、社會、與宗教等等又有何種區別?」
余英時的學生王泛森後來在一次演講中,曾經談到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余協中在哈佛讀書時候的導師是阿瑟•施萊辛(Arthur M. Schlesinger),王自己曾經在服役的時候,偶然在士官學校圖書館看到過《西洋通史》,王對於此書的作者居然是余英時的父親大感震驚,因為這書不僅寫的不錯,而且給學生上課還頗有參考價值。余英時後來去哈佛讀書,余協中還特意叮囑余英時前去拜會阿瑟•施萊辛。
余協中在南開大學教書期間,余英時出生,張韻清因為難產而去世,余協中睹物傷情,遂離開天津,到安徽大學授課。而後余協中還曾經在復旦大學教過書,最後在東北辦了中正大學。王泛森提及,台灣中正大學要復校的時候,曾經請余英時擔任復校之後的第一任校長,當時《中國時報》的董事長告訴王,希望由他致電余先生,請他回來繼承父親的事業。
余協中在南開期間,發表的文章較少,目前查到的只有一九二九年發表在《社會學界》的《北平的公共衛生》一文,這篇文章篇幅較長,是一篇非常詳細的調查報告,還附有圖表,全文分為七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北平衛生泛論」,第二部份為「公共衛生的略歷」,第三部份為「北平過去現在衛生的行政」,第四部份為「北平衛生工作的困難」,第五部份為「北平過去衛生的工作及預防政策的重要」,第六部份為「由統計表研究北平公共衛生應注意之點」,第七部份為「現在衛生局對於北平衛生的計劃」。《社會學界》是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刊物,余協中發表的卷數是第三卷,同期發表的還有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和歷史學家瞿兌之的文章。
余協中生命中至關重要的轉折,是一九三○年出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常委兼研究部主任,張學良任該會會長,數月後又前往南京就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外交組委員,當時蔣介石是該會的委員長,兩年後余協中返回北平任原職。抗戰爆發前夕,余協中南下開封,任河南大學歷史系主任,一九三九年赴重慶任國立編譯館編譯,後往昆明任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余協中在此時結識了于右任,以書法名世的于右任曾經手書贈余協中,其中有「開門常遇竹馬鄰」,可見兩人私交頗密。
余協中在自述中曾經言及,當時國防設計委員會外交組委員還有李維果、高宗武等人,當時蔣介石的剿共正處於關鍵時期,蔣介石親自在南昌指揮,余協中所在委員會改為偏重國防資源研究,外交組轉併入外交部,於是余協中才返回北平出任原職,當時是民國二十五年。余協中感覺日本侵華形勢日漸緊張,在七七事變之後將余英時送回潛山老家寄養。
余協中在河南大學時,學校受當時新生活運動的影響,成立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組織婦女問題討論會,當時請余協中指導進行,可知當時余協中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時河南大學時事研究會還請余協中就中日關係發表了題為《從國際立場觀察最近中日關係》的演講。
據《申報》一九三五年所刊登的《省立河南大學現況》報導,當時余協中是文史學系的主任,當時的校長是劉季法,文學院長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蕭一山,法學院長是王希和,英文學系主任是饒孟侃。著名歷史學者蕭一山後來和余協中過從甚密,據陳夏紅在《法政往事》中記述,一九三○年代的余協中曾經和楊兆龍、蕭一山、祝世康等人,在南京成立經世學社,創辦了《經世》月刊。楊兆龍在經世學社時間不長,但短期內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擔任過一段時間《經世》主編之外,還寫了不少時政評論,余協中也對此月刊貢獻甚大。據查余協中在民國時期一共發表過約五十篇文章,其中在《經世》上發表的文章就有二十一篇,其中有《戰鬥精神與最後勝利》、《幾點關於游擊戰與民眾組織的意見》等文章。
從余協中三十年代發表的文章可以很明顯看出他從學者轉而從政的變化,三十年代早期余協中主要在《外交月報》上發表文章,其中有《兩大戰爭中法國的外交與我們應有的教訓》、《美國遠東政策的過去與將來》等文章,同時還翻譯有《經濟制裁與外交》一文,從這段時間可以看出余協中對於中外政局的高度關注,也可以看出當時余協中身份的變化。
抗戰爆發後,當時河南大學也隨著局勢發生變化,轉而前往他地,余協中一開始在重慶,後來在戴季陶的幫助下前往昆明,但是余協中非常不適應昆明的生活,加上胃病常常發作,後來接到家書得知母親故去,因此返回潛山,抵達重慶時得知歸鄉之路已斷,於是留在重慶,後來與尤亞賢在重慶結婚。當時雖然兩人都有工作,但還是要靠賣文補貼家用,余協中認為此為一生寫文章最勤的時候。
隨著抗日局勢的日漸緊張,日本準備完全切斷中國的國際路線,同時進攻緬甸,於是政府派遣遠征軍入緬甸,余協中隨軍擔任外交聯絡員,駐眉苗與英駐緬甸都督保持聯繫,但是英國駐紮緬甸的軍隊毫無戰鬥力,迫使中國遠征軍向南撤退,許多軍隊無法撤退而轉向前往印度,死傷不計其數,余協中僥倖不死返回國內。余協中返回國內之後,任職於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繼而被任命以休假教授的名義赴印度講學,當時余協中的次子余英華剛出生,營養不足,國內收入遠不足用,所以余協中答應前往印度,此時已經是一九四一年秋。
據余協中自述介紹,當時余協中旅居印度八月,足跡遍及加爾各答、新德里、孟買等地,當時甘地和尼赫魯都在獄中,無法與余協中見面,但是尼赫魯在獄中致函,請其妹哈青遜夫人與余協中接洽,當時余協中住在孟買,哈青遜夫人經常來訪,同時甘地的長子和次子也和余協中有過多次接洽,余協中認為甘地長子似乎不大成器,次子辦報,似乎較有思想。余協中在印度還會見了回教的領袖真納,余協中受真納邀請會面,本不想見,後來雙方約定談三十分鐘,不想談了四個小時,其間讓余協中印象深刻的是雙方談論如何防衛東巴基斯坦問題,後來東巴基斯坦的獨立,證明了余協中的預見性。
余協中回國之後,根據研究調查所得,撰寫出報告呈交軍委會,余協中認為根據當時的情形,印度獨立是必然的結果,甘地為宗教領袖,尼赫魯是政治領袖,將來掌握政權的必然是尼赫魯,中印關係和諧大過衝突。余協中本來想回國重執教鞭,但是軍委會力保其出任遠征軍政治部中將主任,余協中認為自己一介書生,不能擔任此大任,但是另外一方面,余協中也有不赴任的考慮,當時余協中就戰後和平問題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得到了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賞識,戴季陶命令秘書邀請余協中擔任考試院參事,余協中欣然答應,在考試院工作期間,余協中加緊讀書,同時在南溫泉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教職,一九四四年,軍委會將全國分為四區,每區聘請一人擔任演講,余協中被調任兩廣、湘、鄂、贛等地。
余協中之所以獲得戴季陶的賞識,與當時余協中對於戰後世界局勢的判斷有關,一九四○年《讀書通訊》雜誌將余協中的這篇社論轉載,置於問題筆談欄目第一篇,同時也刊發了林同濟《戰後世界的討論》和胡適的《論戰後新世界之建設》等文章,可想而知當時余協中這篇文章的影響。余協中認為,戰後應該成立和平組織,嚴懲戰爭罪犯,同時防止戰爭再次發生。應該說余協中當時非常具有遠見。
余協中在福建時,日軍大舉進攻,余協中欲返回重慶未果,幸虧胡宗南部和美國飛虎隊的到來,才阻斷了日軍的進攻,隨後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戰爭結束,當時余協中的朋友杜聿明被任命為東北保全九省司令長官,請余協中一併前往,擔任長官部秘書長一職,余協中無奈向考試院告假一個月,抵達南京後才知道自己已經被任命,考試院職務自動取消,余協中感到非常無奈。余協中前往瀋陽之時,當時蘇軍還未撤退,共軍還在沿途,所以行程緩慢。
余協中初到瀋陽,被任命為東北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沈脗無自述中曾言及:「這年冬天,燕大同學李蔭棠和余協中來找我,余協中比李蔭棠高兩班,他們都是歷史系同學。我以前不認識余協中,他來約我到東北去教書,說要在瀋陽辦中正大學。」中正大學成立時,校長張忠紱並未到校,余協中隨後被任命為校長,當時和余協中同事的還有中文系主任高亨,但是高亨在中正大學只是兼職,本職工作是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據《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五十輯的一篇文章介紹,當時的中正大學校董會都是由東北政界頭面人物組成,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擔任名譽董事長,杜聿明擔任董事長,校董會而且囊括了當時東北軍政大員,但創建一所私立大學,仍需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批准,在校董會商討這所私立大學的名稱時,杜聿明主張定名為「中正大學」,一則為取悅於蔣中正,二則便於立案,爾後以中正大學之名義報呈教育部。果然教育部一反辦事效率極低的常態,很快就批准了這所東北中正大學。杜聿明為了辦好這所大學,不惜重金聘請名教授到瀋陽,一時人才雲集,校長為張忠紱,是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原系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全校劃分為四個學院,文學院院長是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工學院院長是留美的王華棠;法學院院長是留美著名的國際法專家學者王鐵崖(薄熙來的夫人薄谷開來的老師);農學院長是林業專家賈成章,原中央大學教授王書林擔任訓導長。
但是不久之後,瀋陽就被中共軍隊攻下,攻城前余協中還曾經前往上海與陳納德商議租借飛機,將學生接到北京,當時中共部隊駐紮在石家莊,學校無法繼續辦下去,只好請教育部接辦。余協中自此離開瀋陽,攜家眷前往上海,旋即赴香港。此時已經是一九四九,天地玄黃。
余協中的三子余英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隨父親遷居香港,一九五○年余英時也來到香港,入讀新亞書院,而余英華則進入華仁書院就讀,余協中的二兒子余振時一九四九年之後二子隨養母張韻華留在中國大陸。一九五五年余英時前往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次年正式讀博士,這一年余協中攜全家赴美,定居波士頓。
余英時一九四九年之後到香港,也經歷過一番思想鬥爭,余英時後來在為巫寧坤的書所撰寫的序言中回憶,他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一滴淚》的作者巫寧坤早了兩年。一九四九年年底,余英時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的來信,原來他們又從台北移居到香港。五○年年初,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余英時後來如此描述跨越羅湖橋的感受:「突然我頭上鬆了,好像一個重大的壓力沒有了。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有一個壓力,思想上的壓力,那壓力就在過橋的一刻,頭一松就消失了。這是我真實的感覺,如果講自由不自由的感覺,那是真實的。」
余英時原來認為來港只是短期探親,還決定回去,在回程的火車上余英時內心掙扎,後來他再接受香港電視台採訪時回憶:「三、四個鐘頭里我都在回想,我在想的不是政治問題,想我的父親年紀大了,一個人在香港,我弟弟還很小,七、八歲。我離開,他嘴裡不說,但心裡很難過。好像是不顧他們。所以我想,中國那麼大,多少億人,少我一人,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對我的父母來說,我就比較重要。用共產黨的話,是自己作思想鬥爭,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跟愛國主義之間的鬥爭。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我就決定還是回香港。」
余英時覺得自己對香港一直有情感,五十年代他當學生時跑遍大街小巷,雖然開始不習慣,很想回去,待久了才發覺真的自由,無拘無束,余英時認為要不是在香港成長,他也沒有今天這種自由想法,余英時說:「如果在共產黨或國民黨教育下長大,一定會受限制,有些東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余英時同時認為:「現在香港的言論、說話的人,慢慢自我控制,香港有這個危險性,開始一個自我洗腦的過程。」
也正是因為香港這種自由的氣氛,余英時才得以在思想、學術的世界中暢遊,以至於後來卓有成就,和余英時一樣,余英華也非常優秀,余英華一九六八年獲得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後即在密西根執教,一九九七年起任紐約州立大學布羅克堡分校校長,二○○四年起擔任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校長。余英時一九六一年從哈佛畢業時,也曾經在密西根大學執教。余協中晚年最值得欣慰的事情便是二子均有所成就,當時余協中的妻子尤亞賢在哈佛大學任職,後來在密西根大學解剖系擔任研究員,曾經與伯克(Baker)教授合作撰寫多篇有關癌症的論文。
余協中僑居波士頓劍橋時,還曾經和胡適有過交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潛山余協中來訪,他是用Refugee Act(難民法案)來美國居留的,現居Cambridge(劍橋),他說起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無可限量。」胡適當時還對余協中說:「我常常為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
但是胡適當時沒有想到,後來他的年譜長編乃至日記的出版,都是余英時寫的序言,胡適更沒有想到的是,余英時成為了繼他之後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人。
余協中自述來美時年事已高,所以索性不再工作,安心讀書,專心學問,余協中認為美國是難民的天堂,美國社會基礎穩固,能夠充份保障個人的自由,讓每個人安居樂業,而且美國以前雖然有種族歧視,但是現在越來越少,現在黃種人和白種人沒有差別,余協中說自己剛來美國時一無所有,但是現在生活得很舒適,來美國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美國沒有特務跟蹤或者秘密警察的盤問,但是「唯共產嫌疑者除外」。
當然余協中晚年也有很多的遺憾,最大的遺憾便是不能回國,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經致信給在國內的侄子余天寶,詢問當時的國內情況,當時余英時即將率團訪問中國,余協中也申請回國,他在信中提到國內很多長輩均已過世,非常悲傷,同時余協中詢問天寶那些長輩的墳墓安葬在何處,同時詢問天寶從安慶到官莊是否需要乘坐公共汽車,需要多少時間等詳細問題,同時還問起官莊和其同輩的一些朋友是否還在世。但是這封信因為其中問及家鄉是否能吃飽的問題,被當時的生產隊劉書記扣下,沒有及時送到余天寶手裡。
余英時一九七八年訪問大陸,見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再也沒有晤面的弟弟余振時和養母張韻華,當時兩人住在東城區北兵馬司胡同二十三號,這處房產是在余協中四十年代以其夫人尤雅賢的名義購買的,余英時離開大陸之後不久充公,政府另外安排了許多居民遷入,張韻華和余振時只住其中一間,但是政府至今也沒有歸還余家這套住宅。據說余英時當時在北京把養母接到北京飯店話舊時,還曾經遭遇過跟蹤。
余協中最後估計是因為余英時在一九七八年回國的這些不愉快經歷,加上年事已高,沒有落葉歸根,在一九八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他在去世前所寫的自述中說:「有一事不能釋然於懷者,即有家歸不得,因之而來之痛苦,終無法擺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