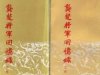龔楚
龔楚曾是紅軍創建人之一、高級將領,他是歷史的見證人。《龔楚將軍回憶錄》很有價值,通過這部書,我們能夠清晰地了解當年蘇維埃政權是怎麼回事,紅軍肅反有多麼殘酷。
毛澤東死後,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才敢於在小範圍內承認龔楚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
紅軍代總參謀長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1929年12月參與百色暴動,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著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干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干。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律援助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看守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所謂長征)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暴動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污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人質與綁票
有飯吃,有衣穿,這是一支軍隊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
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有膽有識的毛澤東就開創了抓「人質」索錢糧和「借糧款」的經驗。這對軍隊的生存和最終勝利意義重大。這一巨大功績理所當然的應記在主席的功勞薄上。
根據毛澤東的戰友、紅軍軍官龔楚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其中記述了一樁紅軍抓人質索取光洋的具體見聞。
一天,龔楚經過瑞金附近的龔房,「因為天氣炎熱,到村里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房,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幾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繳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們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起頭、流淚。龔楚雖然答應替她們想辦法,但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她們。「曾有個醫生因繳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淪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線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份。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當紅軍主力突圍走了之後,這班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著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著手槍藉借糧籌款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款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強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項英曾嚴飭各省級黨政負責人消除這極嚴重現象,迅速恢復蘇區秩序,但結果毫無辦法,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
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龔本人於1990年90歲高齡時回國定居。毛死後,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才敢於在小範圍內承認龔楚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
另據陳毅回憶,若捉住了豪紳家裡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一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一萬元則貼一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摘自《陳毅軍事文選》,陳毅著,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再讀龔楚
龔楚被稱為中共第一叛將,他當時在井岡山的排名僅在朱毛之下,「朱毛龔」更是當時中共公文里常出現的名字。他不但是紅軍的締造者,一手創建了紅四軍和紅七軍,而且長於政治,是中共早期罕見的文武全才。
在讀了他的《我與紅軍》後,又讀了他的《龔楚將軍回憶錄》,後者比前者敘述得更詳細些,但都到他脫離紅軍嘎然而止,對以後的身世經歷沒有一點交待。
龔楚的回憶錄比較難得的是,因為沒有什麼顧忌,所以無論當時高層的人事關係,還是作戰經歷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現出來,比如毛的聰明絕頂與驕橫跋扈,比如朱的溫厚隱忍與籠絡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與唯上是從,比如彭德懷的剛愎自負與推諉責任等等。
讀了龔楚的回憶錄,就可對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討厭知識分子,並不是因為他在北大圖書館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岡山作山大王作得風生水起好不得意時,來攪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來的知識分子,後來是從蘇聯跑來的知識分子,他受這些知識分子的打壓和鳥氣比北大時的奚落更甚。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是激情有餘才幹不足,敗事有餘成事不足,而這又恰恰被中國革命所證明了的。
彭德懷是一個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對自己的軍事才能非常自負,但他統籌規劃,戰場調控的能力很差,打了敗仗還要推諉給人,也是龔在紅軍時期唯一與之有過摩擦鬧過不愉快的人。彭的這種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當年發起百團大戰,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個重要因素。
而周恩來唯上是從的個性也從最早的緊跟共產國際到最後的緊跟毛都沒一點變過,可能唯一改變的就是本來冷酷嗜血的性格變得溫和圓滑。
讀龔楚的回憶錄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幹革命,一干命就會沒有。龔楚在紅軍的那段日子裡,可謂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給他逃過來,一次比一次驚險,他曾坐船僅僅因為沒有和同行的人在一個船艙就逃過一劫,而另一個船艙的同志被捕後就被殺了,他曾和一隊士兵被敵人俘虜,就在敵人要槍決他們時,他用廣東話喊了一句「沒想到我今日要命喪於此」,沒想到同是廣東人的國軍營長就此給了他一條生路。
龔楚的叛變絕不是官方所說的意志薄弱受到誘惑,而是他的信仰和當時蘇區執行的共產國際政策越行越遠。周恩來到蘇區後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殺掉還把富農殺掉,蘇區經濟在重重盤剝之下迅速走向崩潰的同時,周對內部人也展開比毛更瘋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層幹部被殺,一點不亞於張國燾在四川搞的清洗。
龔一方面看到蘇區人民的生活比過去更加悲慘,蘇區政府幹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這種悲慘的生活,一方面看到優秀的部下被保衛局殺掉而無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發展根據地經濟而對地主富農採取溫和態度背上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這種種都使他對中共革命產生失望以致於絕望,他說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而共產主義不講人道,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在中央紅軍長征後,他留下和項英陳毅一同支撐殘局,他主管軍事。此後中央要他帶最精幹的24師去鄂贛粵創立根據地,他任軍政一把手,他到了那裡後找機會脫離了紅軍。
龔楚脫離紅軍,先回了老家樂昌,後加入余漢謀的部隊負責剿共,若不是陳毅謹慎,項英陳毅差一點被他抓住。1949年龔楚在家鄉向解放軍投誠,後經葉劍英舉薦去海南當說客,但他沒去海南而在香港定居下來,蔣介石曾委派他在香港收編殘部,但也被他所拒,從此遠離政治。
1990年年逾90的龔楚重返故鄉,1995年在故鄉去世。
龔楚的一生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他一系列的選擇很值得現代的我們再回顧一下,同時也對中國那段歷史有更深的體會和認知。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