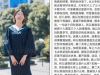19歲女生李同學因為班主任老師性騷擾患上抑鬱症,最後選擇了跳樓輕生。在這個案件里,我們除了指責班主任和圍觀跳樓的看客,更應該回溯李同學為自救做了哪些努力。
更為悲劇的是,她的每一步都走對了,卻沒能換來本該被救贖的結局。她的死是從班主任到學校到公權力機關到看客的一次集體合謀。
我沒有想到李同學遭遇班主任性侵害這件事,居然是以這樣的形式被傳播開來。
兩年前,這位19歲的中學女生遭遇了男性班主任吳老師的猥褻。精神狀態非常差、曾經兩次自殺嘗試服用藥物自殺的她,在爸爸的陪同下到警局報案。而當時這名老師僅被行政拘留十天。
這個處理結果出來之後的同一個月里,李同學再一次嘗試跳樓自殺。她和爸爸開始嘗試向檢察院申訴,希望這名猥褻學生的老師能夠受到刑事處罰。
從刑事立案到檢察院認為「情節顯著輕微,決定不起訴」的這7個月裡,我們不知道已經被取保候審的吳老師做了什麼動作,也不知道傳聞中校方提出35萬元私了的操作是否真實,我們只知道,在這期間的今年年初,李同學第四次自殺,未遂。
這些聳人聽聞的情節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輿論關注,直到李同學在看客們一片瘋狂的「快跳啊」歡呼中縱身跳下高樓,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也許我們應該在譴責圍觀看客的冷漠和醜陋之外,思考一個問題:是否因為針對女性的性侵案件越來越多且嚴重,所以這種案件已經不能激起公眾的憤怒,以致於這種案件只能因為更不堪的國民性的暴露,才能被傳播、引起巨大的輿論關注?

我不喜歡討論國民性、群體道德這種話題。因為它總與一種抽象的群體心理學、行為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很容易就掩蓋了「世風日下」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人的行為和其所處的社會結構、和其社會關係緊密相關,誰也沒有像活在真空玻璃罩里抽離具體社會情景做出ta的決定。
當我們在譴責圍觀群眾道德淪喪時,一來我們並不知道這些人在圍觀時是否真的對李同學遭遇的性侵事件有所了解;二來,ta們也陷進了一種對秩序偏執地崇拜的敘事中去——你在公眾場合選擇結束生命,你在給社會添麻煩,你活該被圍觀人們指手劃腳、噓聲唾罵。
這種敘事方式在最近幾年尤其火熱:為了逃票翻牆進入動物園被老虎咬死的遊客、高速路上下車被撞死的女子……難以被理解的行為一律被大家看成一種對安穩秩序的擾亂。而跳樓自殺,則常常被主流話語敘述成「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生活,於是當眾撒嬌表演,給社會添麻煩」的行為。
大家在唾罵這種「給社會添麻煩」的行為時,也許在當場那個時刻能夠得到一種自我安慰的快感:因為ta(自殺者)管理不了自己的生活,或者ta做錯了什麼事情,所以ta才會遭遇厄運。而我自己因為反對這樣的行為、唾棄這種行為,而且我也許更有才智或者能力去處理侵害,所以不幸的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尋釁滋事」這種刑事拘留並不會讓這些瘋狂的冷漠和消遣消失掉。當人們在日常公共事務中缺少參與的機會、無法消化對社會問題的不滿時,他們只能用這種畸形的方式把戾氣表達出來。「別做傻事,任何事總有正確的解決方法」成為了大家自救式的幻想。
那麼,這位19歲的女同學,在遭遇了性侵害之後,在自殺之前,到底做錯了什麼?她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沒有。
她每一步都做得很對。在事發後她主動告訴了自己的爸爸,並沒有因為羞恥或者恐懼而把這份不平埋在心底——這是信任家長,積極溝通的表現。
遭遇了性侵,她心裡非常難受,於是向學校的心理老師求助,主動尋找方法使自己好過——可是心理老師卻簡單粗暴地把性侵施害者吳老師叫到她面前,對她進行了二次傷害。
在爸爸的陪同下,她勇敢地走進了警局,講述了事件的經過,她勇敢地拿起筆,控制住了自己的痛苦,寫下了控告信——可是最終這個猥褻她的男人,只是被行政拘留了十日。
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她積極配合治療。她知道自己要吃藥,吃了藥會睏乏,但還是不封閉自己,回到學校繼續學習——可是校長並沒有如她期待給她一個公道,只是像哄小孩一樣表示希望她返校上課。
因為病情和藥物,她沒法繼續學習,可是她沒有自暴自棄,還是在百貨大廈找了導購的工作,努力把自己的日子過下去——然而,檢察院並沒有起訴這位吳老師,這也許成為了刺激李同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吧。
她努力地、積極地做對了那麼多步驟,可是她卻發現自己的生活並不能由自己掌握——積極報警,法律卻沒法懲罰性侵她的老師;積極求助,學校卻沒法還她一個公道;積極控訴,爸爸的身體卻日漸不適;積極治療,自己的病情無法通過藥物馬上恢復狀態……
一切都不在她的掌握之中,整個社會合謀起來施加在她身上的壓力和傷害一次又一次使她的命運失控。本來應該保護一個年輕女學生免受性別暴力傷害的校方和公檢法部門,都一次一次地辜負了她。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樸素道理,被發現根本無法應驗在自己身上。任何的努力都指向了不確定和失敗。
而自殺,也許就是唯一她能確鑿確定的、做了就必然導致死亡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她能自己決定的。
到底還需要多少鮮活生命的消失,才能撼動這個以剝削女性身體為樂的腐朽世界?又有多少次這樣沉痛的教訓,才能讓人明白,個體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中遭遇不公的時候,她們的抗爭有多麼困難?
甚至,她們需要的也許不是圍觀群眾的同情心,也不是什麼公序良俗——她們需要的,也許只是李同學在控訴信中的最後一句訴求:我只求,能還我一個公道。
而這樣的一個公道,絕非我們所處的這個無處發泄戾氣,只能消遣苦難的世界可以給予的。公權力應該把重點放在防治性侵害的制度建設和執行上,懲罰施害者和不負責任的教育機構,而非只能跟著時事熱點,忙著刑拘圍觀叫好的看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