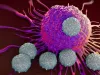今天看了洗版的《我不是藥神》。說實話,對於這部不算精美不算完美的電影,我沒咋笑,也沒咋哭,它能洗版,我覺得有些詫異。
不是我心硬,是我見到的現實,比這還要硬。
我畢竟陪過患癌的家兄近兩年,一百多次呆在癌症病房或手術室內外,見過更慘痛的畫面,與更多更複雜的社會百態。
作為攝影家,我完全可以紀錄一部生死線上的情景,作為記者,我完全可以寫一篇第一人稱長篇特稿。何況,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考驗,用盡全部心力。
癌症哪怕只是醫藥問題,都值得寫,何況,在我看來,它更是個社會問題。
我沒拍沒寫。在那時,我只關心親人的命,那之後,我不敢回顧。我其實有詳細的醫療日記,但再也沒回看過。沒救回,作為資料的影像與文字白費了。沒有創作。
但一直想說些什麼,好像這樣才對社會負責,畢竟我們多了一點點經驗教訓。現在就隨心說說吧。不夠嚴謹——反正人類在癌症面前還沒能力嚴謹。
片中的白血病,還算有特效藥,雖然正版格列衛要兩萬元,可我陪伴的肺癌這種病,活下來的都是手術能割掉的,中央型的只能靠藥,可以籠統地說:沒見過能根治的藥——從化療藥物到可以從印度走私的靶向藥——只有能延緩的藥,基本一兩年是個死。最有效的有廣譜性的比如PD1,也只能給大約四分之一的病人延續幾個月的生命:一針四萬元,一個月三四針。
絕望在於,窮人死得快,富人也活不長。
家兄病發時,是在家鄉做醫生的中學同學查出來的。隨即同學們聚餐,他也急著回廣州再查,我哥笑著對我說:他們氣氛凝重,好像我從此一去不復返似的。
事實上,同學們是對的。有不少醫生得癌放棄治療的新聞,因為醫生知道,人財兩空,多數情況下是你與癌症鬥爭的最後結果。
我哥是成功的商人。當時是2015年初,我這才關注這一社會現象:僅僅在他的同事圈子裡,就有另兩位也得了肺癌,一位年輕的父親,一位年輕媽媽,都才三十多歲。還有至少兩位乳腺癌一位子宮癌(有人有了也不會說,尤其老年人)。我哥那圈子也就幾百人吧這樣,因此我粗略估計,在同一時間,我們這個社會,得絕症的大約百分之一,算上乳腺癌子宮癌這種好治一點的,還不止。
這麼多,這麼年輕,難道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嗎?以前沒這麼多。記得省中醫院芳村分院腫瘤科負責人鄧先生,對我說過:他八十年代在醫院實習時,來一個腫瘤病人,大家都會去看稀奇,是很珍貴的。
現在,他說,中醫院都有腫瘤科了,縣級以上醫院都有腫瘤科了。
我因沒有關注過身邊的癌症病人而後悔,因為我失去了得到治療經驗的機會。我回想一下,我工作的單位,有過四位我認識的因癌症而迅疾去世的人,多是我的恩師,決定過我的前程:
《現代人報》一把手易征總編輯,去世時約64歲;前《羊城晚報》社長、時任廣東省文化廳長的曹淳亮,去世時約50多點; 《新快報》社長許挺斐,去世時40多。
這個名單竟然都是大佬。最後一位是去年,車隊隊長水哥。他其實也是大佬,車隊的老大也是老大。想到我哥也是他圈子裡的老大,我想,我不做老大也挺好,不求升職了,太操心了。
失去的多是國家的精英啊。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嗎?
但社會似乎沒覺得這是個問題。得了病的人,仿佛已是被遺忘的社會的另冊。我明顯感到國民都在賺錢拼命的路上,來不及看一眼要倒下的同伴。
比如,我們在各種慶典、活動上,會看到大量的志願者,可癌症病房近兩年,十來家醫院,我沒看到過一個。對中國的志願群體,我有了深深的懷疑。如果說有近似的話,那是廣州一家部隊醫院的老清潔工,她看上起那麼平凡,但有基督信仰,知道家兄也是,便在打掃後,跪在病床邊為他禱告。
比如,我這一行,紀實攝影家,拍麻風病的很多。其實麻風早在幾十年前,就有了特效藥,療效幾近百分之百。但沒人拍癌症。為什麼?可能是因為麻風病人長得怪,又多生活在荒野孤島中,容易出影像。看來得病也要得個有傳播效應的病。傳播有時很功利。
被遺忘也罷了,但更讓人絕望的,其實癌症病人在走向死亡的路上,會感覺到社會還要補上一刀。
簡單說,癌症病人的利益沒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這就是《我不是藥神》提示的現實:智慧財產權,國家面子,資本利益,都比生命重要。
《我不是藥神》能引起巨大的共鳴,是不是因為它少有地展示了一次老百姓的生活,並告訴你:我們的命也很重要呢?
從體制上說,是的,我們各大醫院都有了腫瘤科,但並沒有讓癌症患者得到超出普通病人的照顧。照樣排隊,照樣找關係等病房,化療三天就請你離開——得癌症的又不止你一個。
我哥初治時,三天就讓離開病房了,可第二天脈搏就狂跳,很是危險,幸虧我愛人還有點經驗,及時提醒,便奔向一家部隊醫院,才急救回來。那裡病床緩和一些。
我要傳遞一個經驗:治癌路上處處是陷阱。在我國,沒有很細緻的針對個人的醫療,必須認識較多的醫生,綜合起來下結論,交給流水線上的醫生,我認為,早就沒命了。
有次爭取到最權威的腫瘤醫院會診,看他下一步打哪種化療藥。讓我們亮了一下相,專家們就請我們出去了,討論完事居然忘了我們。我逼住年輕一點的主持醫生問,他遞給我一張紙條,寫著藥名,同時說:其實都差不多,都是這麼回事。
這個藥讓其他醫院我們的主治醫生們驚奇,這個藥並不對。我們沒聽他的。這種會診,對病人心理生理都是個打擊。
折騰人。癌症病人得到的禮遇,跟任何普通患者一樣,醫生多是不耐煩的,你得到的時間不比治一個感冒多,而這是在決定生死啊。當然,醫生也可憐,累到他們也和病人一樣絕望。
這難道沒有一個解決方法嗎?讓醫生和患者都能靜心,有尊嚴,有力氣,來共同面對?
你說做不到吧,可美國日本治癌的報導,為什麼描繪得就完全不一樣呢,甚至讓你如沐春風?我後悔沒安排親人去美國。
體制或政治或利益,決定了他們用藥也比不上美國病人。《我不是藥神》是想用便宜藥,而現實更多是,就算你有錢,你也用不上美國的救命藥。就是不進口,理由很多。而國內山寨,也一時不成功。就是進口了,價錢如何,大家百度。
這對人的國家信念是摧毀性的。
說說美國的藥物PD1 (俗稱)吧,這是明星抗癌藥,不傷身。在治療當年秋天,病情又急劇惡化,親戚都提醒我準備後事了。這時,我想起他在廣州某院一位主治醫生的指點,說是最後不行了試這個。但這個國內不賣。好在香港有位邵醫生有得賣,合法正版的,近四萬元一次成人用量。行,做好資料傳過去,邵醫生同意賣,我們去香港取就行,比印度快多了。取過來醫院又不敢打,還好,部隊醫院敢於探索,打了。一針就起死回生,兩三針人就快能正常生活了。這藥讓家兄延長了十個月生命,已屬奇蹟。同期該藥終於在中大腫瘤醫院藥試,試了十來個病人,沒一個成功的,比較起來,我哥是幸運者。
同是中國,為什麼香港能, 大陸不能?一國真是兩制。
美國的各種新藥還在上市。我們沒有。但通過病友了解,鄰市有山寨的。於是就像電影一樣,我等在東風路邊,等到一部車,我交一兩萬元,人家給一堆粉末和幾十個空膠囊。說是從美國回來的醫學專家,知道配方,自己配出來的。
就這樣兩次吧。也沒什麼效果。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那粉末是不是只是「張長林院士」賣的哪種,我們是不是被騙了。可我們別無選擇。
最讓人糾結的,是圍繞癌症的各種療法,遊說這些療法的,有明目張胆的貪婪,也有難以察覺的自大。我們經歷的,正規的西醫與中醫院之外,還有:
針灸放血療法;台灣某醫的原始點療法(盛行,以用姜為主);台灣某專家的營養療法(以吃幾種蔬菜為主);生物免疫療法(沒錯,就是魏則西那種,我們進行了兩次,沒有療效且貽誤時機);偏方——比如土灶老泥加蛤蟆什麼的,弄來還真不容易。
其他玄學的宗教的就不說了。那放血法最早,直接破壞了家兄的身體基礎,耽誤了治療時機。而且那位女「醫生」還借了家兄十幾萬元,家兄的同學也贊助給她五萬元。後來,我哥病逝後,她也許出於愧疚,還了五萬。
我還在等著她還錢。不急,我等。她自稱也是基督徒。記得我哥,一位極寬容的人,在病重時對我說過:她是有罪的人。
我很想去見台灣的兩位專家。說實話,他們在大陸的信眾太多了。以我的人生經驗,一眼可以看出,他們究竟是有癔症,還是有罪。
我很想去問問台灣的衛生部。我確實讓人當面問過原始點總部,他們當面的回答,是不敢說能治任何大病的,可網上是另外的宣傳。
就有這樣一些人,一些勢力,敢發這種財。你耽誤別人救人,就等於殺人。你如此發財,更等於搶劫臨終者。給臨終者補刀的社會,讓他們在生存絕望之外對人類絕望,無異於地獄。
面對生死,既要有良心,也要有理性。我說幾條忠告,一家之言,但是我自己的理性推斷,稍為靠譜的如下:
預防:癌症難以預防。少喝白酒可以減少肝癌,我只能肯定這一條。(像抽菸楞往死里抽的導致胸腔出問題就不說了);最好多運動,十來天流一次大汗(這是一種太強烈的預感)。
治療方向:正規醫院,西醫。中醫我不敢說。其實中醫院也靠西藥在治癌,這是肯定的。上述其他方法都是扯淡。
治療的注意事項:
1.家人要介入,要多少掌握相關知識,從一開始就要加入病友QQ群,幾天下來就專業了,每種病都有它的群,很容易搜到。同病相憐,很容易交上朋友,都是真話;2.化療等重要方案,可去兩家以上醫院會診,醫生意見不同時,投票決定(我最多有9個全國的醫生參與,不過有時真理是在小部分那裡);3.不要相信寫書多或演講多的明星醫生,相信一線中層醫生,裡面有高手;4,化放療悠著點,見好就收,不求奇蹟,但求周旋(一過度就擴散人也虛弱);5,實在不行時去注射PD1,雖然貴,但效果有沒有一針看得出,也沒副作用。
至於目標,中國的治癒率,就是說活到第五年的為三成。除了那些能動刀的,一般能多活幾年就不錯了,不敢抱太大希望。
費用,只能說,往往一種藥一兩次無效,就該換了,不該繼續費錢了。準備賣房吧。這是很殘酷,但一般中產,在城裡往往有兩套,賣一套也就差不多了。命重要還是房重要,自己掂量。如果你能與癌症鬥爭那麼久,那麼你的能力意志力會提升的,用在賺錢上,賺到新的一套不難。
治病,能去歐美的就去吧,也給國內沉重的現實減負。總之,看了這部電影,還有最近的一些事件,感覺中國不容易。一個正常的社會 ,不該有這麼多絕望者,更不該給絕望者補刀——想想是誰讓那個女孩最後跳下來?
中國的路還長,比中國足球還長。也許路太多,等於沒有路。
說了些悶了兩年的話,也不準備再說了。只求對病人與家屬有點益處。最後向幾位我敬佩的醫生表示敬意,我不再找你們是害怕一起回顧那永遠無法完全明白的病案。那只有上帝知道。在腫瘤科,沒那麼強的醫患對立,而是大家是戰友,有同樣的絕望:病人絕望於活不了,你們絕望於治不活。你們的事業成功感能有多大,可以想像,但大家一起在做西西弗斯,足夠悲壯,其中人的光芒,那是萬丈!
記得我哥過世後,還有一枝PD1,我們放著。那位醫生也在等,比如老人可以算了,終於有一天發信息來:有一位年輕的女博士,是山窩裡飛出的金鳳凰……
給她吧。正好快過期了。送過去了,然後醫生再也沒消息。不用問,沒救活。
前面說過的,我哥圈子裡的三位肺癌,都在這一年走了。其中小田,是很陽光很好玩的一個人,和我哥一起治過。我也建議他用PD1,老鄉圈子裡也捐了錢。每一次微信問他,他都說,長江哥,疼那。總是比上一次更疼,弄得我不敢問了。再問,是2016年春,是他老婆回復的:長江哥,小田已走了,沒用PD1,將錢留起家裡。
他比我哥早走半年多。他在家鄉治,便宜些,報銷方便些。我呆在這個圈子裡,常常在告別。在群里,常常就有人說:各位別費心了,我父親(或老公或老婆)昨天已走了。最後是我告別:8月,家兄走了,感謝大家,請繼續戰鬥。
然後退群。病友群專家群(還是國際的)。你們見過這驚心動魄要命的群嗎?咋沒記者寫這些故事呢?
我常常想,如果病的是我,我該怎麼著?我想,我沒我哥那麼多錢,也沒他的堅強意志,我略治一下,見勢不對,就會安排好家事,請求大家同意我去遊歷一番,搞搞創作,留下點作品。也許有意外驚喜呢?好像是高爾泰,查出肺癌後就到西北去寫書,書寫好了再查,沒了。
這樣的事是有的。癌細胞也有它的生死的。有時不治,它卻自殺了。
回想呆在醫院腫瘤科室的日子,我現在才覺得穿越:當時身邊的人們,不出半年,大多會陰陽相隔。這樣的場景,難道還不悚人嗎?還不該是個社會熱點嗎?或者這個社會在有意避開它?
感謝這部電影,讓癌症進入公眾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