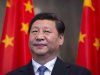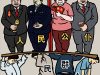這本書的德文版在四年後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並且修訂擴充。實際上,其後阿倫特這本書主要影響在社會及媒體,在不了解極權主義問題的人那裡,而在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專業領域中、在學術界,卻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獻。而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後展開的極權主義研究它的影響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說的第二個問題,認識論問題。
阿倫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認識論基礎無疑廻然不同於普普為代表的文藝復興後復興的希臘式的哲學探究。研究極權主義及阿倫特的專家認為,阿倫特的這本書是一本各種題材的雜文的拼湊,它沒有統一的方法,更沒有統一的思想研究基礎。就這本書的成書出版過程,及在當時討論時阿倫特自己的說法,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阿倫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採取了一種似是而非,環顧左右而言其它的迴避的方法。據阿倫特自己說,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為她感到一種外在的壓力。這本書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時候,在美國的書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國出版的書名則是《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閱讀此書中文本的讀者是否注意到,這本書實際上並沒有回答極權主義的「起源」是什麼。據研究阿倫特的學者說,這點阿倫特自己是意識到了的,她無法決定到底是什麼題目,但是由於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國和英國用了不同的書名。
對此,阿倫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號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承認:在結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遠遠少於她所想要的。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修訂的德文本的時候,她刪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結論,再次擴充了關於蘇聯問題的文字,同時把書名改為,《極權統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後,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國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訂,書名則改用了美國版的書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刪掉前言和結論後她特別為德文版重寫了前言。在這個前言中她說,「極權主義起源於歐洲民族國家的衰落和解體,以及現代群體社會(Massengesellschaft)的無政府主義的興起。」
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不僅她的這個對於「起源」的解釋言不及義,經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權統治,這個說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區別的。集權統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權力,但是卻還不是極權主義所獨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徹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權統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經是納粹黨員的德國政治學學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後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開始出現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描述的是一種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在一個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新的現代專制形式。它類似於政教合一,但是卻沒有更高的能夠約束人的神的存在的專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權統治、集權國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權力的集中,它並沒有涉及到一個社會的價值和倫理問題,或者說涉及徹底的對社會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統治及改造。
阿倫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對於此書所做的修改,應該和她在冷戰初期匆匆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一樣是有原因的。因為此間,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五四年蘇聯作家愛倫堡發表著名的《解凍》,緊接著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事實上,對於蘇聯共產黨政府的極權專制,阿倫特始終不願意把它和希特勒納粹的極權專制等同並論,她更願意稱蘇聯為「史達林主義專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則甚至公開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
關於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解釋之所以如此模糊、游離不定讓我們看到,正是她的認識論基礎、方法導致了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這點進一步告訴我們,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不是近代啟蒙思想,自由主義傳統的產物。
其次,由於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論,有時候是思辨,有時候是一種心理推測,有時候是現象堆積,有時候是觀念羅列,著名的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甚至在給她的信中說,她在這本書中使用了「情緒性方法」,做了過多的判斷。因此這本集成的文字,從根本上可以說「不是研究」。而對於她的「看法」,如果不說這些看法是否是錯誤的,那麼至少可以說她既沒有說清楚她所主張的極權主義的概念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極權主義的起源。而這個事實就註定了不僅讓她的這本著述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對於學界的「研究」影響甚微,而且在未來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也肯定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阿倫特的這本書由於它的卷帙,由於它出版的時間,至多它可以作為一種平行於那一時期出現的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研究的歷史現象,出現在思想史中。
3.極權主義研究的深化——世俗宗教問題研究的認識論基礎
3.1.極權主義研究的第三階段:世俗宗教問題:
對於最近二百年來歐洲,甚至可以說西方給世界帶來的災難的研究的第三部分,一個已經或者說還正在展開的部分就是對於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文化社會學的研究。這就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後被弗格林(Eric Voegelin)和阿隆分別從不同角度,即不同的出發點提出的政治化宗教(politisch Religion)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後來弗格林和阿隆都不同程度地進一步使用了「替代宗教」(Ersatz Religion)、「世俗宗教」(Säkular Religion)來代替政治化宗教一詞,阿隆甚至說,他感到用「世俗宗教」來替代「政治化宗教」的說法更為恰當。他公開聲稱,在政治學思想領域中,他的主要貢獻不是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而是對於世俗宗教問題的提出。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我已經開始陸續對中文界介紹,不久我還會有一篇如以前對於極權主義其它問題的研究那樣的有關這個題目的專門文字。
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和納粹「產生於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居然對於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不僅睜眼不見,而且在有那麼多名家進行了研究的文獻面前還要爭論。
事實上,極權主義產生於歐洲文化歷史,這個問題不僅是一百年前面對蘇聯共產黨政權、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歐洲及西方社會的主流學界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而且是經歷了八九年的歷史性的事件後再次陷入危機的西方,時下繼續在更為廣泛地、深入地展開對此研究及及討論。
和一九三〇到八〇年代的五十年相比,最近三十年,對此的研究特點是越來越具體化、經驗化。為此,德國學者邁爾(Hans Maier)不僅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主持了由大眾汽車公司資助的研究項目《政治化宗教和極權主義》,並且為此已經出版了三巨冊的文集,從理論上、歷史上、案例研究上,第一次全面描述這個研究的歷史現狀,而且他自己也從多方面研究了極權主義和基督教的關係。邁爾已經出版了《政治化宗教》、《宗教的雙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現代政治化宗教》、《沒有基督教的世界將會如何?》。
布拉赫先生的學生
在布拉赫學派的創生地,德國研究極權主義的重鎮波恩大學,一系列詳實全面的對於這一問題研究的書籍以及博士論文由布拉赫教授奠立極權主義研究專業叢書,「極端主義與民主系列叢書」(Extremismus Und Demokratie)中湧現出來,例如:
馬庫斯·胡特訥爾(Markus Huttner)的《極權主義和世俗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äre Religionen,1999);
弗爾克爾(Evelyn Völkel)的《極權主義國家—世俗宗教的產物?》(Der totalitäre Staat- das Produkt einer säkularen Religion?,2009);
科羅岑-馬德斯特(Ulrike Klotzing-Madest)的《東德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種政治宗教?》(Der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DDR- Eine Politische Religion?,2017)……。
與此同時,義大利著名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學者根提爾(Emilio Gentile)出版了《作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2006),全面地分析了最近一個世紀世界政治變化與基督教文化及社會的關係。
對此在這裡,我要提醒中國讀者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裡所有提到的、在這個研究中所使用的「宗教」(religion)一詞,幾乎都可以等同換成「基督教」一詞,這樣可以讓人們更為準確容易地理解。例如邁爾研究的實際是「政治化基督教和極權主義」,「基督教的雙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的現代政治化基督教」。因為邁爾及所有這些學者所說的「宗教」就形上學的前提來說根本不能夠用佛教、道教來替代「宗教」這個詞。而這就更理所當然地讓人們看到,時下有人居然如此使用的「儒教」來指謂「儒家」,那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極為荒誕的事情。
3.2.在此,對於這個問題,我再次特別強調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首先基督教和當代極權主義的關係的研究在西方已經是一個經驗研究的題目。沒有對於概念如何清楚地定義、區分劃界,沒有具體的事實變化和內容的描述,就不能夠進入這個領域討論。目前流行於中文世界的那類的意識形態化的談論,在學界已經毫無立錐之地。
例如德國的邁爾提出,表面上看來毛澤東雖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也對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人們可以通過具體的研究,即毛澤東的語言方式、隨之而來的語錄出版、存在形式,檢閱儀式,發動運動的方法,政黨組織以及運作都是基督教式的。
德國學者羅爾瓦瑟爾(M.Rohrwasser)則更是具體地研究了共產黨社會的語言很多根本就是直接沿用的基督教宗教傳統中的語言,例如異教徒、持不同政見者、異端分子、叛徒(Ketzer、Dissident、Häresie、Verrat……)蛻化分子、清洗等等……。
弗里德里希則在對魏瑪共和國、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要實行極權主義首要的就是粉粹傳統社會的結構,各方面讓它基督教社會化。他直接指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的建立、北伐完成的就是這個過程。中國沒有這個過程不可能有後來的極權主義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及鞏固。而幾乎絕大多數極權主義問題研究者都針對共產黨社會依然需要和西方整體類似的表面的政黨制、表面的議會存在,即中國到如今還要裝模作樣地要例行地開所謂兩會,可以完全說明極權主義的產生和存在必須要在基督教社會的這種教會式的結構形式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德國另外一位自由主義大師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極權主義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對一切文化傳統的存在,反對近代人權價值。事實上這個反對一切其它文化傳統的一元論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論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結果。共產黨社會沒有神,但是卻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點繼承了下來。然而,這種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結構的高度的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的特點,卻絕對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不是儒家,甚至也絕對不是道家乃至佛教所可能具有的主張。
當代中國人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看不到傳統中國專制和當代極權主義專制的區別,妄談儒家,其實正是真理部對於這個社會的精神的改造的結果,那就是,他們在看任何以前的著述,都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了。其實對於這代人來說,即便是去看看距離我們不遠的,出生在傳統教育下的那些研究者的文獻,即梁啓超、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乃至當代的余英時、許倬雲先生的著述,就可以知道如何理解歷史及文化,如何看待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及思維方式,以及它們和中國文化傳統思想的根本區別。而造成這代人看不到這一切的,則又要回歸到本文作者強調的——認識論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