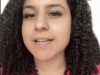一個晚上,13個小時,接17單,能賺1800多塊錢。
這是鄭雷做全職代駕的一年半時間裡,最好的戰績。那天,他從晚上7點半一直開到第二天早上8點多鐘,回到家後一下癱在了床上,「身體大腦累得不行」。這一晚的經歷對他來說像剛吃糖的小孩一樣,嘗到了甜頭,「如果每月能有3-5天這樣運氣就好了」。
這位35歲的代駕師傅,曾是一家建築公司的採購員,5年朝九晚五的生活讓他感到疲乏。2016年公司解散,他開始全職做代駕。一輛電動滑板車,一部手機,就可以隨處開始,他很享受,覺得來去自由。
2017年春節從安徽老家過完年之後回到上海,鄭雷隱約感覺到,新一年的單不是特別好接。平台上的代駕司機越來越多,蛋糕越做越大,每人分到的卻越來越少。現在一晚單量在7單左右,賺個500多塊錢,他已經知足了。
某代駕平台全國大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2017「99」全國酒駕安全形勢報告》顯示,從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9日,全國代駕使用次數達到2.27億次。報告分析師認為,按全天平均客單價計算,全國網絡代駕產值破百億元。而在2018年「世界盃」期間,報告統計發現,代駕使用超過1500萬人次,零點之後的訂單增加了47%。
這百億代駕市場背後,是無數發生在黑夜裡的故事,而代駕司機的那部分,有關等級和尊嚴、生計和漂泊。
接單
只有在接單的那一刻,師傅們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代駕平台會按照司機登錄時所在地點,就近派單。
剛開始做代駕時,鄭雷對這種「未知感」充滿了期待和好奇。「上海這麼大的地方,不做這一行,有的地方肯定沒去過,現在有可能哪一單就把我帶到那個地方去了。」
但時間久了,新鮮感也消退了,現在接單時他只想著不要離開寶山區——鄭雷家住寶山區吳淞路,他對這塊片區輕車熟路,哪怕跑到較偏遠的劉行鎮或水產路,也不用導航。
運氣好的時候,一晚上都在寶山來回,最後送客人回家時,順便也把自己給捎回家。
出發前,他會先檢查好隨身攜帶的裝備:代駕公司發的挎包里裝著手機行動電源和駕駛證,這兩樣很關鍵,行動電源能保證手機持續在線,駕駛證則是自己資質的證明。
保溫杯里的熱水要提前裝好,不論春夏秋冬,鄭雷每天都會帶一杯熱水,抵禦深夜的寒涼。此外他常年備著雨傘,「萬一下雨呢?方便一點。」
在公司上班的5年,他覺得最麻煩的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現在做了代駕師傅,處理的是流動的人際關係,「一切要對顧客負責」。
兩隻車把手一收,接著折座椅,一疊。10來秒的功夫,摺疊車就躺進了客人的後備箱。有些客人會介意摺疊車把後車廂弄髒,鄭雷二話不說,從包里拿出車墊,鋪在客人的後車廂上,然後給客人回一句:「您等一等。」
「滴滴滴」晚上7點左右,手機里傳出客戶叫單的提醒聲。鄭雷響應車主的時間很快,完成線上接單,他會即刻給客戶打個電話:「您好!××代駕公司,很高興為您服務,請問您現在具體位置在哪裡?」
完成接單的動作只需要8秒。而8秒之後,是一場不確定的等待。
「等」對於代駕司機來說是必修課。客人們從提前下單,到走出娛樂場所的大門,中間要花多長時間,一切未知。即使走出了大門,也可能心血來潮再去k歌打牌,一整夜的時間便在等待中過去了。
司機們圍聚在一起等待,年輕一些的打「王者榮耀」打發時間。鄭雷35歲,對遊戲沒太大的興趣,他會坐在自己的電動滑板車上,逐條打開微信語音,聽群里代駕們交流彼此的單子。
「哈哈哈哈,你這一單怎麼跑到崑山去了,那多遠啊!」群里有人今晚「運氣不佳」,接到一個崑山的單子,估摸著今天就只能做這一單了。
客人的電話還沒打過來,門裡的世界也許正熱鬧著。鄭雷謹守行業規則,只能等——銷單的主動權掌握在顧客手中。在鄭雷做代駕的一年半時間裡,等單的最高紀錄是4小時。
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過了午夜12點,客人還沒出來。12點之後,10公里以內的起步價提高到99元,「等待每15分鐘10塊錢,再加上起步價的99元,也能賺好幾百了」,他一邊等單一邊安慰自己。
超過預約時間,司機們通常會跟客人確認,但有人晚上的活動一場接一場,為了「好評率」,司機們很少催單。
那次等了四個小時,鄭雷終究等到了客人。但假如沒有等到,「你也不能跟客戶說你取消了,害我白等這麼長時間,你給我錢,這是不可以的。」
在2018年9月底,公司加收取消訂單費用前,「白等」的代價需要司機埋單。
在客戶面前,鄭雷儘量收斂自己的情緒,他擔心過激反應引起客人的投訴,進而招致平台的降分處理。對他們來說,積分和好評是晉級的關鍵。
等級
鄭雷的等級是「鑽石」,這是級別最高的一檔,享受系統優先派單的特權。
他所在的代駕公司,把司機的級別從高到低劃分為鑽石-鉑金-黃金-白銀-青銅5檔。公司規定,積分必須達到35000分才能獲得鑽石級別,而升級最關鍵的除了接單量,就是好評率。
鄭雷把代駕公司的「11條規定」設為手機壁紙,時不時拿出來看一下,提醒自己。他如履薄冰地守著自己日積月累攢下的信用分,這直接關聯到他的收入。
鄭雷一個月全職跑下來能賺1萬2到1萬3,而「青銅」等級的司機賺的錢只有四五千。
高等級與高收入通常意味著更高的工作強度,和更少的睡眠。鑽石級司機王新海48歲,入行不到兩年時間,累計代駕次數超過2000次,扣除平台信息費前的總收入超過16萬元。
從2015年9月開始,他每周全職代駕七天,每晚從七點開始連續工作12個小時以上,2016年的「年三十」也沒休息。
他本不屬於這個行業。從山東淄博來上海打拼近20年,他從普通司機到創業開了家小物流公司,買了房,也在「魔都」立住了腳。兒子畢業之後,他把公司交給兒子打理,「在家閒得實在著急」,經朋友的介紹做了代駕。
「不累,這比年輕時候開集卡(貨櫃卡車)輕鬆自由多了,集卡有時候開一夜,累了只能歪到座位上休息」,王新海是個勤勉的司機。
與王新海從容篤定的職業選擇相比,陳坤踏入代駕行業更像是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
陳坤是「90後」,2011年來上海前,他在江蘇老家乾的最後一份工作是理髮師。這是他幼時嚮往的工作,「哇,那男男女女頭髮搞成那樣,多帥啊!」
整日跟染髮膏打交道,他手上的皮膚現在「一碰到頭髮、碰到水就疼,跟針扎的一樣」,堅持了兩年,最後還是放棄了。
7年的時間裡,他先後做過廚子、服務員、專職司機和保全。最窮困潦倒的時候,還沾染上了賭博,最終賭得一分錢不剩,還欠信用卡2萬塊錢。
2015年底,陳坤的孩子在上海出生,在產房外,他抽完了最後三包煙,此後再也沒碰過,決心結束這糟糕的生活。
2017年,陳坤感覺終於「走上了正軌」:他白天在某電單車企業做維修人員,到了晚上8點,就在上海最熱鬧的「新天地」周邊,當一名兼職代駕。
兼職做了兩年,陳坤的等級還是青銅,他秉持著「能做幾單就幾單」的「原則」,不主動跟客人拉關係,客人不找他聊天也不主動聊天。
時間久了,他學會了看車,也學會了看人。
最初做代駕,碰到客戶的奔馳皮卡,他「緊張的手抖,生怕給客人的車碰壞。」時間久了,再看到這些車也波瀾不驚了。
喜歡給小費的人開的車價格大致在30-50萬。開150萬的車,給小費的10個人當中只有2個人——陳坤入行一個半月,就總結出這個規律。有時看到喝多的客人,開的又不是特別好的車,他會直接跟客人說:「老闆你看著給吧!」
客人「啪」地一下甩給他100塊錢,問:「夠不夠?」
「夠了,走了呀!」陳坤狡黠一笑,「明明五六十塊錢的,他給你100,你幹嘛要明說這個錢呢!」
遇到年紀輕的人,陳坤覺得他們很有「腔調」,眼神、語氣都帶刺,衝著他喊「過來過來,代駕!」「有的就是讓我做這個那個的,看我們就跟看『癟三』一樣,都不正眼瞧你。」
他更喜歡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中年客人,「性格比較溫和穩重,醉酒了也很少動怒。」這些客人從見面開始,就會喊陳坤「小伙子」,結束代駕時,還會對他說一句:「謝謝你,你辛苦了。」
這讓他感覺到「被尊重」。這種尊重就像冬日的暖流——即使有時在車上跟客人稱兄道弟,陳坤心裡還是有些自卑,「跟他們不是一個層次的,人家開的什麼車我們開的什麼車,能一樣麼?」
王新海和陳坤心態不同,從司機到老闆,再到司機,他並不覺得有落差,「在上海,做老闆還是做司機都不重要,重要的能掙到錢。」
在他看來,服務質量分很重要,「誰的服務質量高,接到的單就多一點。」為此,他謹慎而謙卑地奉行「顧客為上帝」準則,客人的忙能幫就儘量幫,有人為感謝他給的小費,他一直記著。
有一次,王新海冒著大雨幫客人換了沒氣的輪胎。本來80元的代駕費,客人硬是塞給他200。「人家覺得畢竟耽誤了我的時間。其實他也一直在幫我打傘,讓我很感動的。」
夜歸
凌晨1點半,家住上海浦東南路的代駕司機顏路在寶山結束了當天的最後一單。時間掐的剛剛好。他提前10分鐘來到火車站南廣場等待隧道三線公共汽車。
這條夜班線路,顏路已經相當熟悉。公共汽車會在停站後的十幾秒鐘,亮起車燈。車燈照亮了整個車廂——密密麻麻地擠著的,跟顏路一樣的代駕司機。
城市的夜晚很安靜,除了路面上往來的車輛,和夜宵車裡的這幫夜歸人。司機們熱烈地討論著當晚的收穫和見聞:
「我今天遇到一個客人,真大方,給我小費!」
「哎,我今天遇到一個喝醉的人,拽什麼拽奧,吹牛皮吹得,我笑死了!」
這是他們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刻——在無數次繃緊神經、送別人回家後,這是唯一通向自己家的旅程。
司機們都希望最後一單可以離家近一些,遠郊是代駕司機們眼中避而遠之的「雷區」。
有一次,顏路接到一筆崑山的單,結束後,他返回浦東,40公里路,就靠著一輛電動滑板車連騎帶趕,花了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才趕上火車站南廣場上的夜宵線。
即使碰到好心的客人,給他一些返程費,顏路還是捨不得花這筆錢搭計程車。「畢竟賺的都是辛苦錢,怎麼會捨得隨便花出去呢?」
入冬後的下半夜是一天中最冷的時候,顏路必備的行頭是衝鋒衣、手套、護膝、口罩,一樣都不能少,一般的羽絨服無法抵禦冬夜寒風。
在歸家的途中,顏路的手腕和腿部都曾受過不同程度的摔傷。「幾乎每個做了1000單的代駕都會有摔跤,只是輕重不一樣。」
顏路至今做了1489單,最嚴重的一次,他轉彎時與一輛逆行的電瓶車相撞,現在左手腕只要一用力,還能感受到筋被拉扯時的疼痛。
顏路有時會到上海外灘邊,坐著歇一歇。18歲那年,他跟家裡的親戚踏入上海,一邊做生意,一邊在夜大讀機電相關的專業。面對這個陌生而華麗的都市,外灘就是他眼中的「標誌性的風景」。他喜歡獨自去外灘邊走走,但那時還沒有見過12點後外灘的模樣。
現在,顏路已經35歲。在上海的16年裡,他曾打拼到公司科長級別的位置,也曾經歷創業失敗,最終妻子離開了他。為了放鬆心情,「不讓自己想太多」,2015年,顏路選擇了全職代駕。
12點過後的外灘,在顏路眼中看起來「遊客少了很多,彩燈也暗了一些,讓我感覺上海要沉睡了。」他和其他代駕一起,坐在外灘邊一邊抽菸,一邊想著「今晚賺了多少錢呢?要不要繼續跑下一單呢?」
陳坤仍有一種疏離感。晚上回到位於城中村的家,已經是凌晨一兩點。這裡距離新天地只隔著一條街,附近保時捷、法拉利、凱迪拉克等豪車來回穿梭。他見過喝醉了的年輕人徑直躺到在新天地的路口;也嘲笑過從酒吧出來的年輕人,喝大了對著警察喊:「這裡我說了算」的樣子。
熱鬧是他們的。回到12平方米的「家」里,陳坤洗完澡,什麼也不想,倒頭就睡。這個小單間1500塊一個月,還不包括水電。白天他在電單車公司上班,能賺200塊錢。晚上按照平均一單代駕費40元,每晚接三單計算,大概能賺百十塊左右,去掉房租和其他開銷,他每月的純收入大約在6000塊。
這6000塊要拆成幾大塊,其中花在孩子身上的每天就要接近一百塊。陳坤還指望攢點錢,過年帶回老家探親。2018年是他來上海的第7年,他仍覺得,「還沒資格享受這個城市。」
生計
2017年9月底,顏路花了18800元在婚戀網站上註冊了一個VIP會員帳號。他希望通過紅娘一對一介紹,找到合適的伴侶。畢竟在老家安徽滁州,還有兩個孩子在爺爺奶奶身邊。
一年過去,他找到了伴侶,但賺得也越來越少。「2018年一年接的單比2017年少一半多。」原來靠兼職代駕能有三四千塊的額外收入,現在有點困難。
除了單量減少,顏路明顯感覺自己身體不如以前,「有時候晚上沒啥事就出去做兩單,12點就回來了」。他笑說自晚上熬夜做了代駕後,「30多歲腰上就貼了膏藥。」
儘管眼下做代駕能補貼家用,但考慮到未來,這份工作終究無法提供更多保障。
「沒有學歷,也沒有其他的工作經驗,只有在社會上混的本事」,陳坤覺得自己外表雖是「90後」,但始終「跟出入辦公大樓的年輕的90後不一樣」。
他辭去某騎電動單車管理員的崗位,索性代駕也不做了,生活又重新來過。他期待能在「老家給自己安個小家,有輛車,把老婆孩子安頓好,就好了呀。」
陳坤還記得,從老家宿遷,剛來上海時的樣子。「一床被子、兩身衣服、一雙鞋,再帶1000塊錢。」就出來「闖蕩江湖」了。
7年在上海「混」的時間,他終於找到一份有「五險一金」的工作,「給做電影的老闆當私人司機,很正規。」

夜宵公共交通里堆滿電動摺疊車。
(文中鄭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