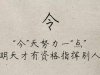有一種說法頗為風行:近代中國所用新名詞多半來自日本,若無日本名詞,現代國人無法說話作文了。此議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里
借詞必需
漢語是一種開放的語言系統,古來即有采借外來語的傳統,早期漢譯外來語不少,如葡萄、茉莉之類。由於近代文化是在中西衝突與融會間生成發展的,故作為關鍵詞流行的近代術語,廣為採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詞身份。
中華文明沿襲數千年不曾中輟,原因之一,是作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漢字詞(名)豐富且詞義相對穩定。今人閱讀兩三千年前的先秦兩漢古文,藉助工具書,領會其意並無大礙。
漢字文化又不斷邂逅外來語,與之互動,獲得源頭活水。如在魏晉隋唐間,吸納大量源自南亞的佛教概念,組成若干反映佛法的漢字新名,諸如法、空、禪、世界、現在、覺悟等,漸成漢字常用詞。
時至近代,漢字文化又與西方文化相交會,知識量迅猛增長,反映新知識的概念井噴般湧現,經由「方言超升,古語重生,外國語內附」等途徑,藉助漢字將新概念「詞化」,生成批量新名,漢字舊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對於此一演變態勢,語言學家王力述評道:「佛教詞彙的輸入,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從詞彙的角度來看,最近五十年來漢語發展的速度超過以前的幾千年。」王力此言之後,又過去40年,其間漢語詞彙的發展更甚於前50年。有人統計,時下每年新增漢字詞達三四百個之多。
由於日本明治維新學習歐美近代文化有成,作為漢字文化圈一員的日本與中國相互藉助,利用漢字翻譯大量歐美詞彙(主要是學科術語),這些新名隨日譯西書傳入清末民初的中國,故近代中國通用的關鍵詞,不少是在中—西—日三邊溝通中生成的。
借詞以新名形式進入借方語言,增加語言數量,豐富語言表現力,是語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現。漢字具有強勁的表意性。每一個漢字不僅是一個音符,同時還具有特定的義位,而且漢字往往一字多義,可供翻譯時選用。意譯詞能發揮漢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內蘊,有時音譯+意譯,如啤酒、卡片、霓虹燈、繃帶等;連音譯也往往擇取音意兼顧的漢字組合成詞,如邏輯、維他命、可口可樂等,以及近年出現的奔馳、黑客、迷你裙、托福之類,在表音的同時,又提供某種意義暗示。嚴復在音譯Utopia時,取「烏托邦」三字,在對音之外,又可從這三個漢字中產生「烏有寄託之鄉」的聯想,以眑示「空想主義」意蘊。這些音意合璧譯詞,是充滿睿智的漢字文化的絕妙創作。
通過借詞以創製新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語言現象。王國維積極評價新語的借取,「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語,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於此者矣。」
百年過去,「新語之輸入」有增無已,而諸如科學、民主、自由、經濟、文學、藝術、封建、資本、教育、新聞、物理、化學、心理、社會、革命、共和、政黨、階級、權利、生產力、世界觀、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等學語的確立,都是在古今演繹、中外對接的語用過程中實現的。這些漢字新名,詞形是漢字文化固有的,詞意大都受中國和西方雙重因素的影響,日本因素也參與其間。故追溯漢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為現代人思維紐結的新概念的生成機制、發展規律,將展開中—西—日文化多邊互動的複雜圖景,彰顯近代思想文化的網絡狀歷程。
語文互動
古代日本從中國進口包括大量漢字詞在內的漢字文化系統,此為確論,無須贅述。一種流行說是,文化傳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間發生逆轉,僅就詞語而論,日本便從輸入國變成輸出國,中國則由文化供應源轉為文化受納處。
此說有粗疏之弊,略做歷史分期,應當作如是說:近代早期(中國的明清之際及清中葉,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傳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國通往日本;至近代後期,日本因明治維新成功,研習西學的水平反超中國,其表現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國從日本引入大量譯介西學概念的新名詞。張之洞稱「日本名詞」,林琴南稱「東人之新名詞」,劉半農稱「東洋派之新名詞」,20世紀50年代語言學者稱其為「日語借詞」。
近代中國使用的反映新知識的新名固然不少來自日本,但稱多半為「日語借詞」,則過甚其詞。筆者以下將陳述此種誇張之誤,絕非要給「詞彙民族主義」張目,不是為了證明「老子先前比你闊」,以獲得阿Q式的「精神勝利」,而是從近代漢字文化史實況引出的結論。
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促成國人「大夢初醒」,決意向強敵學習,自1896年開始派遣青年學子赴日,研習經日本人消化過的西學。此後十餘年,漸成留學東洋高潮。經中日兩國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數以萬計的中國留日學生的轉輸,漢字新語從日本大量湧入中國。康有為1897年撰《日本書目志》,收錄大量日制學名,如經濟學、倫理學、人類學、美學等,一時朝野注目。
清民之際從日本入華的漢字新名,有如下幾類:
(1)音譯詞(瓦斯、俱樂部等)。
(2)日本訓讀詞(入口、手續等)。
(3)日本國字(腺、膣等)。
(4)日文譯語(基於、對於等)。
(5)將中國古典詞原義放大、縮小或轉義,以對譯西洋概念。(如「現象」本為漢譯佛語,意為佛、菩薩現出化身,日本哲學家西周為其注入新義,成為與「本質」對應的哲學術語。)
(6)運用漢字造詞法創製新詞,以對譯西洋術語。
上述幾類詞語有些確乎源自日本,如(1)至(4)類,但數量更大、更為重要的(5)(6)兩類,多不能以「日源詞」一言以蔽之,因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來歷——
(1)源出中華古典
清民之際被認作是從日本入華的大批漢字詞,如自由、社會、科學、衛生、小說、機器、參觀、代表、單位、發明、反對、範疇、現象、革命、共和、講師、教授、博士、悲觀、標本等,究其原本,多來自中國古典詞庫,是晉唐宋明以降從中國傳至日本,近代經日本改造後作為西學譯名「逆輸入」中國的,稱其為「僑詞來歸」比較恰當。因為它們本為中國舊詞,在中土語用已然千百年,後僑寓日本,領受外來文化洗禮,近代作為「僑詞」回歸中國漢語系統。
(2)來自在華編譯、出版的漢文西書
還有一批反映近代學科概念的漢字新名,如植物學、物理學、地球、熱帶、溫帶、冷帶、寒流、暖流、細胞、大氣、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權利、立法、選舉等,曾被誤以為是「日源詞」,實則非也。它們是在明清之際和清末這兩個時段,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以「西譯中述」(西方人口譯,中國人筆述)方式在中國創製的,先後於江戶中後期和明治前中期傳至日本,其載籍為在中國刊印的早期漢文西書(明清之際成書)與晚期漢文西書(清中末葉成書)。
(3)晚清「開眼看世界」中國人的創製
清道咸年間國門初開,一些先進計程車人渴求新知,藉助漢譯西書、西報,撰寫一批介紹西事、西學的書籍,著名者有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魏源編纂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編纂的《瀛環志略》等。這些書籍在介紹外域情事、學術時,譯創了一批史地類、政法類、科技類漢字新名。這批書籍在本國遭受冷遇,而傳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陽紙貴,多次翻印,幕末維新志士吉田松陰稱「魏源之書大行我國」。這些書譯製的漢字新名隨之播傳於日本,日人廣泛使用之餘,還引為譯製漢字新名的範本。如《海國圖志》的報紙譯名「新聞紙」,美國元首譯名「大統領」,皆被日本人採用,通行至今。
總之,上述幾類漢字詞,有的並非「新語翩至」,而是「舊詞復興」,或曰「古典詞革新」;有的不是「日詞入華」,而是「僑詞來歸」;還有不少新名產地在華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轉站。因而,把它們一概視作「日語借詞」,不符歷史實際。從語源學角度論之,必須恢復上列三類詞語的「中國首創」「翻新古典」及「回歸僑詞」身份,並論析翻新始末,輸出與逆輸入過程,考查中—西—日三邊互動間的因革及傳遞轉換情形。
互為師生
我們不應輕忽幕末明治日本發展漢字文化的重大貢獻。近代日本創製一批漢字新名;大量選取漢語古典詞翻譯西洋術語;普及詞綴化用法,如前綴(如老~、小~、第~、非~)與後綴(如~者、~力、~性、~化),又借鑑西式語法,豐富了漢字語用,對白話文運動及漢語的現代化進程起到推動作用。這一勞績必須肯認,卻又不能因此對漢字新名的語源張冠李戴,一概讓與日本。
筆者以為,近代日本對漢字文化發展的促進,主要並不在於提供了多少新詞,而在於終結漢字新名的散漫無序、自生自滅狀態,界定了中國自創、或由日本製作的新名的古典義、現代義、世界義,並使之貫通,匯入學科體系,並通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為漢字文化構築現代性知識系統提供語文基礎。這項極有意義的工作,既非中國、也非日本單獨完成,而是16世紀末以來的三百餘年間,中—西—日三邊互動的結果,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此間互為師生,交相更替創作者與學習者身份,而歐美傳教士在中國士人協助下的譯創之功也至關緊要。
自嚴復等兼通中西語文的譯者出現以後,中國逐漸減少藉助日譯西書,而直接譯述西學,根據英、法、德、俄諸文本譯創漢字新名。日本的「二傳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時代日本新語的效用並未中止,其某些優勢繼續張揚,如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躊躇」,苦心孤詣譯創的「計學」「群學」「母財」「腦學」固然準確、典雅,卻不及日譯漢字新語「經濟學」「社會學」「資本」「心理學」明快易懂,故在近現代中國流行的,少有嚴譯詞而多為日譯詞。
直至當代,日本詞彙傳入中華還在進行中。時下流行的新詞,如「達人、人氣、人脈、完敗、完勝、物流、研修、職場、熟女」等皆為日制詞。
日本譯詞雖有便捷易用的優點,但不應忽略,這些日本漢字詞多半源自漢語古典,或用漢語構詞法創製,皆與中國文化保有深刻的淵源關係。新近一例頗能說明問題。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號「令和」。官方解釋此名是從日本最早的和歌集《萬葉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並序》「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句中擇字組成,並宣稱這是第一個典出日本古籍的年號。這顯然有文化「脫中」用意,但經考索卻適得其反。公元8世紀成書的《萬葉集》「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句,脫胎於東漢科學家兼辭賦家張衡公元2世紀初作品《歸田賦》的「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而張衡又參酌了先秦典籍《儀禮·士冠禮》「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漢字詞彙,多源出中國古典,這是不必也不可迴避的歷史實際,日本近代翻譯西學時創製漢字新語,深植中華文化土壤,這是不可忘卻,更不能斬斷的歷史脈絡。
綜論之,中日之間的語文交際,呈一種互為師生的關係,今人不必作偏執一端的估量。中日兩國協力共創的語文成果,是豐厚的文化財富,至今仍在中日雙方發揮作用,並且構成當下及今後語文建設的堅實基礎。
(作者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