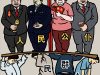那年風波後,王朔說要構思一篇新小說,我問他講什麼?他說:忍術。
是日本忍術嗎?我問。
不是,是中國的。
可中國哪裡有忍術?
他說,中國沒有忍術這種形式,但是,忍的學問卻融進了中國人骨子裡。
這個忍,是忍耐的忍,也是殘忍的忍。中國人不僅很能忍,而且很殘忍,特別是對自己,對自己人,尤其殘忍。
他的一篇小說里有句話,叫: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
在他看來,人死不是問題,活著才是問題,能屈辱地活著,才是真正的王者。
我理解他的表達,他說的那種忍,其實就是一種潑皮牛二精神、滾刀肉精神,或叫阿Q精神,拖不垮,打不爛,不屈不撓,絕不屈服。這也是一個種族生生不息,繁衍下去的理由。
舉目世界,中國人的忍,恐怕是無雙級別。元代,初夜給蒙古占領軍,忍了;清代,剃髮結辮,也忍了。
有人說,那是古代,那是漢人,不能代表中國人。
其實,當代中國人的忍應該還有所超越。你看,三年饑荒,十年艱辛探索,不是照忍?而且,五十六個民族一起忍。
經歷了兩次「活下去就是最高追求」的時代,基本也就沒什麼不能忍的了。
僅僅能忍遠遠不夠,還得會忍,還得把忍變成一種博弈的手段,靠忍來征服敵人,那才是忍的最高境界。
他說他要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故事梗概是這樣:某人比武失敗,不服,但又打不過,於是,跟對方約定,咱不比武了,比忍,對方同意了。
雙方的忍術從比忍耐力開始,忍耐指數不斷升級,中國人始終無法戰勝對手,於是,由忍耐級別升級到殘忍級別。幾道自殘下來,眼見依然無法讓對手屈服,中國忍者一怒之下,拿出終極忍術——切命根子。對方一聽,傻眼了。說:你先。
中國忍者毫不含糊,揮刀就把命根子切了。
對方望之,嚇個半死,立馬表示服輸。於是,中國忍者勝出。
活下去不是問題,能不要命根子地活下去,才是王者。
比自殘,論輸贏,這讓我想起一個群體——天津混混兒。

早年間的天津,碼頭河運昌盛,誰能占住地盤,有活干,誰就能發財。於是,下層社會興起搶地盤之風。但是,天津畢竟是租界地帶,法制社會,有洋巡捕管著,胡來不行,打打殺殺,可能招致租界制裁。如果抓起來關幾年,美好人生就荒廢了,那不划算。
武鬥不行,就來文鬥。所謂文鬥,就是比自殘。不驚動警方,也不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
天津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對決,是在天津三岔河口某處。一塊空地,架起十口鐵鍋,雙方各出五人,跳油鍋「炸果子」。「炸果子」就是炸油條,不過,這個「油條」不是面劑,是大活人。鍋中注滿油,下面用柴火燒,待油熱冒煙,雙方選手猶如點球決勝一樣,輪番出場,跳進去,一個活生生的人,瞬間只剩一堆骨頭。
形式文明,對決公平。最終其中一方4:3勝出。

其實,看過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的,也應該記得其中混混兒的自殘描寫。
漢奸偽軍司令高大成年輕時,從河北農村來到天津衛,他要和一個女混混兒搶地盤。
那是冬季,高大成找上門去,女混混兒的屋中有一個煤球爐子,爐子上坐著一壺水,高大成腳踩凳子,擼起褲腿,把鐵壺拿開,用兩指從通紅的爐膛里,捏出一隻紅煤球兒,放在自己大腿上,立時「絲絲拉拉」一陣亂響,屋中飄滿一股肉香,只見紅煤球由紅變暗,直到變白。高大成眼都沒眨一下。
女混混兒看著紅煤球變成白煤球,只說了倆字:認栽。地面就歸了高大成。
天津混混兒太粗鄙,太野蠻,太低端。
他覺得「忍術」應該更斯文、有風度。中國忍術的最高境界在於不是戰勝對手,而是戰勝自己,這種忍耐和對自己的殘忍,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真正的流氓,忍要忍到無恥,狠要狠到無情。
忍到無恥,可以呼他人為爹(如石敬瑭),為爺爺(如郭沫若);狠到無情,可以殺自己的親爹(如楊廣)、親兄弟(如李世民)。
歷史是發展的,忍術文化也不例外。
對自己殘忍,切自己命根子,那還算是有操守的。沒操守的,就是市井做法,外面受氣,回家拿孩子撒氣。
在傳統社會裡,打孩子是自家的事,沒人管。進入到現代文明,就不行了,有人會心軟,打孩子過於殘忍了,也會對周邊人、對手形成心理震懾。厲害的,能讓對方脆弱的心臟不堪忍受,向自己服軟,哀告自己:別打了,看不下去了,我服你了,你說吧,怎麼都行,只要別打你孩子。
這就是意志力的比拼!
當然,21世紀是文明時代,拿家人撒氣的形式也文明許多,比如不施以暴力,文明地虐待,給對手看。
當然這種群體性的忍術,需要內部兩方面的配合,一方要殘忍,另一方要能忍,如此,才能形成震懾力。戲碼方得完滿,效果才能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