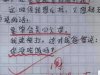那是個蟬聲高唱的午後。天應該很熱,不然也不會想去那個林業局的山頭,一個西南小城中樹木最茂盛的地方,5歲的我和一群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發現的「秘密花園」。這天的玩法是扯樹林裡麻繩粗的樹藤,纏在兩棵樹間做成鞦韆。樹藤粗糙僵硬,最後製成的鞦韆松松垮垮垂在離地面很近的地方,必須有一個小夥伴在身後助推,鞦韆才能啟動。
但就在那個記不清年月的夏日午後,鞦韆越盪越高,我記得自己幾乎倒立起來,腳尖碰到樹梢,發梢掃過地面,感覺像飛起來了。樹林很安靜,只有樹藤搖晃時與粗糙的樹皮摩擦的吱呀聲,還有孩子快樂的尖叫。

這是記憶里最淋漓盡致的一次快樂。蒙台梭利分析兒童一些重要的精神時刻,第一次提出「皈依」的概念。她描述一群大地震後倖存的孤兒,沮喪、沉默、冷淡,難以進食和睡眠。但在一個有寬敞庭院、寬闊走道、金魚池塘和美麗的花圃兒童之家中,在一群修女精心但溫和的教導下,這些兒童找到了皈依。
「他們到處跑和跳,或在花園裡提東西,或把屋子裡的家具拿出去放在樹下,既沒有損壞它們,也沒有相互碰撞。在這整個過程中,他們歡快的臉蛋上呈現出一種幸福。」當時有一位義大利著名的作家評論說:「這些兒童使我想起了皈依宗教者。再也沒有比征服憂鬱和沮喪,使自己上升到更高的生活層次更不可思議的皈依了。」

我也願意把在鞦韆架上不足為外人道的喜悅理解為一種皈依。蒙台梭利認為不幸的兒童擺脫悲哀和放任是一種精神更新,但對更多沒有遭遇巨大痛苦的普通孩子來說,能夠與環境和諧相處,並在平常中遇到比以往更深刻的快樂,也是一種精神更新。通往物我兩忘的專注的幸福可不容易。回想我們站在那架樹藤製作的鞦韆架之前,首先要翻過一堵約2米高的牆。一群1米多點的小孩像螞蟻搬家一樣,先找一堆界面相對平整的石頭壘在牆角,相互推舉後爬上牆頭。然後顫顫巍巍站起來,沿著牆頭走好長一段路,找到離牆最近的一棵粗細適中的樹,猛地撲過去,抱著樹幹滑到牆的另一側,才能到達那濃蔭蔽日,隔絕人跡的秘密花園。每一步都考驗著一個學齡前兒童的體力、觀察力、想像力和勇氣。更重要的是,在這群小人兒按照自己的想法,笨拙緩慢地征服障礙前進時,沒有橫空飛來成人的怒喝:「危險,停!」

因此,要到達那鞦韆架上的片刻歡愉,還必須有更多天時地利的鋪墊。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大規模的工業化尚未開始,很多城鎮還保留著依山傍水的格局,山林觸手可及,鄉村尚未凋敝。我們所在的那個西南小城,風景平常,但也有青綠色的沱江繞城而過,江邊是連綿的綠色稻田和山坡,坡上有各種不知名的花草野果。
城裡沒有車馬喧囂,父母似乎也放心讓孩子去山野獨立探險。我們可以趁夏季水淺時,手拉手趟著近腰深的水去江中心的小島,打著牛毛氈的火把去山洞深處找蛇的口水。這些獨立的田野練習試探拓展著我們的能力邊界,也是一次次情緒的試錯。有自然中的秘密花園,有孩子的自治空間,積累了無數次快樂或無聊後,大多數小孩遲早可以遇到自己的皈依時刻。

《童年隨之而去》劇照以成人世界的價值衡量,這種快樂通常比不上又認識了多少字,或者又背了多少首唐詩重要。童年通常承擔著「為未來生活做準備」的重任。在童年對孩子進行智力、體力、知識的訓練,被認為是一種負責任的遠慮,保護孩子在將來的激烈競爭中不致落敗。但如果孩子能在幼年時感受過發自肺腑的深刻快樂,他可能建立了一條與未來的精神通道。雖然記憶里只是片刻,但那種淋漓盡致的快樂,讓人在多年後即使身處最低谷,也有一種免於崩潰的力量。因為當環境太糟糕的時候,曾經嘗過的快樂會指引人有反抗的勇氣和方向。我回想自己成年後稱得上真正幸福的時刻,都與那鞦韆架上的快樂相似,這是30多歲的人生對童年的呼應。
這是個體化的童年解碼,可能有過度闡釋,還可能遮蔽得更多。蒙台梭利把0~6歲稱為「精神胚胎期」,認為這段時間是人的敏感期——距離自己天性最近的時刻。但「精神胚胎期」只是對童年蘊藏著巨大力量和可能性的模糊認識。即便是這個最著名的兒童心理研究者,也承認對童年可能孕育的幸福和罪惡所知甚少,「心理分析並沒有成功地探明童年這個未知的世界。它未能越過海格立斯的石柱,未能冒險進入這浩瀚的汪洋」。

《童年遊戲》劇照
因此,當滿懷愛意但缺乏耐心和觀察的父母們討論讓孩子的童年快樂,守護孩子的天性時,大多數時候是在說一些力不從心的口號。對這片私密莫測的領域所知甚少,父母們就不明白避免打擾和應該保護的是什麼,強烈但缺乏指引的愛意,甚至讓家長走上一條南轅北轍的道路。蒙台梭利就這麼警告過:「人們對兒童心理上的創傷仍然知之甚少,但是他的傷痕大多數是由成人無意識地烙上去的。」盧梭曾經指出過一條道路。他在育兒寶典《愛彌兒》中認為,12歲之前是理性的睡眠期,不能進行道德教育,也不能進行知識教育,感官和身體的訓練才是重點。有三種教育共同作用於童年: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如果這三種教育在一個學生身上相互衝突,那麼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將永遠不合他本人的心意。要想三種教育一致,自然的教育因為完全不能由我們決定,這種無法控制的教育就決定了其他兩種教育。這裡的「自然」指的是合於天性的習慣。由於孩子的節奏明顯慢於成人,他對自己天性的探究看起來是緩慢、笨拙且無厘頭的。如果成人根據自己經驗和節奏的習慣,認為孩子在做傻事而喝止他,可能就阻斷了他通向皈依的路。

《西小河的夏天》劇照
蒙台梭利的觀察也表明,成人的沉默和等待更可能是兒童天性萌芽的溫床:「兒童有一種特殊的內在活力,它能使兒童以驚人的方式自然地征服對象;如果兒童在他的敏感期里遇到障礙而不能工作,他的心理就會紊亂,甚至變得乖戾。」因此,「自然的教育」是一種消極教育——要阻止去做某些事情,讓天性說話。盧梭把鄉村設置為童年最理想的場所,大自然是「消極教育」最溫和適度的老師,它不會對兒童呼來喝去。兒童憑自己的能力和情緒,決定來還是去,開始還是停止。這樣的感官訓練是真實的,而真實是通往皈依的敲門石。什麼能欺騙孩子的心呢?
但有多少21世紀的父母能完全實踐這樣的鄉村教育呢?城市化讓自然支離破碎,密集的車流,陌生的墮胎,以及時常見諸報端的針對孩子的犯罪,讓幾乎每個受訪的父母都判斷,對孩子來說,這個世界是更壞了,即便是最大度寬鬆的父親也說:「絕不敢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
缺少最溫和適度的天然老師,喪失大部分的自治空間,孩子的童年由一系列和成人相處時吃飯穿衣談話交往遊戲的瑣碎細節構成。每個父母守護孩子天性和童年的願望實現多少,取決於一個個因人而異的技術問題:聽從孩子的懇求,讓他多玩5分鐘iPad,還是果斷收掉?當他為某件志在必得的玩具流眼淚時,應該轉過身去,還是掏出錢包?當他攀爬比他高出數倍的山崖時,是應該打斷還是讓他繼續?

每個問題都存乎一念,微不足道,但它們累積起來就是孩子的童年。一位教育研究者說,和孩子的相處不是科學,父母不應當是科學家,而是藝術家。「藝術」是仲裁這些技術問題的分寸感中父母要努力保持純真那部分,以理解孩子,又要放棄肆意那部分,以成為一個公正的仲裁者。盧梭說,對孩子的童年,父母要阻止的比要加諸孩子身上的更多。現在更是如此。有太多聲音對孩子的童年發言:傳統的遠慮、商業機構、學校關於秩序和規則的訓誡,還有家長自己的成見和焦慮。這是一個不斷自省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在微博上,一位因育兒心得頗受關注的媽媽的簽名是「做媽媽是一種修行」。還有一位父親稱這個過程是「一名普通父親的自我救贖」。這真是沉重的偈語。可是,家長們要憑一己之力,涉險越過海格底斯的石柱,守護他又儘量少打擾他,這絕不是件輕鬆的任務。

5月12日,荷蘭奧伊爾斯霍特,在荷蘭皇家軍隊開放日,兒童獲准進入軍營參觀。
這還是父母可以參與的部分,童年世界中還有更大的部分是需要孩子一個人走過的。我能記起孩子還不會說話的時候,漫長的午睡過後,他看著窗外即將西沉的太陽,臉上總有悲戚欲泣的陰鬱;進幼兒園時歇斯底里的號哭反抗後,認命的無可奈何又讓人心酸的嘆氣;當他看到一大堆不認識的小孩在嬉笑追逐時,自己也快樂地迎上去卻沒有任何一張笑臉接納他時,臉上那種茫然的神色。還有更多我們沒有能力觀察和解讀的黑暗時刻。
大部分時候,父母只能付出自己的時間和耐心,懷抱愛意地沉默和等待,等待孩子小小的身影自己穿過對外部世界的恐懼和障礙,接近自己童年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