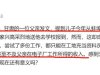1969年5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甘肅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十一師農一團九連,發生了一起針對普通軍墾戰士、支邊青年的屠戳事件。自始至終,由軍管當局和團革委會一手策劃和指揮。9人被射殺、暴毆致死,另有多人致傷、致殘,事後被施以酷刑,或被投入大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五二O」事件。
——原文編者注

一
黎明前時刻,各個「參戰」連隊都風塵僕僕、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地先後趕到了預定地點。因為各個連隊駐地離目的地的距離遠近不一,為了使大家能夠基本都在預訂時間到達預定地點,當初革委會和軍管組聯席會議制定方案時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要求各「參戰」連隊帶隊負責人事先要在不打草驚蛇的前提下親自到現場踏勘,一是熟悉分配給自己連隊位置所在方位的地形地貌,以免黑暗中出差錯;二是測算從自己連隊駐地到達目的地所用的時間。
不然到達的時間不統一,形不成嚴密的包圍圈,就有可能使「敵人」事先發覺,從後到連隊的缺口轉移或者逃竄,使這次精密設計殺戮行動不能取得完滿、徹底、乾淨的「勝利」。
畢竟不是經過正規訓練的部隊,各連隊的「參戰」人員到達指定的位置後,說話的、吸菸的、小便的,場面一片混亂。他們手中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門,長矛、鋼叉、大棒、鐵銑,好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赤衛隊。
幾名通訊員分別在各個「參戰」連隊通知帶隊負責人到臨時指揮部開會。臨時指揮部設在距九連營房50米處一片小土包上。這個位置是幾天前團里的頭頭和軍管組長以檢查麥子出苗情況為由,親臨九連周圍「偵查」後選定的。這次行動的總指揮是團參謀長李明讓,副總指揮是副團長劉二貴,參加指揮的還有以軍管組單副組長為首的四名軍代表。

在臨時指揮所,李總指揮仿佛又回到了戰爭年代。他身披軍大衣,腰別手槍,脖子上懸掛著望遠鏡,一臉殺氣,煞有介事地凝視著黑暗中的九連方向。不知是因為臨戰前的緊張,還是因為聽到從各個「參戰」連隊隱蔽待命方位不斷傳出的嘈雜聲,他雙手叉腰,緊蹙眉頭。副總指揮劉二貴和幾位軍代表圍在一起低聲研究著什麼事情。團警衛班10多人攜一挺輕機槍,其餘的是衝鋒鎗和半自動步槍,在指揮所周圍擔任警衛任務。機槍架在指揮所前5米遠的臨時工事裡,槍口虎視眈眈地指向九連駐地。除了三名通訊員外,還有一名司號員,緊隨李總指揮左右聽候指令。
各「參戰」連隊的帶隊負責人到齊後,李總指揮讓大家圍過來,在黑暗中向大家做最後的戰鬥部署:「各個連隊報告參戰人數和事先分配給你們連駐防的方位。
「一連。」「我們實到100人,駐防正南方位。」
「十七連!」「我們實到120人,駐防東南方位。」
「十五連!」「我們實到150人,駐防正東方位。」
「十四連!」「我們實到100人,駐防東北方位。」
「十二連!」「我們實到150人,駐防正北方位。」
「加工廠!」「我們實到100人,駐防西北方位。」
「機修廠!」「我們實到80人,駐防西南方位。」
「好!900比30,勝算有絕對把握。下面我再強調幾點戰場紀律:第一,要安靜。你們聽聽,從不同方位傳來『嗡嗡嗡』的嘈雜聲。這要是在正規戰場上,敵人早就發覺突圍了。好在我們的敵人不是真正的軍人,他們只是一幫沒經過正規訓練的F革命分子;第二,沒有命令不許出擊,衝鋒號吹響發動攻擊。第三,注意各個連隊結合部位不能留下縫隙,以免F革命分子從縫隙中逃竄漏網;第四,敵人手中有槍,要注意保護自己,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有人提問:「衝上去遇到頑抗怎麼辦?」「如果頑抗堅決消滅!下面看劉副總指揮和軍代表還有什麼指示?」他們都表示「沒有了」「好!大家各就各位。」
二
西邊的月牙漸漸墜落,啟明星閃爍在東方天際,朝霞漸漸顯露出她絢麗的色彩,太陽就要升起來了。

天漸漸亮了,九連駐地內開始有人影晃動,有早起習慣的人都起床了。有的去井邊打洗臉水,有的人急匆匆趕往廁所解手。炊事班的煙囪冒著黑煙,炊事員正忙著為全連準備早飯。有個叫董義慶的小伙兒去廁所解手,他睡眼朦朧地看到不遠處黑壓壓的人群,開始他還以為自己看花了眼,用手揉揉眼睛再仔細看,就是人群,並且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他突然醒悟過來,吃驚地大叫起來:「哎呀,不好了,我們連被包圍了!」邊驚叫著邊往回跑,連解手都不顧了。清晨的靜寂中,這驚叫像炸雷一般全連都聽到了,所有的人全都慌慌張張地穿上衣裳,出了宿舍像無頭蒼蠅一樣亂竄,有聰明的溜到馬號或躲到關係好的家屬屋裡藏了起來。
這時,朱森林心中也犯開了嘀咕—畢竟是「文攻武衛」的年代,啥樣的事都有可能發生。幾天前他就預感到情況不妙,曾和他的那幫弟兄商量著出去躲一下。但有幾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愣頭青滿不在乎地說:「兵來將檔,水來土掩。怕什麼,不行和他們拼了!」看到這樣,他也只好作罷,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吧。
昨晚,他一夜都沒睡踏實。白天發生的一件蹊蹺事令他頗費思量。二連衛生員劉X說是來看望教導員賈春芳的,但她卻在營部後邊的九連駐地大搖大擺來回竄動,一副目空一切、耀武揚威的架勢。被這幫弟兄們看到,認為她是二連「一一四」事件的主謀,是有意來挑釁,就圍住她進行審問。別看她是個女流之輩,但面對這幫當時在團里惡名遠揚、驍悍善武的男人毫無懼色,振振有詞,對答如流,並不時帶出揶揄挑逗口吻,氣的有幾個人想動粗「修理」她,教導員老婆適時出現,拽她出了重圍。朱森林當時沒有參與也沒有制止,只是在旁邊察言觀色,這個弱女子竟有如此膽魄,莫非她擔負有特殊使命?
這時,他一邊安排弟兄們上房頂占領制高點,一邊緊急思考著應對措施:黑雲壓城城欲摧,四面八方全是人,九連已經被圍的水泄不通,連只老鼠都逃不出去。看這陣勢,反抗肯定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只有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他暗地吩咐都不許攜帶刀具棍棒之類兇器,每人只帶上《毛主席語錄》,那才是戰無不勝的利器!
此時,另一位心中最明白的是指導員。這幫愣頭青二桿子們,他們不聽勸告、肆無忌憚,早就是天怒人怨,遲早會天理昭彰的,沒想到是應在今天。他和連隊幹部招呼全連所有不相干的人都撤離是非之地,到較遠點的糧食倉庫內靜坐學習,不許外出亂跑亂動,更不許參與。
還有一位不能不提的角色—團革委會委員、三營教導員賈春芳。頭天二連衛生員劉X就是到他家。這時被通訊員通知來到臨時指揮所。李總指揮問他:「二連衛生員劉X現在何處,目前有沒有危險?」賈回答:「劉X現在我家,沒有危險。」李總指揮讓他把朱森林叫到營部談話,命令他們:一、繳械投降,全體下房接受審查;二、交出壞頭頭朱森林、李成璽、張勝利;三、交出槍枝彈藥等一切兇器,否則後果自負。年輕氣盛的朱森林當時斷然拒絕,他心中早打定主意,與其舉手投降、丟人現眼,不如像條漢子硬撐著,至多就是二連「一一四」事件的再現,挨頓毒打,流一些熱血。二次上房,他把這個意思傳達給房頂上的弟兄們:「我們手無寸鐵,他們不敢真開槍。」
太陽升起來了,桔紅色的太陽透過朝霞放射出萬道光芒。臨時指揮所前移到離朱森林他們所占據的三棟房子較近些的糧食倉庫的頂部。
三
見「勸降」失敗,軍管組單副組長拿起話筒喊話「對面房上的人聽著,對面房上的人聽著,限你們5分鐘,限你們5分鐘:一、繳械投降,下房接受審查;二、交出壞頭頭朱森林、李成璽、張勝利;三、交出一切槍枝、彈藥、兇器。再重複一遍……」

聽到喊話後,出現了一陣短時間的沉寂。這時,房頂上的人才感到事情比預想的要嚴重。但此刻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他們突然發現天津籍知青金燕寶也在房頂上,大家紛紛勸他下去,不要跟著摻和,因為小金是朝鮮人,已經拿到了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定居手續。再說,他只是和這幫弟兄關係處得近些,並不參與他們的一切行動,應該不算是他們圈內的人,這時不知咋地給卷了進來,也上了房頂。還有另一位天津籍知青滕繼先,以前從不參與他們的任何行動,此刻也被卷了進來,上了房頂。而且,不知為何竟鬼迷心竅、不聽勸告,堅持留在了房頂上沒有下來。這一念之差改變了金燕寶的人生軌跡,沒能去成他應該去的國度,而是去了他不應該去的天國。
這時房頂上有人唱起歌來:「北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封信兒去北京,紅衛兵戰士想念親人毛澤東……」大家不約而同齊聲和唱起來。唱完一曲又接著唱另一曲:「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喊話再次響起:「房頂上的人聽著,再給你們最後一分鐘,再給你們最後一分鐘,不然後果自負,不然後果自負!」這是最後通牒。
60秒很快「嘀嘀嗒嗒」過去了。突然,隨著李總指揮一聲槍響,衝鋒號也響起:「嘀噠噠—嘀噠噠—嘀嘀嘀嘀—嘀噠噠—嘀噠噠—嘀嘀嘀嘀……」攻擊開始了。
「沖啊—殺啊—」已經等待的不耐煩的近千名「勇士」吶喊著,爭先恐後地沖了上去。霎時間圍住了朱森林他們占據的三棟房子。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手雷」—饅頭般大小的石塊一起向房頂上的人投擲,石頭像冰雹一樣砸到朱森林他們的身上、頭上。
按上千人每人投擲一次計,房頂上約30個人每人就要承受30個「手雷」的砸擊,如果每人投擲兩次呢?三次呢?這第一招就把房頂上的人整得暈頭轉向、難以招架。砸到身上痛,砸到頭上就是包,他們無處躲,無處藏,《毛主席語錄》也發揮不了作用,只好脫下棉衣蒙在頭上。個別人也有騰出手拾起落在身邊的石頭向下扔進行還擊的,但畢竟是以少對多、以弱對強;第一輪「石頭雨」結束,房上的人剛想喘口氣兒,忽然聞到一股並不陌生的氣味兒,原來是訓練有素的爆破手將竹竿頂部綁著已點燃導火線的炸藥包舉到了房頂上。房頂能有多大的面積?又沒有遮蓋物,房頂上的人在驚恐中只能儘量離炸藥包遠點,匍匐在那裡等待著命運的裁決。
在煎熬中炸藥包響了,第一聲爆炸把房頂上的人震暈過去,緊接著第二聲爆炸又把他們震醒過來。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們經歷了「生」「死」兩重天,體味著「生生死死」的滋味兒。這樣「死去活來」反覆數次後,爆炸終於停止了。房頂被炸出了多處大洞。驚魂未定,咳嗽未定,又感覺到一陣颶風從身邊刮過。隨即看到幾個人中彈倒下。
李成璽被機槍打中肚子,肚腸子流了出來,他對身邊的李文建說:「我……不行了……」但當時還沒咽最後一口氣;楊嗣壯被機槍打中下身當即悲憤地死在現場;魏成愛被一槍斃命。他們躺在那裡仰望藍天,死不瞑目。朱森林被機槍打中右肩靠下部位撿了一條命,張勝利腿部中彈與死神擦肩而過。
機槍手是十五連的復轉老兵肖丙干,當年被部隊培養成神槍手,和平年代一直沒有機會發揮自己的特長,沒想到在這個場合給了他發揮的機會。他才一個點射就斃「敵」傷「敵」這麼多,這樣的戰績使其興奮異常。光線適宜、距離適宜,目標是一群只能挨打不會還擊,無處躲藏、沒有遮擋的「活物」,就是打獵也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他調整了一下姿勢,移動了一下槍口,瞄準其中一棟房頂上的目標,這次準備打連發,把自己的特長淋漓至盡地發揮出來,給在場的領導和戰友們露一手,讓他們重新認識認識我肖某人。他剛要摳動扳機,說時遲,那時快,軍管組單副組長握住槍管向上舉起,一梭子彈射向了天空。等他看清是誰時,儘管心中有無限不滿但也無可無奈何。接下來,軍管組單副組長卸下了他機槍上的彈匣。

三輪攻擊過後,房頂上的人已驚恐不安且陣腳大亂,此時他們才明白,《毛主席語錄》和革命歌曲是阻擋不住機槍子彈的,手無寸鐵也無法使殺戮停止。他們紛紛從三、四米高的房頂跳了下來。但是,從這時起,近距離的殺戮卻開始了。譚建業手舉著《毛主席語錄》喊著「要文鬥不要武鬥」。作為回應,他被大批手持棍棒的人團團圍住,亂棒活活打死在雙槓跟前,他手中的《語錄》本掉在地上,被眾人來回踩踏。
他至死也沒能明白,能夠「一句頂一萬句」並能「立竿見影」的毛澤東的話,為啥沒能挽救他的生命?高其林也同樣被亂棒打死在現場。李文建從房頂跳下一個腳指骨折,當時並沒有感覺到疼痛,只是覺得腿軟站不起來。許多人將他圍住,其中一人咬牙切齒,手掄大棒朝他腰部砸來,他本能地躲開了。但那大棒沒有輪空,而是掄到旁邊的自己人身上,這一棒竟掄倒了兩個自己人。又有一個頭戴安全帽的欲用棍打他。這時,從營部方向衝過來一行人,其中一人撲向他,把他護在身下,才使他免遭荼毒。
這一行人原來是三營水工排的部分戰士,他們在施工員的帶領下,冒著被誤打誤傷的危險,儘自己綿薄之力保護手無寸鐵的受難者。先後保護了李文建、魏福星、劉小毛、馮健、王長安等人。否則,團部東面的山包上又會多出幾座墓冢。參加這一救助義舉的有施工員、景榮生、崔尚州、黃鐵錘及九連副連長候貴新等人。被救助的人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恩德;歷史應該記住他們的膽識和義舉,應該書寫上他們的事跡和他們的功德。
閆興貴的頭被大刀砍的血往外涌,他無力地靠在李文建身上,血把李文建的衣服都浸濕了,在上報死人名單時一直有李文建的名字。劉小毛除後背被炸藥包炸開了幾個傷口外,頭被棍棒打的腫的像鬥,對人說話頭不能扭動,得把整個身子一起轉動才行。馮健被無數棍棒追打,無處躲藏,無奈地鑽進劉小毛的雙腿間,劉小毛的雙腿也因此而被打斷。魏福星的後背也被炸傷多處。老實木納的姚易生被「手雷」多出砸傷鼓起了大包。
此時房頂上的人並沒有完全下來,有幾個人身負重傷動彈不得。參加屠戮行動的「勇士」們紛紛「勇往直前」,「協助」他們下來,許多人用棍棒、鋼叉、長矛像高寵挑滑車一般挑起房頂上的傷員,「一、二、三」地喊著號子,扔到三、四米以下的地面。往衛生隊解送時,也是幾個人拉胳膊拽腿,「一、二、三」,把人扔到敞篷車廂里。到了衛生隊,又是幾個人拉胳膊拽腿,「一、二、三」,從車上把人扔到地上。就是往治療室轉移,也是兩人各拽一條腿拉著走,被拽的人頭磕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台階上,發出「砰砰」的聲響。這一幕幕驚心動魄,令人驚悚的場面,是現場的局外人膽顫心驚。然而「勇士們」卻不時異常興高采烈地相互傳述著「好消息」:「又死了一個,又死了一個!」金燕寶、李小盆、楊廣、李成璽、閆興貴這五人,就是這樣先後被殘害死去的。張勝利負傷後,被人從房頂挑落房下後,自己裝死才躲過了真死。朱森林被挑落房下後,下巴被人恨恨地掄了一棒,鮮血濺到了幾步開外的王長安身上。

屠殺現場,炸藥包爆炸掀起的煙塵,加之上千人來回奔跑攪動起的土塵,在九連駐地久久沒能散開,那情景真好像日本鬼子大兵壓境在滅絕一處村莊。
四
在打掃戰場和清點戰利品時發現,現場實際擊斃加「俘虜」的人數同事先掌握的人數對不上。為了不致有漏網之敵,又派人仔細搜查了九連的角角落落,先後搜出了韓永平、葉元勝、姬西安等人。他們舉著雙手被從馬號押到操場等候發落。
軍管組最關心的是「F革命」們手中的槍枝彈藥,這是當初決定圍剿九連最關鍵的問題所在。整個「戰鬥」期間,情報中所說的槍枝彈藥並沒有出現,戰後讓大家反覆搜查,只是搜出了幾把改制刀具。「戰鬥」結束後,四名參加了整個戰鬥的軍代表,坐在營部的一間屋內面面相覷,心情沉重,大家誰都不明白,為什麼情報中提到的槍枝彈藥就沒有出現呢?誰心裡都明白,如果真的沒有槍枝彈藥,這次行動的合理性可就成了問題。
這是一場以多勝少的「戰鬥」、一場以強勝弱的「戰鬥」、一場全副武裝對手無寸鐵的「戰鬥」、一場設計得無懈可擊的「戰鬥」(甚至設想到以西安知青為主的五連得到消息後會支援九連,因此事先把十連的武裝人員埋伏在五連通往九連的必經之路上預備打援),這也是一場有計劃、有準備、有預謀,由具有實戰經驗的現役軍人參與並指揮的「戰鬥」。他們的「敵方」是一群手持《毛主席語錄》、口唱革命歌曲、沒有戰鬥經歷也沒有戰鬥經驗,只是「瞎胡鬧」,只知「打砸搶」的沒有真正「組織」的群眾組織。「戰鬥」理所當然地、毫無懸念地「完全」「徹底」「乾淨」地取得了全面勝利,並且「戰果輝煌」,斃「敵」5名(後又陸續斃「敵4名」),傷「敵」10多名,俘「敵」10多名,只有一個遺憾,那就是繳獲為零。
這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屠殺血案。顯然,對這幫手無寸鐵的「F革命」們,當初設計者並沒想要斬盡殺絕,不然他們完全可以把進攻時使用的石塊改成手榴彈。每人一枚,投擲1000枚手榴彈,房頂上的人肯定完全都會死光,甚至三棟房子都會夷為平地。他們攜帶的武器有兩挺輕機槍、數支衝鋒鎗、數支半自動步槍和手槍,如果想斬盡殺絕,三棟房頂上的人根本不夠「消滅」的。另外,團武器庫內還有迫擊炮、八二炮等重武器都沒有投入「戰鬥」,這說明設計者還是留有「善心」的,他們沒有製造更「慘絕人寰」的大血案,還是「慘有人道」的。
五
每名「俘虜」都被五花大綁,然後再用繩子穿成串押往團部,兩邊都有端槍(或持棍)的武裝人員押送。想必這樣的場景大家並不陌生,在現實的戰鬥影片結尾處,人民解放軍打了大勝仗,都是解放軍戰士押解著俘虜向集結地走去的鏡頭。不對,好像只要敵人繳械投降不再抵抗,解放軍對俘虜不五花大綁穿成串押解。要不就是與另外一種場景相似—反動派士兵押解著革命義士走向刑場……不,話好像不應該這樣說,當時的實際情況並不是反動派士兵在押解革命義士。還是算了吧,不探討這個問題了。因為那是一個人性泯滅、是非顛倒、謊言橫行的非理性的病態歲月,是一個一團糟,說也說不清的年代。

押送途中,天氣驟變,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天空驟然黑了下來,厚重的烏雲貼著頭頂翻滾著、涌動著。風聲似鬼哭、似狼嚎、令人心驚膽戰。負責押解的人撩起衣襟遮臉,用來阻擋暴風沙石的襲擊。「俘虜」們就沒這個「福分」了,他們被五花大綁,並被串成串,頭頂烏雲,任憑沙石擊打,艱難地行走在前途未卜、命運難測的路上。
18名「俘虜」全部關押在團部所在的十五連先前裝藥材的空窯洞裡。看押人員牢記偉人的教誨:「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因此他們對「俘虜」們絕不會有一丁點兒心慈手軟。
有個叫范小旺的「俘虜」就被五花大綁,胳膊勒得脫了臼。每名「俘虜」都要「過堂」,這樣的場景想必大家也都不陌生。梁仲運在激烈的「戰鬥」中躲過了大難沒有斃命,也沒有受重傷,但他卻躲不過「過堂」時的劫難,備用蘸了水的鞭子抽了178鞭,另加200多棍,回到關押他們的窯洞,抱起水桶猛喝了小半桶涼水;劉小毛也是劫難連連,先是在近距離殺戮時頭被打的腫的像個斗,頭上還被刀砍了幾個大口子。
在團衛生隊處理傷口時,醫生不給打麻藥,只是掰開傷口草草清理了傷口內的髒物,用針粗粗地縫上。當時他疼的死去活來,雙手抓住桌腿硬挺著。縫完針他當即站起來對旁邊的李文建說:「X X死了!X X也死了!」李文建眼含熱淚,低聲回答:「我都知道了!」隨即,他們被轉移到了「犯人」關押地接受審訊。
受審時,劉小毛又被棍棒打的皮開肉綻、血肉模糊,連身上穿的絨衣後背部位都被打的稀爛,回到窯洞也是抱住水桶一通「牛飲」。接下來,輪到李文建受審。「棍棒鞭子打的不計其數,有個人戴著手扣對準我肚子狠狠擊打了6下,只覺得翻江倒海般地疼痛。」回到窯洞也同樣像牛似的飲了許多涼水。魏福星被打時,打人者都嫌他沒出聲回話,說:「還嘴硬,繼續打,只打到他會出聲回話為止。」那位糊裡糊塗被卷進該事件的天津籍知青滕繼先也被嚴刑拷打,受盡磨難。

朱森林是應該被濃墨重抹的,他是本事件中之關鍵的人物。軍管組掌握的情報中說:是他從西安帶回了手槍、手榴彈,是他領著九連的一幫歹徒干盡壞事,殺豬宰羊、搶汽車,團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他們給送花圈,還製造了頭年「九二四楊XX事件」。他早已被革命委員會和軍管組內定為F革命組織的壞頭頭,是首犯。
「戰鬥」打響之前,教導員賈春芳受命和他進行談判,軍管組指令要保住他的性命。不然的話他即使沒象楊嗣壯、魏成愛那樣當場被機槍掃射身亡,也會在跳下房頂之後象高其林、譚建業一樣,當場被亂棍打死,或者象李小盆、閆興貴、楊廣、金燕寶、李成璽一樣被捅、被叉、被戳、被摔、被虐待而斃命。看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弟兄們先後死去,他內心愧疚不安、悔恨不已,不願意再妄活人世之間,要追隨他們而去。於是,他拒絕治療,扯掉繃帶,拔掉打點滴針頭,拒絕進食進水。
但是,他不能死,不能讓他死,團革委會和軍管組精心策劃的這次「鎮壓F革命暴亂」的行動,據說是取得了戰果輝煌的全面勝利,但是除殺戮了9條人命外,其他一無所獲。他們無法向上級交代,無法向全國群眾交代,也無法向自己交代。一句話他們無法為這次殺戮行動的理由自圓其說。現在,朱森林是唯一可指望利用的一個籌碼,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死。軍管組向衛生隊黨支部下了死命令,要採取一切手段,包括採用醫學手段和非醫學手段保住朱森林的性命,這下,朱森林想死也死不了啦。但是,他的災難也就自此開始了。
軍管組想保住他並非是可憐他這個「F革命壞頭頭」的性命,而是要從他身上挖掘出能向各方都有交代的材料:是要從他身上找出能夠證明實施這次「鎮壓F革命暴亂」行動是正確的理由;要從他身上撈到能混過關的稻草。
為了這些,朱森林在受審中被打斷了一條胳膊一條腿,經受了煉獄般的磨難,真正是九死一生,也真正是生不如死。在衛生隊住了100多天院後,仍被當作「F革命壞頭頭」判了三年徒刑,最終下了大獄。
結束語
這是一段塵封的歷史。40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把這段歷史翻出來,彈去它封面上的塵土,翻開扉頁,把它的真實面貌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們並非要追究哪個人或哪一方面的責任,因為事發後,在上級甚至中央的干預下,已經對這次事件定了性:它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鎮壓群眾組織事件。為那些受冤屈者平了反;對死難者按正常死亡對待,開追悼會、重新入殮、重新安葬;對他們的家庭給與了一定經濟補償;對本事件的相關責任人全部給與了處分,甚至師軍管會主任、蘭州軍區參謀長項智毅也受到處分。

關注昨天就是關注今日,關注歷史就是關注我們自己。如今,我們都已年過花甲,子孫滿堂,闔家團圓,享受著天倫之樂。而那些在這次屠戮中悲慘死去的鮮活的年輕生命,卻永遠孤獨地躺在團部東面的小土丘下。面對他們,我們只能默默地道一句:安息吧,兵團戰友們,願你們在天國能夠活得好,不要再像在陽世一樣遭受不公。
最後,要感謝朱森林、李文建、梁仲運、魏福星等幾位當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在採訪過程中,筆者深深感到,雖然經過40多年的時間跨度,但當事人對當時的場景、人物、甚至言談話語及許多微小細節都記憶猶新,因為所有這一切,對他們是刻骨銘心的。還有一點要說及,經過40多年的反省,特別是面對死者和這次事件中的一切受害者,上述當事人對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深感自責。(作者:王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