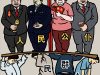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1—
當我們在十三陵勞動快要結束的時候,就有消息說,回校後將要把我們這些「奴隸」集中起來。消息說,學校兩派武鬥正酣,聶元梓的校文革害怕黑幫們從中鬧事,決定將「黑幫」集中管理起來。我們一回到學校,就沒有回到自己的宿舍,而是直接到建立「黑幫大院」的工地上。這就是說要我們自己給自己建立一座監獄,或者說是「作繭自縛」。
「黑幫大院」就是聶記監獄。這個監獄就在北大西門內左側的東方語言文學院大樓後面。原來那裡有12間平房,是北大的業餘學校。文革一來,業餘學校也不辦了,他們就要在這裡建立「黑幫大院」。工程並不複雜,就是把蓆子連結起來,搭建成一個圍牆,大概有三米之高。具體的時間我已記不清了。「黑幫大院」的正式名稱似是監改大院。《北京大學記事》對此有所記載:「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決定在校內民主樓後面的平房建立監改大院(『監改大院』俗稱『牛棚』),先後關押各級幹部、知名學者及師生218名,『監改大院』設有監管人員20多名,由國際政治系學生劉國政任總負責人(劉國政是歷史系學生,不是國政系學生。引者按)。」
在「黑幫大院」這所監獄裡,北大的主要幹部,從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有時被關在這裡,有時又被關到別處)到各系、各部處的大多數幹部,都被關在這裡。200多人都有名目。例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漏網右派、流氓、牛鬼蛇神、反動學生等等。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指文革前學校的各級幹部;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指寫過一些不符合他們口味文章的人;所謂叛徒,就是指那些曾經被敵人關進監獄裡的人;所謂現行反革命,就是指那些曾經對文化大革命有過不滿言論的人;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就是指在學術界、科技界有成就的學者和科學家;所謂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就是指那些被冤枉劃為右派而始終不肯認罪的人;所謂漏網右派,就是指那些欲加之罪、不患無詞的人;所謂流氓,就是指那些生活作風不夠嚴肅的人;所謂牛鬼蛇神,就是指那些對他們不滿而找不到適當帽子的人。總之,他們製造了各式各樣的帽子來打擊他們要迫害的對象。
在「黑幫大院」受迫害的北大名教授我認識的有:化學系的傅鷹和邢其毅,他們是中國著名的化學家;地質地理系的侯仁之,他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歷史系的鄧廣銘,他是中國著名的宋史專家;歷史系的張芝聯,他是中國著名的西洋史專家;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吳組湘,他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朱德熙,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王瑤,中國著名的現代文學史家;魏建功,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法律系的陳守一,中國著名的法學理論家;芮沐,中國著名的刑法專家;季羨林,中國著名的東方語文學家、散文家;西語系的朱光潛,中國最著名的英國語言文學家、美學家;李賦寧,中國著名的英國語言文學家等等。上面我提到的都是我所認識的若干著名教授,至於我不認識的還有很多。他們都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對中國文化有過相當貢獻的人。而這些人現在都受到豬狗一樣的待遇。劫後,梁漱溟先生曾寫過一首詩哀悼中國的知識分子,其中有幾句說:「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2—
「黑幫大院」里的管理者,雖然大多數是學生,但他們出手不凡,懂得不少管理的策略。記得馬基雅維利的權術中有這樣一條:「不讓國家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不讓首都知道外地發生的事。」它的意思是要將自己的奴隸或其他獵物同外界隔絕,變成聾子、傻子,變成沒有思想、沒有頭腦、馴馴服服、服服帖帖任人擺布的工具。根據這種指導思想,「黑幫大院」規定:(1)要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2)黑幫之間,不准傳遞任何信息;(3)黑幫同黑幫不能說話;(4)黑幫晚上大小便,要向值班人員報告;(5)黑幫走路要低頭;(6)不能擅自走出監改大院;(7)扣除每個人的工資,只給每人留17元伙食錢。大家都住在大院裡,沒有什麼信息可以獲得,這點容易做到。只有低頭走路這一條執行起來很難。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都是抬起頭來、眼睛平視走路的,這是生理上的需要,違反這種生理的需要,就很難受,常常會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直起頭來走路。
在「黑幫大院」,如果你稍不留心,就會被監管人員來一個當頭棒。我就曾經看見一個被監改的人員,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一時疏忽了低頭走路的規定,被一個監管人員看見了,這個監管人員立即當頭一棒,喝道:「低下你的狗頭來!」所幸我對這一條比較注意,沒有受到過這種當頭棒喝。
只給17元伙食費,夠吃家常便飯了。沒有外出的自由,也沒有花錢的機會,也不感到十分難過。但也有例外。有一天,從河南家鄉來了一個堂妹,她是一個貧農子弟,來北京告狀,在「黑幫大院」找到我。我當然無法關心她要告什麼狀,也不敢問她家鄉的任何情況,相對無言地站了一會兒。這時候,我的母親已經去世,我是多麼想問一問我母親去世前後的情況,但這在監獄裡是絕對不允許的。我的堂妹要走了,她說她回家沒有路費,要我給她一點錢。這在平時是絕對要盡的義務,我向監管人員請示,可否從我的工資里給她30元錢?監管人員拒絕了我的請求。我的堂妹眼淚汪汪地望著我走了。我這個人不大會哭,而在這裡、這個時候也不敢哭。據後來了解,我的堂妹回家後沒有透露我在北京的情況。
1968年國慶節,我們是在監改大院度過的。百無聊賴中,趙寶煦同志口占一首《西江月》小詞,排遣他的鬱悶。錄之於下,以見證當時在「黑幫大院」被迫害者們的心情。
「黑幫大院」即興(調寄西江月)
是人是鬼未定,
走來走去低頭,
黑幫大院數風流,
蝦蟹魚龍都有。
熱火朝天國慶,
淒風冷雨中秋,
值班深夜啃窩頭,
休管明天挨鬥。
—3—
在「黑幫大院」,一般的情況是白天勞動,晚上回來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在那個時候,據說北大有500個勤雜工。文革一來,他們都解放了,由我們這些人取代了他們的工作。每天吃過早飯後,「黑幫大院」的黑幫們,分成若干小分隊,到不同的地方去勞動。我和趙寶煦常常去北材料場,有時去南材料場。
晚上收工後吃晚飯,晚飯後是例會,這個例會每天都有,是監管人員集中迫害「黑幫」的時候。每天晚飯後,一聲哨子響,全體集合。大家因為怕挨打,都爭先恐後地去排隊。排好隊後,就是聽他們的訓話。他們的訓詞,開頭照例是:「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你們都是人民的罪人,你們要好好改造,否則,只有死路一條。」訓詞之後,就是挑毛病了。他們會無中生有地說某某人今天勞動不好,立即把那人叫出來,問:「你今天為什麼偷懶?」如果你不承認偷懶,他就幾個嘴巴打過去,打得你滿嘴出血。那時候還有一個制度,就是規定背誦毛澤東語錄。頭天給你布置一條毛的語錄,第二天的例會上讓你背誦,你如果不會背誦,就要遭毒打。毒打之外,還用各種辦法折磨你。我記得哲學系有一個教授,名叫桑燦南,可能是他的記憶力差一點,每次背誦毛語錄,他總是背誦得很不流利,因此總是被打嘴巴。打了之後,就呼口令:「立正,向後轉,向前走。」聽見口令的桑燦南,抹一下嘴上的血,馬上就立正,接著就向後轉,然後就向前走。他前進的方向是一堵牆,桑燦南一直走,頭已經碰在牆上了,監管人員也不喊立定。此時的桑燦南,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原地踏步。監管人員看見桑不前進了,就呼叫:「桑燦南,怎麼不走了?繼續前進!」這實際上是讓桑燦南用頭向牆上撞。桑燦南沒有辦法,只好以頭撞牆,結果弄得滿臉是血。每個晚上例會,他們都要用這種辦法折磨幾個人。趙寶煦就曾經這樣被他們折磨過。趙寶煦同當時的黨委副書記張學書在同一間房裡住,而且床鋪靠近,兩人又非常熟悉,有時會違反禁令說幾句話。有一天,張學書問趙寶煦黨費如何交法?趙告訴他如何交法。趙說我領18元生活費就交1.8元。張說,我仍按以前的工資交黨費。這個簡短的談話,被某某人匯報上去了。這個談話違反了兩個規定:(1)違反了黑幫之間不能說話的規定;(2)黑幫是敵人,沒有資格談黨費問題,談論黨費表示不肯認罪,是翻案的表現。當監管人員聽到這個匯報後,就在例會上問趙寶煦:「你同張學書談話是不是事實?」趙回答:「是。」監管人員又問:「你是不是混進黨內的?」趙為了避免挨打,無奈地回答:「是。」之後,監管人員就喊口令:「立正!向後轉!齊步走!」趙寶煦按照口令走去,前面是一棵樹,無法前進了,趙只好面對樹原地踏步。他面對樹一直站了4個小時,到了夜裡11點才讓他回去。
像這樣打人、罵人、折磨人的事,每個晚上都有,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對於這個晚上例會,都提心弔膽。首先是一面勞動,一面默默背誦毛的語錄,以應付晚上的例會。我不害怕勞動,不怕吃苦,只害怕這種對人的折磨和侮辱。我們在北材料場勞動,沒有挨過罵,更沒有挨過打。那裡的工人對我們表示同情,有時候還同我們說悄悄話,叮囑我們要保護好身體,要處處小心。我十分感謝他們。有的師傅的姓名我忘記了,只記得一位何師傅的憨厚善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工人這麼善良,而那些有知識的大學生卻那麼殘暴?人性善?人性惡?階級性?我說不清楚。後來我想出了一個道理:人們的利益觀決定人們的行動。工人們只是靠自己的兩隻手幹活吃飯,他們沒有別的能力,沒有想過一夜會暴富起來,也不妄想在自己的生命里會出現奇蹟。而有些知識分子則不同,他們以為自己有能力,幻想一夜會發達起來,以為只要緊跟某某路線,就可以直線上升。不是嗎?不少地方的縣委書記、縣長,不少地方的省委書記、省長一個一個地垮台了,而不少名不見經傳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縣委書記、縣長,變成了省委書記、省長。真箇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這樣的暴發戶,怎能不引人發狂呢?所以,他們有些人要發狂地表現自己。怎樣表現?就是瘋狂地打罵鬥爭「黑幫」,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4—
「黑幫大院」雖然只是一層席棚,但卻如同銅牆鐵壁,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裡面20來個監管人員如同牛頭馬面,個個兇狠異常。在這個用草蓆圍起來的小院裡,陰森可怕,隨時都可能有災難降臨身上。走路忘記低頭,要遭棒打;不慎同別人說了一句話要挨嘴巴;背毛語錄掉了一字,要吃耳光;出門沒有帶毛語錄要罰跪;呼叫一聲沒有馬上回應,也要挨鬥。事情已經過去30多年了,有些事情已經忘卻了,現在僅就還記得的一二,略述如下:
(1)周鐸身上的血。
前面我介紹過周鐸。隨著監改大院的建立,周鐸也進來了。他雖然並非大人物,但卻是監管人員關注的對象。他在勞動中挨打最多,他穿一條白褲子,褲子上經常血跡斑斑。他被整得精神錯亂,神經失常,他到海淀的飯館裡舔人家的碗底,在去勞動的路上揀柿子皮吃。監管人員見他如此,就狠命地打他,打得他滿身是血,在地上翻滾。雖則如此,他依然如故。監管人員問他:「周鐸,你為什麼揀柿子皮吃?不是給我們政府抹黑嗎?」周鐸怯生生地說:「我不是抹黑,我喜歡那個味道。」人到這個樣子,算是改造成功了。在兩個月後的一個全校「寬嚴」大會上,給了他個從寬處理,並被分了工作。但他十多年來身體被嚴重摧殘,不久就死去了。
(2)李賦寧鼻口冒血。
我在前面提到過,李賦寧是國內有數的英國語言文學家。有一天他勞動完畢,在回「黑幫大院」的路上,看見一張大標語寫著:「崔雄昆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在那個年代裡,凡是出現這樣的標語,就表明這個人自殺身死了。崔雄昆是什麼人,他原來是北大的黨委副書記、教務長,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文革開始後,他又是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因而成為聶元梓校文革的結合幹部。當時北大分為兩派:新北大公社派和井岡山派。前者是擁護崔的,後者是反崔的。當李賦寧看到這一消息後,就在院內悄悄地散布了這一消息。崔雄昆之死,是校文革的不幸,他們忌諱別人知道這一消息。當他們知道李賦寧散布了這一消息時,「黑幫大院」的監管人員,就狠狠地打了李賦寧的嘴巴,李馬上鼻嘴出血。當李被打時,我就在李的身邊,嚇得心裡咚咚的響。因為我也看到了這條標語,也散布了這條消息,只是沒有被他們發現。
(3)陳守一、黃一然經常被打翻在地。
陳守一,老共產黨員,法學界的老前輩,曾在中央政法幹校做過副教務長。文革前是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文革前夕,康生之妻曹軼歐曾找他寫攻擊北大黨委發動文革的大字報,他拒絕了;不得已,曹軼歐才去找聶元梓。在複雜的革命鬥爭環境中,他曾一度脫黨,這是早已弄清楚了的問題,而此時又被翻騰出來,被誣陷為叛徒。這兩大罪狀,特別是拒絕寫大字報的罪狀,更是被上綱為反毛澤東路線,當然是十惡不赦。我曾多次看見這位老革命家被打得遍體鱗傷,在地上翻滾,真是所謂「打翻在地,又踏上一隻腳」。最早的一次是在煤場,那是1966的文革初期;後來是在「黑幫大院」。
黃一然,老共產黨員,曾做過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當時是北京大學副校長。他也蹲過國民黨的監獄,因而被誣陷為叛徒。在「黑幫大院」,那些監管人員對被誣陷為叛徒或特務的人格外殘酷。我曾多次目擊這兩位老共產黨員被毒打的情況。有一次,就在大院內,一個監管人員問黃一然:「黃一然,你是不是叛徒?」黃答:「我不是。」打手罵道:「混蛋,你不老實!」說著,一拳打下去,黃栽倒在地。打手喝道:「你別裝死!」說著,就用腳踢,肋骨上踢。踢得黃一然發出聲來。同樣的情況,我還看見他們這樣毒打陳守一。
(4)捉弄王瑤。
王瑤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教授,研究並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史。我不知道是有人揭發王瑤勞動偷懶,還是監管人員故意捉弄王瑤。他們強迫王瑤手上拿一面鑼,一個小槌子,走遍全院12間房子。每到一個房間就敲鑼,同時向大家宣讀寫好的幾句話:「我是王瑤,是中文系的,我幹活偷懶,我是壞蛋,請大家不要學我。」
(5)唐子健跪石渣。
唐子健是物理系的講師,他患有腿疾,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在北大兩派的鬥爭中,他支持井岡山一派的觀點,這就為聶元梓校文革所不容,並把他抓到大院來進行批鬥。別人被批鬥時,是站著,或讓彎腰站著。因為唐子健腿有毛病,不能站立,打手們就讓他跪在地上。後來又從別的地方弄來一些石頭渣子,勒令他跪在石渣子上批鬥。
(6)被五花大綁、打得皮開肉綻的朱承立。
朱承立是西語系的年輕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風暴一來,他也被送進「黑幫大院」。他年輕氣盛,受不了這裡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我也記不起來他逃向何方。「黑幫大院」的打手們用了好幾天的工夫,又把他抓回來了。抓回來後,幾個大漢手執皮帶,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開肉綻。朱承立雖然疼痛難忍,但他並沒示弱。打手們也無可奈何。
(7)朱光潛的吃飯之辱。
朱光潛當時是一位70歲的老人,中國著名的文學家、美學家。照理他應該是受人尊敬、有人侍奉、在家安度晚年的時候,可他也作為「黑幫」被揪出來。在「黑幫」的隊伍里,是賤民,大家沒有高、低、貴、賤、老、少之分。在吃飯的時候是依次排隊的,而朱先生卻排在後面,他飢腸轆轆,不自覺地走到了前面,被舔痔之徒向監管人員告發。晚上例會時,他們要整朱先生了。監管人員一聲斷喝:「朱光潛,出隊列!」一位白髮老人走出了隊列。他立正地站著,監管人員問:「朱光潛,你今天犯了什麼錯誤?」朱光潛答:「沒有。」監管人員問:「你吃飯為什麼不排隊?」朱光潛答:「我不是故意的。」監管人員:「明天寫認罪書。」第二天晚上例會時,朱光潛在會上宣讀了兩首認罪詩,我只記得一首:「買飯排最後,飢腸似熬煎,誰叫你貪吃番茄,誰叫你排隊搶上前?」
(8)史夢蘭因耳聾吃嘴巴。
史夢蘭是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是文革前的北大黨委第一副書記。他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出來的。他和我同住一室,他耳朵不好使。有一天,一個監管人員呼叫:「史夢蘭!」史夢蘭沒有聽見。接著又是一聲「史夢蘭」的呼叫,史夢蘭仍是沒有聽見。那人怒吼了,他跑過來對準史夢蘭的臉,一連幾個耳光,並叫罵:「老混蛋,你幹什麼吃的?」史夢蘭被打得口鼻出血,一臉無奈。
(9)胡壽文、趙以炳被侮辱與被折磨。
胡壽文是1948年入黨的黨員,長期任北大生物系的總支書記。系總支書記,已經夠上「走資派」的頭銜,還曾經同他的愛人議論過當時的極左政策,於是走資派之外,又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當然是罪上加罪。因此,他成為監管人員求之不得的獵物。他們無事可干,就以打罵「黑幫」取樂。有一天中午,正烈日炎炎,有一個監管人員命令胡壽文張開雙目,對準天上的烈日直視了半個小時,而他則在樹陰下看笑話、取樂。這事我雖早知道,但並非我親眼所見,後來我問老胡:「他用這個辦法折磨你,動因何在?」老胡說:「沒有什麼動因,就是他們要侮辱我,他們要取樂。」最近我拜讀了周一良先生的《自傳》,看到監管人員曾經用同樣的方法折磨他的夫人鄧懿教授。還有一次,監管人員把胡壽文和趙以炳從獄房裡叫出來。趙以炳是生物系的教授。監管人員要胡壽文和趙以炳「牛抵頭」,就是要胡和趙兩人的前額相抵,作「牛抵頭」狀。這樣,兩人都要各自半弓腰,以保持平衡。這種狀態如果堅持三兩分鐘也沒有多大關係,可惡的是,這些缺乏人性的傢伙,竟讓他們這樣站了半夜,使他們兩人疲憊不堪。
(10)李獻之被打不計其數。
李獻之,地球物理學系的教授,此時大概60多歲,他是大院挨打最多的人之一。他們為什麼要那樣經常打他,現在也記不來了,也沒有去問過他。我只記得他不斷挨打。
(11)文重被打耳光。
文重,曾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化學系副系主任。按照「黑幫大院」的規定,晚上為學毛著時間。監管人員是不學毛著的,他們只是從毛著中尋找毛澤東罵敵人的話,用來罵他們監管的教授和幹部。但他們卻強制教授和幹部們學毛著。有一天,一個監管人員走進房間,檢查學習,他要文重背誦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這段話,文重背錯了一個字,他便開口大罵,聲音極高和粗暴,並動手打了文重幾個耳光。我住在文重的隔壁,對打罵之聲聽得很清楚,我們這個屋子裡的人都非常緊張。第二天,我們才知道詳細情況。
在「黑幫大院」,監管人員打人是經常的事,被打的人很多。他們打人也沒有什麼理由,有時只圖一時痛快,有時也只因小事一樁。例如,你沒有低頭走路;或者你同另外的「黑幫」說了兩句話被他們聽見;或你耳朵有點毛病,沒有聽懂他們的話;或者你背誦毛語錄不流暢;或者你背誦毛語錄漏掉了一個字或兩個字;或者他們根據某些不實之詞強迫你承認;或者你忍受不了他們蠻不講理的虐待而稍感不愉快;或者他們覺得你走路快了、慢了或者說你勞動磨洋工;或者說你學毛著不積極;或者根據匯報人的某些莫須有的匯報,都可以成為打你、罵你的起因。因為這都是35年以前的事,有些人我並不認識,上面的事例大都是我親眼看見的,至於我沒有看見的也不知有多少。那些不堪回首的事,真是罄竹難書,我這裡說的只是掛一漏萬。
選自《我在北大六十年》,陳哲夫著,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