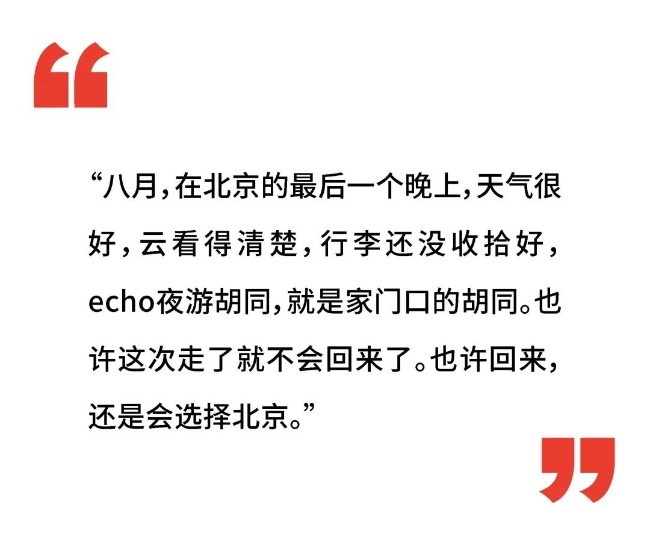
「你只能反覆告訴ta,這不是你的問題。」在一期離開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這句話,「這個感受非常普遍。剛離開時候,我會想個人原因和環境因素哪個更大。」今年8月,她離開了北京。
很少會這樣,離開一座城市,人們要如此謹慎地反思、審視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問題?但北京是個特別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個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就該認識「北京」,它出現在課文《我多想去看看》裡:「遙遠的北京城,有一座雄偉的天安門,……我多想去看看!」
來到北京總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勵。地圖上,北京是雄雞的心臟。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個複雜的龐然大物。它創造了許多名詞,北漂、朝陽群眾、海淀媽媽,人們被北京定義。關於它的文章光怪陸離,《北京零點後》是密集,《北京摺疊》則是弔詭。今年六月,北京成為中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標。
於是,說起「離開北京」,像是逃兵,被競爭、房租和交通壓垮,一種被淘汰的失敗。
近三年來,「離開北京」這個話題越來越熱門,而且人們的去向越來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國外,已經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來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這是怎樣的一種趨勢,同時也是一個個真實故事發生的情景呢?

20+,
離開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
毫無疑問,竹子在北京已經足夠努力,光看她的履歷表就可以知道。
從2019年畢業前,到2022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換過五份工作:廣告公司、紀錄片工作室、文化空間、劇場、媒體……
與此同時,她還在夜裡兼職,有時是咖啡店的店員,有時則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時清晨六點下班,早上繼續上班,精力充沛得像個孩子。
北京滿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東北成長至22歲,學習的廣電專業,在家鄉一帶往往只能找到事業單位的工作,她總是倒在筆試環節。
在北京,工作機會要龐雜得多。劇場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現代舞課程,卻找到了招聘啟事,幾個月後,她就與以色列、加拿大老師,一同出現在舞蹈周節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則乾脆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間裡遇到了陳嘉映與劉瑜。
北京永遠有最新的東西。竹子剛來北京時,短視頻上了風口,無論她在的哪家公司,都願意試試短視頻;疫情之後,她的工作又轉成了新晉寵兒——播客製作。
就連兼職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夠多的劃分。一種是她熱愛的酒吧,多在東城,譬如school,人群混雜著隨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緊事。
另一種泛稱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調酒師、優秀供貨渠道、穩定而資深的投資者組裝而成,像一輛福特汽車。據說,部分酒吧有著嚴苛的規則,著正裝進入,消費達標可以進入二層,再往上升,還得有點品味,一種隱喻。竹子的態度是:「我暫時是不太習慣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東城酒吧」類型和「三里屯酒吧」類型中切換,要麼是更成熟和商業廣告公司,要麼是體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總是不滿意,兩者難以平衡。商業化帶來了無價值感,而缺乏商業的理想同樣感到讓人虛無,竹子說:「那種沒有一個行業和崗位想做,就和咖啡師沒有一個店想去的感覺是一樣的。」
疫情是讓竹子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她所兼職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關閉。正職的文化空間也從實驗性的,變成努力求生的小店。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但至少她還挺喜歡bartender的工作。於是,她去了三亞,繼續做bartender。

此前,她猶豫過,對於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夠成為白領的人來說,完全變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種墮落?
但三亞好像沒人在乎。這裡曾經去過、住過北京的人不少,現在,他們都在這裡,等到夜裡來喝杯酒、聊會天。
竹子的生活變成了發呆、潛水、無所事事或是學習。她想:「離開北京對於我們這樣機會很少的小孩來說,其實只是讓自己有得選,哪怕只是看起來的、暫時的。我終於發現,當吧員不是一種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麼,代價是什麼。」
可以把離開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經培養了足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機會讓人疲憊。她需要休息和考慮。
竹子打算繼續學業。那之後,會不會再回到北京?也許吧,誰也無法預測幾年後的事。

同樣去往了旅遊城市的還有日堯,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間往返,從事動物保看護作。
在離開北京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前,日堯決定:「我要到山裡去,人越少越好。」而後得償所願。
滇西的村寨得開車抵達,距離縣城一個小時的路程,攏共二十九戶人家。每天早上八九點鐘,長臂猿像公雞打鳴那樣把人叫醒。村民們把長臂猿叫做「甲米嗚呼」,傈僳語,「嗚呼」就是模擬它的叫聲。
和族人建立聯繫,日堯也會和他們一起餵牛、打筍子,偶爾用漢語聊聊天。傈僳族人說漢語依然遵照自己的語法,先說主賓,再說謂語。
大理的辦公室沒那麼山野氣息。其實日堯過去並不喜歡大理:「總讓人想起安妮寶貝,或者文藝青年。就是太文藝了的感覺。」但她覺得大理和想像中很不一樣。
在大理,日堯租住在750元一個月的房子裡,看得到蒼山,走路幾分鐘便能到達古城。她參加過706空間的聚會,在那裡,比她還要「離經叛道」的人更多,數字遊民們分享著經驗,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亞」。
「離開北京以後,感覺到世界開闊了,原來還有那麼多種生活。」這是日堯的感受。
在北京,日堯最自在的行為,是工作後去看live。非得在現場,才能沖刷格子間裡螺絲釘的感覺。每周或每兩周一次,從公司出發得一個小時,回家得兩個小時,北京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超大城市裡可供選擇的娛樂地點種類不多。日堯的工作地點曾在798邊上,有同事趁著午休一口氣逛了三個展覽。今年,龐寬進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堯很容易地認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間。
798園區里四處是塗鴉,時不時有人拍照,日堯覺得那很傻——她太頻繁地來到798,對於塗鴉已經習以為常。她幾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塗鴉照片只有一張,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換了工作近一年,日堯還沒有去過live,也沒有再去找live 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堯暫時沒有計劃再回北京:「現在,我還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後的離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