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亞洲電台製圖
外界常以"56789"幾個數字來概括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其中5是指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50%的稅收,9是指貢獻了新增就業的90%。但近幾年,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採取打壓和漠視的政策,使民營企業的信心大受打擊。去年底中國結束疫情封控、走入經濟復甦的通道後,民企的信心並沒有得到有效恢復,甚至拖累了中國經濟整體的表現。本台記者王允采寫了三集系列報導,以多位民營企業家的經歷來揭示中國民營經濟遭遇的困境。在以下第二集的報導中,將主要講述三位服務、貿易類小微企業主的近況。
去年4、5月份上海疫情封控的時候,張開宇想過要和自己的兩隻貓一起死。
這兩隻貓他已經養了10年,他說貓就是自己的軟肋。不少人的寵物被封控人員消殺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張開宇尤感恐懼,「我不能忍受他們被錘死,或者我親手去掐死他們,這太慘,所以那時候我想到的,就是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然後把煤氣打開,他們就會慢慢窒息死掉,那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這是張開宇能想到的最完美的方案,但或許是因為還有妹妹和母親,或許是對自由還留有一些嚮往,張開宇最終沒有下手。但這個時候,他心裡已經把自己的生意放下了。
離散與潰敗
張開宇在上海經營一家時尚精品店,到2022年時已經有十六年的時間。他的客戶是上海的富人階層,在他固定聯繫的一千名客戶名單上,很多人都是身家幾千萬以上。但上海四月份封控之後,這批客戶逐漸離散,「特別是那兩個月里,跟朋友聊起來,都是想離開,不顧一切想離開,包括客戶和朋友,特別是客戶,那些有能力離開的,有錢的,都是這樣。」
張開宇一開始還想著維持一段時間看看,但他發現即使留下來的客人消費行為也發生了改變,「就是有新東西上市,你看他們到底來不來,他們有的就不來,或者來了,你看他們,可能看半天就只挑了一件、兩件,甚至還是比較便宜的,而且要很長的思考,不像以前就像無腦買一樣。」
張開宇很快想通了一個道理,「你看封城這兩個月,幾乎所有人都像被關在一個大監獄裡,沒有任何自由,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其實生意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到了年底,張開宇就把生意轉了出去。
也是2022年,身在成都的莫先生(出於安全考慮,使用了化名)在5月份關掉了在青羊區的最後一家快餐店,並決定永久離開餐飲業。
莫先生2014年投身餐飲業,最好的時候在成都擁有六家餐館,但到2022年時已經只剩下兩家快餐店。他最後關掉的這家快餐店仍然是賺錢的,但他最後還是決定不做了,「當時就是不明朗嘛,2022年的5月份疫情還沒有結束,還在陸續的封城,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封到成都了;一封的話就是兩三個月,又要做不起來了,你的庫存、你的人工、你的房租還是要付,雖然說還可以盈利,可以賺一部分錢,但一停工,這些錢都已經投進去的話,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2020年9月8日,成都市,新冠疫情爆發後,一名川劇演員在錦里古街的一家餐廳等待顧客。(路透社)

而杭州的葛平創辦的諮詢公司好不容易熬過了2022年嚴酷的封城,還是選擇在2023年初為其旗下的子公司辦理了「歇業」。為安全起見,「葛平」以化名接受採訪。
根據2022年3月開始實施的《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所謂歇業,是指企業如果遇到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的情況,可以申請保留主體資格,不按停業處理,待情況好轉後重新啟動。但葛平並沒有覺得所謂「歇業」給自己帶來了多少好處,「後面發現,歇業的企業這些基本的支出,財務的費用,稅務的費用,租辦公大樓、租工作室的費用都是要出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保主體,就是不讓市場主體退出得太多,政府是有這個考慮。」
葛平揣測,政府推行這個「歇業」制度就是為了在報表上好看一些,不讓停業或註銷的企業顯得太多。
愛自由
上海的張開宇、成都的莫先生名下企業的關閉,以及杭州葛平的子公司歇業與同一時期中國成千上萬民營中小企業在困境中掙扎、直至關閉的境遇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據港媒「香港01」去年底報導,企業徵信網站「企查查」的數據顯示,2022年截至11月底,中國有190萬家零售業企業關閉,同時有49.6萬家的餐飲相關企業註銷登記。而這些類型的企業都是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
但張開宇和莫先生這樣的服務、貿易類中小微企業遇到困境並不單是因為疫情及封控措施,早在疫情開始之前,他們就已經嗅到了經濟不妙的苗頭。
張開宇的店開在上海法租界的黃金地段,周圍街區都是粗大的梧桐樹,用他的話說,就是很有「老上海」的感覺。在2006年創業之前,張開宇也是在時尚精品行業打工。之所以自己開店,張開宇說是為了自由,「開了店以後,基本上每天就睡到自然醒,愛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並且每年都有三四個月時間到外面去旅行,那就非常自由。」
憑藉對行業的敏銳嗅覺和日積月累,張開宇的店在十年後迎來了自己的巔峰時期,「就是在15、16到17年那幾年,銷售額一年能到500萬左右,毛利率大概是在40%。」但到了2018年,張開宇的店就開始走下坡路。先是客戶群發生了變換,「以前有20%是住在上海的外企高管,就是外國人,但18年以後,這些人幾乎都消失了。那時候我們都感覺很奇怪。」
他同時發現周圍做生意的朋友也都出現了問題,「好幾個朋友就在那兩三年時間,居然都一一生意失敗、破產了,還有一個人跑出去躲債了;其中一個曾經做得挺成功的,在全國有近一百家連鎖店,也在那幾年就失敗了。」

疫情期間, 中共當局下令關閉非必需業務並要求人們在家工作後,一名男子在一家已關閉的時裝精品店外。(美聯社)
舒坦的日子
在成都的莫先生也是在2018年開始感覺到自己店裡的顧客群消費下降了。
和張開宇一樣,莫先生曾經也是上班族。2014年,因為偶然的原因,莫先生跨足到他並不熟悉的餐飲行業,在成都龍泉驛一所大學旁開了一家自助餐廳,賣70元一位的自助餐,「就是烤肉、小火鍋,日餐、西餐等等,種類比較多,價格又比較便宜,主要針對年輕人,什麼都可以吃得到。」
這家餐廳定位非常成功,一路順風順水,做到2016年頂峰時期,一個月的銷售額能達到60萬。莫先生很快又開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莫先生說,那一陣的日子過得很舒坦,「基本上不會愁賺不到錢,沒利潤等等,基本上每個店都在盈利,你不需要到處補窟窿。那個時候想法就活躍起來了,想去做個品牌,把品牌打出去,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到了2018年,店裡的生意就開始下滑了。莫先生首先從大學生們的消費上發現了變化,「店就開在大學旁邊,你明顯地感覺到大學生的零花錢少了。有時候我跟他們聊天,他們就說家裡給的零花錢在減少,不斷在減少,所以他們就必須降低自己的消費,而且你出來吃頓飯本來也不是剛需啊。」
走到分水嶺
但對於2018年生意這種變化的原因,張開宇和莫先生都有點後知後覺。
「18年的時候沒什麼感覺,因為生意這個東西有好就有壞,傳統行業嘛,有漲就有跌,但到了2019年是持續的不好,我也和一些同行去聊過天,所有人的反饋都是這麼一個情況,」莫先生是回過頭去看,才發現主要是經濟大環境的問題。
「總是覺得哪裡出了問題,但看新聞聯播,看中國的官方媒體,就覺得所有都是好的,」張開宇開始學習研究經濟學方面的知識,他找到的答案是經濟結構出了問題,「後來明白是房地產綁架了經濟,老百姓把大部分的錢都拿去買房,所以就導致內需不停地衰退。」
在很多方面,2018年並不像是敗相初現的年份。這一年中國政局平穩,習近平剛剛開啟作為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的第二屆任期;新就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是新人,包括栗戰書、汪洋和王滬寧等等,但外界並不認為他們以後會具備替代習近平的潛力。
而2018年的中國經濟相比於2010年代的其他年份並非特別差。關於中國經濟出現拐點的說法早在2012年就出現了。在2018年,中國經濟依然實現了預定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增6.6%的目標,似乎是差強人意。
但或許因為2018年恰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人們對這一年的經濟表現尤其敏感,媒體紛紛指出,6.6%的增速是中國1991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率;分開季度看,經濟增長率更是逐漸降低的,一季度同比增長6.8%,然後依次是6.7%,6.5%,和6.4%。
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就是中國經濟放緩的信號,但他們對此的解釋莫衷一是。有人歸結於這一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影響。也有人認為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不再適應日益複雜的經濟格局。曾在1990年代初預言過中國經濟崛起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廉·奧弗霍爾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在2018年出版新書《中國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分水嶺,除非轉化成更為市場化的經濟體,才能保持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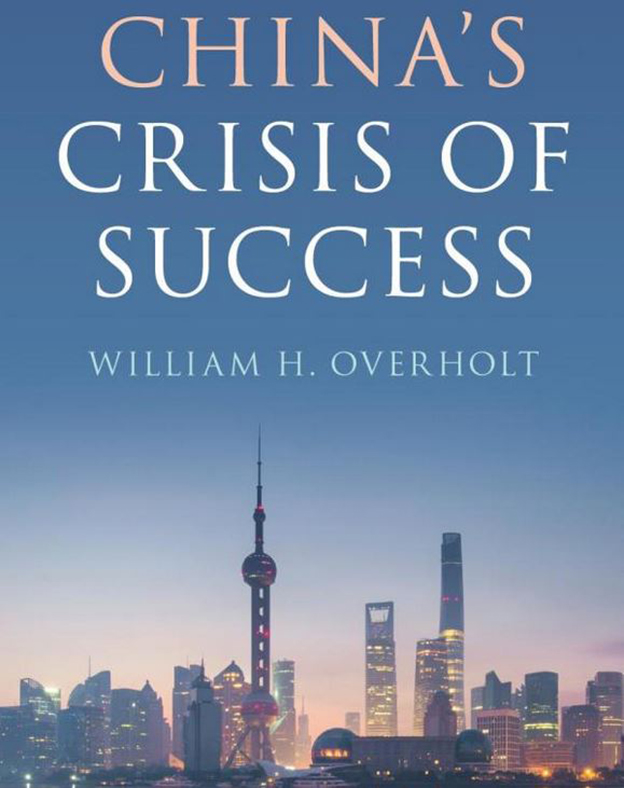
2018年出版的圖書《中國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封面。圖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廉·奧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分水嶺,除非轉化成更為市場化的經濟體,才能保持成功。(亞馬遜官網截圖)
避之唯恐不及
宏觀經濟下行的雷聲雖然還沒有逼到眼前,但張開宇和莫先生,一個在長江尾的上海,一個在長江頭的成都,不約而同開始收縮生意的規模。
張開宇在2018年就退租了一半的店面,「一個月把各種成本算下來,包括租金、員工,還有壓貨的成本、管理的成本,估計一個月能省個三四萬。」
莫先生則開始關店,「是陸續關的,因為不止一家,就是從2019年開始,一直到2022年,最後關閉的那家是2022年5月。」
經濟形勢雖然不好,但兩位老闆感覺自己所處的營商環境還過得去。雖然政府主管部門不時會對他們的經營有干擾,但他們總體感覺,無論上海,還是成都,在中國都算得上對民營企業比較友好的城市。
莫先生說,他做了幾年的餐館,雖然也遇到政府主管部門的刁難,但基本上都能躲過去,「反正中國就這樣唄,和他們打交道,說難聽點就是耍賴,說好聽點,就是要靈活走位,不要被他們粘到。一般情況下,我覺得還好吧,也沒有太為難你。」
他說的「沒有太為難」有好幾次:其中一次,餐館因為消防設施沒過關被開罰單60萬,但實際並沒有被征繳罰款;「包括環保也是,這不行那不行,天天約談你,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嚇唬嚇唬你,沒有非要你怎麼樣,可能會找點麻煩,但實際上沒有。」
但同時,莫先生也從成都市政府的政策中得到過好處。莫先生的自助餐廳因為在2018年成都美食節上贏得一個獎項,在貸款方面得到了優待,獲得了擴張品牌的一筆貸款。
同一時間在上海的張開宇則會為店裡不時受到不必要的行政干預而煩惱,「他的干預會很多,比如要求你的招牌要統一,店面方面的設計要按照他的審美來做,但你知道他們的審美是很糟糕的,本來是很好看的一個店面,會被他們弄得非常難看。」
陳開宇有些嘆息地說,自己的底線比較低,「中國人基本上都已經逆來順受習慣了,對這種事情,我們都覺得,只要它不來管你,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張開宇和莫先生對政府都是避之唯恐不及,而杭州的葛平從2018年創業開始,他的業務就和政府有緊密的聯繫。
保的都是頭部企業
葛平創業之前在企業里為人打工,做管理諮詢,創業後也主要是在這個領域從企業和政府拿諮詢類的合同業務。他為政府所做的業務中還包括維穩機制的諮詢,即防止社會惡性事件的政府反應機制諮詢。
葛平很清楚政府業務的門道,「特別是做政府諮詢這一塊,其實說到底還是權力尋租,這個業務他之所以給你,可能是因為你認識某個官員,他對你的專業性有客觀的評價,然後你也可以私下裡給他一點好處,做一點利益交換。」他強調,這一塊業務政府表面上也有招投標,但所有這樣的招標都是內定的。
憑著人脈和對行業風向的準確把握,葛平的公司很快在2019年就達到了行業的一個高度,「最好的時候,一年簽的合同大約有四十萬,就是指純收入。我們是屬於小微企業,在這一塊能達到區域內的前十。」
但無論是葛平這種與政府利益存在一定捆綁的諮詢企業,還是莫先生的餐飲企業,或張開宇的時尚精品店,在正常時期要戰戰兢兢地處理與政府的關係,而在面臨疫情來襲和政府一刀切的封控政策下,又都難以從政府獲得必要的幫助。
葛平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企業在疫情期間從杭州政府得到的救助太少,「我這個企業得到的唯一一個政策是在(疫情)爆發之後,有連續十個月時間,政府有減稅降費,降低了企業的營運成本。」
疫情期間,葛平的諮詢公司合同數減少了;因為地方政府缺錢,公司過去的一些政府合同也無法續簽。由於做諮詢的緣故,葛平對市場上不同企業的心態比較了解,「對於我們這種小微企業來說,從市場端看,這個信心從哪裡來?從多數企業的情況來看,疫情這三年,(政府方面)也沒有和我們企業主有任何溝通。」
政府的救助似乎離葛平們很遠,但離其他一些企業則比較近。在中國國務院2022年6月初發布的《紮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中可以看到,在融資、復工復產政策等方面,中央政府支持的都主要是重點企業。
《措施》中也提到,抓緊辦理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留抵退稅並加大幫扶力度。據中國官媒人民網今年初報導,2022年,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1.7萬億元,占全年減稅降費總額的比重約四成。但這些政策下去,三位在不同城市的小企業主都沒有感受到實際的優惠。
葛平則敏銳地察覺到這些政策背後的邏輯,「我個人的感知就是,最近一兩年政府也不裝了,他保的還就是一些頭部企業,比如說上市公司,還不算新三板的公司,就是A股上市公司,政府就是根據這個層級來的。」
傷筋動骨
實際上不同地方政府都有過一些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莫先生所在的成都在疫情前就有困難企業穩崗補貼的政策,莫先生旗下一家餐館的員工每個都曾得到一個月百元左右的補貼。這種政策在疫情三年期間都有延續。
但這些修修補補的政策似乎都難以挽救疫情封控讓企業無法正常經營的困局。
莫先生回想疫情這三年的日子,早已不復2016年巔峰時期的舒坦之意,「我在家裡待了兩個月,估摸著這一關肯定是有點難過了,也做好心理準備了,然後給家裡也交底了,就說這之後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行就行,不行就準備宣布撤了,不能再做這一行了。」
即使是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心,莫先生依舊覺得壓力無時不在,「因為每天你還要付工資,有那麼多員工,他們還是要吃飯的,對吧?」而且莫先生的房租即使在疫情期間還是以每年6%的速度遞增。
莫先生目前已經身在美國加州,他對中美兩國的疫情措施有很清晰的對比,「就是太久了,我當時以為封三個月就差不多放開了,但是真的沒想到這三年下來,讓人傷筋動骨了。反正我圈子裡不少人就是倒在這個地方,就是致命一擊,這一擊就是敲腦門兒!」
店主眼裡的社會面
在讓人惶恐不安的疫情封控下,莫先生看到的不僅是身邊生意人的倒掉,還有整個社會氛圍的裂變,「之前那些騎手都是大叔大媽之類的,後來就有很年輕漂亮的小女孩來送外賣了,而且一聊,好多都是高學歷的開始來送外賣,就是說整個就業狀況不是很好啊。」
從外賣騎手的身上,莫先生直接體會到中國社會真實的情緒,「我感覺到他們身上承受了很大的社會壓力,本來賺得又少,又沒有其他的活路,脾氣就很暴躁;單子又少,來得又快,就催啊,經常和我的員工吵架鬧矛盾。」莫先生不得不經常安撫他的員工,讓他們一定一定要忍住,不要和外賣員對著幹。

2023年3月20,外賣騎手在北京市一家超市外面等待訂單。(美聯社)
莫先生說他看到的這種情況在2021-2022年尤其嚴重。實際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隨著經濟的起伏,中國社會的就業情況經歷了大起大落。2021年不少地方復工復產,失業率一度回落,但從當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失業率再度走高。僅就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而言,在莫先生關閉最後一家餐館前夕的2022年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尤其青年群體(16-24歲)調查失業率高達18.2%(2023年4月,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20.4%)。
面對逼仄的經濟空間和日趨惡化的社會形勢,手裡有點積蓄的民營企業家似乎有更多的路可走。張開宇從自己身邊接觸的富人階層觀察到,「整個社會最有活力、最有錢的那些人,我說的是通過正當經營做得非常成功的人,這些人其實是整個經濟的發動機,這些人是最有能力離開的,而且是最有意識離開的,這些人我覺得正在離開,或者是已經離開。」
但在他看來,這只是極少部分人的選擇,「對於大部分普通的店主,或者說中小企業家,他們其實是離開不了的,只能在這裡掙扎,掙扎著生存。」
張開宇和自己的貓於2023年3月遷居到了美國加州,雖然當時中國已經結束了清零政策,但他依然充滿了失望,「他解除這個政策也並不是因為他從全世界學到了什麼教訓」,他仿佛很高興自己說透了這個秘密,訕笑了兩聲,又說到,「他只是因為沒錢了堅持不下去,或者是老百姓反抗太厲害了;他根本不是出於一種理性,關注到老百姓的健康,或者是基本權利生存權等等。」
葛平在杭州看到的社會面就是老百姓的反抗。2022年11月27日晚,白紙運動在全國鋪展得最廣泛的那個晚上,葛平跑去了杭州白紙運動的現場,靠近西湖的蘋果電腦店前,「到後面,那些年輕人,包括一些女生,完全是一種『沖塔』的姿態,八點鐘之前,他們(警方)所有的包圍圈都已經布置好了,包括他們的領導就按照這個時間,還有一輛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還是有一些年輕人去沖塔。」
在這場中國多年未見的社會運動中,葛平看到了社會的希望,同時他從維穩體制的角度有一個新的發現:各地方政府在處理這個事件時也在躺平,「為什麼白紙革命在幾十個城市發生,其實在這個當中,在維穩機制當中,當時他們是存在懈怠的,包括後台的網安數據我們也看得到。」他認為,這也體現了某種社會的進步。

2022年11月27日,抗議者在北京街頭舉起白紙反對中國政府的防疫政策。(美聯社圖片)
「倒查11年」
白紙運動席捲全國後,中國政府迅速在去年底結束了疫情封控政策,到今天已經半年有餘。中國社會似乎正慢慢走向正軌,療愈疫情封控三年造成的傷害。
來自成都、上海和杭州這幾個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城市的三位小企業主都已經對自己的命運做出了安排。莫先生說,他跑到美國就是來躲債的,他已經不願談對餐飲業未來的展望,「說實話至於什麼時候能恢復,我根本就不想關心這個事。因為我已經不在這個行業做了,其次我人也不在國內,關心也是瞎關心。」
張開宇則有些擔憂,他的母親前不久在國內中風,躺在重症加護病房不能說話,但他的妹妹告誡他不要回去。葛平說會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暫時接不到業務;自己的公司還有六名員工,雖然虧著錢,也要給他們發工資。
國內民營企業的信心普遍沒有恢復。中國政府似乎也明白民營企業這種處境。近幾個月以來,各地政府接連召開與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就在7月初,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鄭柵潔與三一集團、農夫山泉等5家民營企業的負責人會談,想聽取民營企業的真實情況和相關政策建議。
但小業主們看的卻是實際發生在民營企業身上的事情。「稍微有點理性的人都知道,這個環境已經到了非常惡劣的程度,」張開宇這樣感嘆說。
2020年底螞蟻金服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叫停,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這一輪打壓民營企業的標誌。而就在今年7月7日,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宣布對螞蟻集團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71億元人民幣。
今年二季度,國家稅務總局廈門市稅務局對當地的陶鄉餐飲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5年的偷稅行為追罰1425萬元。網友以「倒查11年」的標題在網上傳播這一消息,充滿了警示的意味。
這些做法看似有法律和政策的依據,但張開宇說,他對政府種種的舉動看不到邊界,「關鍵是他可以任意地運用他的權力,想讓你生就生,想讓你死就死,沒有任何法律的界限。」
與政府經常打交道的葛平則認為,對中小民企來說,經營環境很難發生實質性的轉變,「現在是政府給頭部企業站台,但站台之後,這些頭部企業能不能生存?比如這些房地產企業,他們的問題能不能得到解決?頭部企業都不好的話,那你指望中小微企業變好,這個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
葛平還在高校為大學生做創業輔導,但他對目前的創業環境持否定態度,「目前的市場環境,我要給一個建議,就是風險太高了,政策支持太少了,就如在疫情期間,那你對創業者有什麼支持呢?沒有任何支持,就是讓他們自生自滅。」
我們的活法與我們的期待
但在經歷了白紙運動後,葛平卻對中國社會自身的力量有一種別樣的樂觀,「目前來講,民智已開,只是要更多地去認識歷史,特別是要認識中共的國家機器是怎麼運作的。」
他暗示地說,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要認清自己所在的階層和對生活的期待,「官二代或富二代有他們的活法,但我們普通人,無論是做技術的,還是打工的,或者是做商人也好,我們要有我們的活法,我們要有我們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