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一年多來,各地醫院的產科陸續傳出被關停或合併的消息。與之對應的是,2023年國內出生人口902萬,和2016年放開二胎後的生育高峰相比,產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萬。
2月28日,知名婦產科專家段濤公開呼籲,「救救產科!你們擔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擔心的是產科學科的塌方。」一時間,網友開始辯論起到底是產科,還是重壓下的年輕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囂聲中,作為一個最早感知到出生率變化的行業,有一批人已經被輕輕撥轉了方向。
基層產科靜悄悄
事情發生前總有預兆,王晴早有察覺,也做了一定心理準備。但過年後返崗,聽到科室主任宣布,醫院產科即將停止服務,那一瞬間,她還是覺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歲,是某一線城市一家二級綜合性醫院的產科護士,已經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後,同事們起初還開玩笑,「我們醫院的出生證明以後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婦建檔工作停止,之前訂購的、藥廠還沒來得及發貨的產科用藥都陸續退了,再後來,護士長說剖腹生產包,還有其他無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識到,「我真的見證了(我們醫院)產科即將落幕的歷史時刻。」
幕布當然不是在瞬間落下的。大約是一年多前,產科的工作已經很不飽和,她開始兼任部分內科的工作,給老人拿降壓藥、打點滴。2023年的最後幾個月,產科每月的接生數量跌至個位數,到今年2月,產科宣布關閉前,「我們只接生了一個,然後就沒有了。」
在廣西東南部某鄉鎮衛生院,助產士梁麗娜「今年還沒有開張」。過去15年,她一直在這裡的產科工作,同時管理醫院的接生登記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記本上的名單越縮越短,「以前每個月最低都能有30多個產婦,能保證至少每一天都有一個新生兒。」後來這個頻率變成幾天,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如今婦產科唯一還算熱鬧的時段是早上,偶爾有人來做檢查,「到下午基本上沒有什麼人過來了,整個醫院都是靜悄悄的。」
臨近幾個鄉鎮醫院的情況也算不上好。醫護人員有時在一起開會,交換各自的信息,梁麗娜知道隔壁市另一個鎮上的衛生院前兩年已經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婦科和孕檢。還有相鄰的一個鎮衛生院,因為配備了麻醉師,能開展剖腹產手術,周圍幾個鎮上的居民都願意過去生產,「最高峰一個月都有一百多個,去年開始直接跌到一個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個左右。」
梁麗娜工作的衛生院不大,只分三個科室,綜合科、婦產科和中醫科。她估計,再過一段時間,婦產科就要和中醫科合併了,「還沒有正式通知,不過我們主任都在討論了,也沒有必要單獨保留產科。」
過去幾年,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多個醫院的產科重複上演。《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數據顯示,2019年到2021年,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減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來,公開宣布暫停或合併產科業務的醫院數量,至少有9家。
這些醫療機構絕大部分是二級綜合性醫院和一級基層醫院、衛生院。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說,在出生率不斷下跌的情況下,目前最受影響的也確實是一二級醫院,「三甲醫院畢竟有好的醫生資源,還是能吸引大多數病人。」
即便是三級頭部醫院,依舊能感受到危機。段濤說,2016年二胎剛開放時,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全年分娩量達3.4萬。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被稱為上海的「大搖籃」,分娩量連續8年位居上海第一,「現在一年差不多2萬5(例),上海過去一年新生人口20萬,現在連10萬不到,我們這個分娩量已經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我們下降這一點,其他醫院受影響的肯定會更大。」
前段時間,段濤和浦東新區的產科主任開會,大家的討論重點是「產科轉型」。他記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產科主任發言,說自己所在的綜合性醫院要重新裝修,一向不滿意產科的院長趁機關閉了整個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濤也很無奈,「他們幹這一行幹了十幾年,花了多少時間精力,轉行又轉去哪呢?」
開完會沒多久,段濤寫下了那篇「救救產科」的長文:「如果再不改變現狀……產科整個學科可能真的就會出現塌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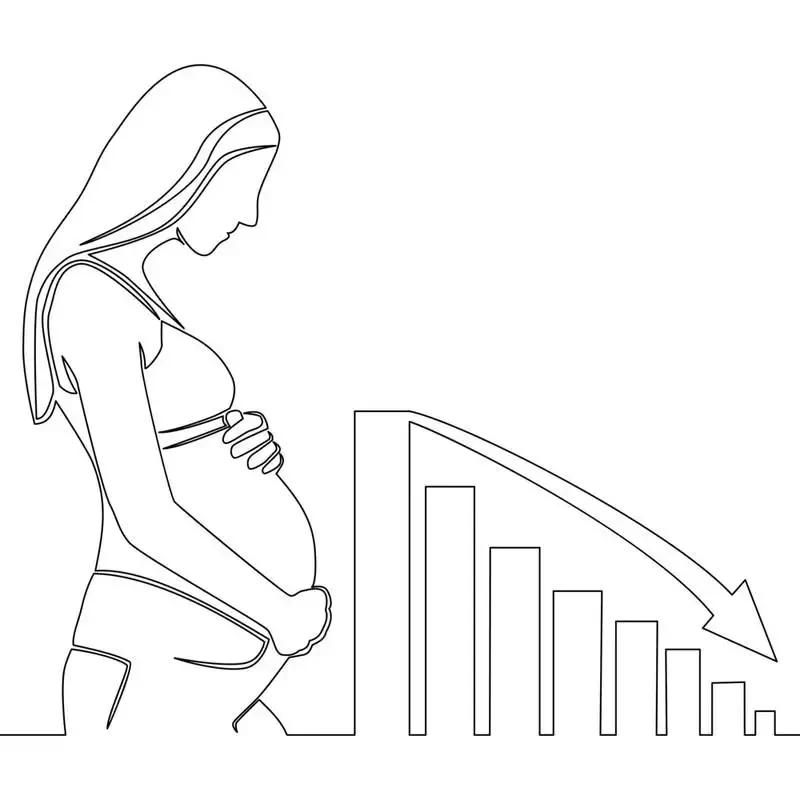
從高峰滑落
段濤還記得產科巔峰的時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開放,那年全國新生人口1786萬。段濤所在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有90多名產科醫生,一天得接生近100個孩子,還得查房、寫報告、病歷。當時醫院裡有個說法叫「閉經指數」,指的是年輕醫生在各科間輪崗,每次輪到產科,忙得月經都不來了,到了婦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線城市,產科護士王晴畢業時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醫護一樣,她印象最深的是產科的樓道,「因為生孩子的太多了,樓道里都塞滿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樣,「我們科有兩個產床,經常是我們在裡邊接生,待產室里還躺著好幾個已經陣痛、準備生產的孕婦,一晚上可能就要出來五六個孩子。」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不少數據機構預測,和過去相比,開放後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過200萬,且未來幾年出生人口將保持增長態勢。
2016年最終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萬新生人口。但那時大部分醫院產科床位已經處於緊缺狀態,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決「建檔難」和「一床難求」的問題,2016年下半年,原國家衛計委要求,在縣級醫院新增產科床位8.9萬張,三級醫院可以將特需病房調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時爭取在「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產科,家長們推著嬰兒車排起長隊,等候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
高峰沒能持續太久。「2017年開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能感受到變化,」段濤說,「但影響是有延遲效應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萬,後續的負面效應都集中凸顯出來了。」
王晴和梁麗娜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所在醫院的分娩量從2017年底開始有下滑趨勢,當時主要因為原國家衛計委從2017年7月開始,陸續在各個城市推行《孕產婦妊娠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規範》。
二胎開放後,多家醫院反饋,高齡產婦比例上升至20%,而過去這一數據在10%左右。《工作規範》按風險嚴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綠、黃、橙、紅、紫」5種顏色對孕婦進行分級。王晴說,她所在的二級醫院之後都不能接診橙色級別以上的孕婦,「當時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擊來自出生率的持續下降。梁麗娜回憶,大約從2021年開始,她所在的鄉鎮醫院肉眼可見地空了。這一年國家開放三胎,但新增人口從2020年的1200萬,跌至1062萬。梁麗娜所在的鄉鎮離市區大約十幾公里,不算遠,且交通發達,產科床位不那麼緊張後,很多人會選擇開車到十幾公里的市區生孩子,「求的就是一個安全。」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經到湖北省兩個鄉鎮衛生院進行調研。據他統計,一個鄉鎮一年僅有200左右新生兒,「新生兒的數量從根本上決定了產科的發展空間。」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鄉鎮衛生院婦產科變得靜悄悄是資源集中與利用的表現,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下的優勝劣汰,在全國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對鄉鎮、村莊的各種資源進行整合。
但他也寫道,「資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後應該怎麼辦?沒有補充力量進入,農村女性想要看婦科病、想要做產科手術只能去縣城,結果是『看病越來越難也越來越貴』,這與我國長期堅持的醫改方向與目標是相矛盾的。」
段濤也提出,「中國人口的出生數量有一半以上是在縣級及以下醫院的,產科的就醫半徑還比較短,不像看腫瘤做試管嬰兒,可以全國跑。特別是孕程後期,她們每一到兩周就要做產檢,你不能讓全縣城的孕婦都從鄉鎮跑到縣裡生孩子,醫療的可及性就沒了。」
「產科以前那麼忙是不正常的,產婦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時不時傳來的關停消息,同樣讓段濤感到憂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將生二胎的媽媽。
被「嫌棄」的產科
梁麗娜從去年開始就沒有領過績效了。身邊很多同事都在考慮下班後做點副業。「有同事出去擺攤賣東西,我們很多護士就找點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裡做,每個月多幾百塊錢。」
她也問過家樓下製衣廠的老闆,自己能不能幹一份兼職,但被拒絕了。老闆擔心她在醫院經常值夜班,遇上工廠趕貨,也抽不出時間來幫忙。
過去生孩子的人多,醫護人員能拿到的績效也高,當時梁麗娜一個月工資能有6000多元,在鄉鎮是個不錯的水平。她有編制,現在每個月工資還能維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們醫院的契約工每個月才1500,還要租房、吃飯,他們也覺得做得沒有什麼意義。」
過去半年,她所在的產科已經有三位醫護人員離職。
在她的觀察里,婦產科一向不是醫院的發展重點。她所在的鄉鎮級別醫院自然分娩的醫療費是230元,「我們一個產包進貨價是九十塊錢,包括棉簽、一次性墊布之類的,還有一個接生包,就是產鉗、剪刀,用一次折舊價算幾十塊錢,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塊錢。」加上整個孕期要收取的各類產檢費用,梁麗娜說,醫院接待一個孕婦,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婦產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說,如果產科月分娩量無法達到50個,就難以覆蓋整個科室正常的營運成本。超過100個,科室的運作才處於良好狀態。
出生率下降後,產科的營運壓力首先暴露出來。段濤說,在所有科室里,產科收費是偏低的,順產費用通常是幾百到一千元,剖腹生產稍高,能達到兩三千元。「但維持產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點人,產科24小時都要有人,很多產婦都是晚上發動,產房醫生、麻醉醫生、助產士、護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碼得有幾十號人。」
而對於三級醫院來說,還有另一重壓力。2019年,國家衛健委啟動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工作,鼓勵大醫院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指標是CMI指數(醫院收治病例的疑難危重度),和四級手術(最高級別)。
段濤認為矛盾的地方在於,產科的原則是保障母嬰安全,把母嬰併發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產科做得好的時候更多的是順產,預防工作做好了,就沒有各種併發症,CMI指數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級手術。要醫院指標好看,那遭殃的就是產婦。」
段濤感嘆,「醫學的學科不像養豬,你能在一個比較短的周期很快做決定,成本不需要那麼高。但你要培養一個好的醫生要花多少年?十幾年吧。現在出生率又越來越低,產科不掙錢,能獲得的投入會越來越少,醫生的機會也少,沒有人願意做產科,以後產婦有個突發情況,誰去做手術?」
他擔心未來有一天,產科也會重複兒科那樣的命運。「少子化這是個大趨勢,但如果什麼都不做,產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體往坑裡掉了。」
3月27日,國家衛健委發布《關於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產科服務兜底責任。其中還提到,要努力使綜合性醫院產科醫師的薪酬水平不低於醫院醫師平均水平,嚴禁向產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指標。
在段濤看來,這是一個積極信號,「但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醫院每天都要算帳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實多少?」

段濤的微博圖片來源網絡
另尋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時候都在內科工作,一個月前,醫院已經正式發出公告,「停止助產技術服務與產前篩查技術服務項目」,之前已經建檔的產婦將陸續分流到周邊其他醫院。王晴說,後續醫院應該就要處理嬰兒床、改造病房,產科的帷幕要徹底落下了。
內科的工作很飽和,病人從來沒有斷過,她發現許多老人用不了兩三個月,還會再來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來,她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失業危機了,畢竟人們可以不生育,卻無法避免衰老。但也說不好,她猶豫了下,8年前她剛進入產科時,也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失業,「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會面臨生孩子這個問題。」
她感慨,「以前做產科,現在干內科,這不就是一個從新生走向死亡的過程嗎?」唯一值得高興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漲回來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時候,她一個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麗娜能理解如今年輕人不願生育的想法。她36歲,有兩個孩子,婆婆有時還會催她再生一個。她說如果三胎開放時間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慮生,「那時候才三十出頭,家裡也還有點積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現在經濟壓力大,養兩個孩子已經很累,「折騰不起,打死都不會生。」
梁麗娜喜歡助產士這份工作,「我想著可以干一輩子,而且看著新生兒出生,感覺真的是挺偉大的。」每次嬰兒哇一聲哭出來,就是梁麗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她嘆氣,「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婦產科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醫院產科分娩室迎來龍年第一個「龍寶寶」出生。圖為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為「龍寶寶」敲腳印。
一些年輕的醫學生在掙扎。浙江某醫學院,一位婦產科專碩研究生入學時就規劃好,畢業後就回家鄉鎮上的醫院當一名產科醫生,壓力不大又安穩。然而兩年後,2023年6月,父母告訴她,鎮上衛生院的產科被取消了。
內蒙古一位助產專業的學生說,剛上大學時,所有人都跟她強調助產士稀缺,她因此放棄轉換到檢驗專業,如今即將畢業,「結果我現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將護理學、助產學調整為國家控制布點專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專業,被列入國控專業的通常是市場需求量已經飽和的專業。
31歲的趙慧子鬱悶了好一段時間,她在某二線城市的醫科大學讀產科博士。2023下半年開始,她發現學校附屬醫院的產科病人越來越少,病床經常住不滿。但年初她決定讀博時,產科的情況還不是這樣的,「沒想到之後我可能要失業了。」
趙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醫院的產科招聘信息,希望儘早做好準備,「從招聘人數上看,這幾年一直是縮減的。我家鄉有些醫院,以前可能一年招兩三個,現在基本都不會招了,對學歷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現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認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郵輪已經開到了大海中央,沒辦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勵自己積極起來,「我讀博也還有機會轉成科研崗,還有一些師兄去到專科院校當老師,還有醫藥生物公司,醫學翻譯。」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來。
最後,她只能安慰自己,「我們學校還不錯,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都還找到了工作,應該不會那麼糟糕。」
(除段濤外,文中其餘人物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