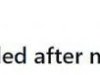2021年,李霖剛剛研究生入學,她的電腦瀏覽器里有一個資料夾,裡面是自己關注的實驗室信息——未來,她希望能前往這些實驗室受訓,以聯合培養或做博後的方式。
三年之後,博士在讀的她在申請CSC(國家留學基金委獎學金項目)時,把資料夾拉出來,發現「沒有一個能去,因為都在美國」。
「我的專業方向是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這個方向在美國最發達,研究也更前沿,做這方面的老師也最多。當時我收藏這些實驗室,根本沒有關注政治背景,注意力都在學術成果上」,李霖說。
目前,李霖已經放棄了短期內去美國做學術的想法,積極聯繫導師的她進展並不順利,發出30多封郵件,涉及國家有英國、瑞士、丹麥、德國、義大利、荷蘭和比利時。在李霖收到的回覆里,丹麥奧胡斯大學、哥本哈根大學、德國馬普所目前都拒收CSC資助的學生。
一位老師在拒信中寫道,"absolutely,maybe times change at some point."(當然,時代也許會在某個時刻改變。)
「我聯繫的老師中,他們中大多數對這個政策(拒收CSC)是否定的。一位德國老師回信給我說,抱歉回復晚了,因為他得知現在關於國際交換留學生的政策變了,他在後面打個括號,裡面是alas(嘆氣),感覺他們也很無奈」,李霖告訴《知識分子》。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逾八百萬名學子跨越國界,尋求知識和合作,豐富了全球科學共同體的多樣性和創新力,助推國家命運的巨變。
「學術振盪」是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學者的共同記憶。正是這些學術先鋒的遠見卓識與不懈追求,創立和改造學科、引進編寫教材、教學方式革命、開展國際學術交流……使得中國的科學體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漸完善,展現了學術探索的深度與廣度。
然而,當下延續四十年的人才流動大潮正無聲地關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門,自由擁抱世界成了一段歷史的特殊景觀。像李霖的名單一樣,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斷抬高留學審查門檻,機構、大學、院系參與其中。時代浪潮反覆撥弄著個人命運,學術血管正以最小的單位被切割。

有的審查以年為單位起步 也有人中途被退學
李霖遭遇的CSC項目被拒只是中國留學生出國交流遇阻的一個切面。在《知識分子》收集的案例中,留學生們還面臨因學科或者學校「敏感」無法拿到offer,也有人拿offer後無法通過簽證審查,有人的審查成為無限期的等待,有人遭遇中途退學。
「據我了解,申請加拿大的簽證時,安全調查甚至以一年起步,上不封頂,有人甚至等了6年都沒等到」,盧波介紹,他目前在德國讀博,量子計算方向,此前他的學術生涯因等待簽證審查中斷了兩年。
這些接受訪問的留學生中,他們大多接受了初步的學術培訓,不少人考慮以學術為志業,但浪頭迎面打來時,他們不得不在慌亂中調轉方向,滑向另一個軌道和人生可能。
拿到全獎的羅真一直沒能在線下見到導師,儘管他已經讀了一年多的博士課程。從2020年之後的這一年時間裡,因為疫情,這位直博生一直都在線上參與課程實驗。
2022年1月美國放鬆COVID-19管制措施,各個方向的交流也逐步恢復,其他學生在前一年12月完成註冊,但羅真始終未能拿到簽證。他才意識到,是因為疫情之初美國頒布的「10043號總統令」。
該政策禁止與中國「軍民融合戰略」機構有關聯的個人赴美學習或研究。羅真畢業的學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中。
早在2001年5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便成為首批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高校;此後,電子科技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也陸續被列入其中;2018年之後,隨著美國對華科技封鎖加劇,「實體清單」上的高校數量迅速增長,到2020年12月高達18所。而「國防七子」,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理工大學,比實體名單上的其他大學受到了更嚴格的出口管制。除此之外,「兩電一郵」也享受同樣規格的審查。
2022年1月,羅真收到退學通知,他被告知不能繼續等待,必須馬上結束學業,同時,學校不會頒發學位證書,甚至還向他索要過去一年多2萬多美元的學費。在導師的據理力爭後,他拿到了碩士畢業證書,沒有支付學費,但也沒拿到最後半年的助教助研費。
羅真最終還能收到一份碩士文憑,但還有一些中途被退學的學生,什麼都沒獲得便遭遇遣返,僅僅蹉跎了光陰。
2023年1月的凌晨,馮展從香港轉機紐約。這是她疫情三年裡第一次回國,與家人匆匆團聚7天,又飛回實驗室完成博士學業。六年的留學生涯即將結束,她距離完成科研訓練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但她遭到了巨大的打擊。
櫃檯的喇叭傳出聲音,她被要求停止登機。機場的突然襲擊,對於近些年穿越中美邊境「敏感」專業的科研人員來說,堪稱家常便飯。
《知識分子》訪問了一些有類似「被盤查」經歷的博士,一些人從行李提取處被叫到一旁盤問數小時,也有人被叫去所謂「小黑屋」。
「當然,小黑屋並不是黑色的,我去的是一間有玻璃門窗的大房間,裡面有幾條長椅,坐著十幾個人,在裡面你不許使用手機」,一位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留學生告訴《知識分子》。
學生們遭遇的盤查問題大多如下:讀博資金來源主要是誰提供,是否涉及政府資助,父母的職業背景,專業研究方向,導師的背景,是否涉及合作方,合作方背景,論文的合作者背景等等。學生們的紙質文件,包括論文、筆記都會被仔細翻查。盤查者們翻閱學生電腦、手機和硬碟中的論文和資料,在字詞之間找尋「可疑的證據」,並反覆質詢。甚至涉及個人隱私的聊天對話、照片和論壇發言也會被審查和提問。
為了應對盤查,一些學者和學生們總結了應對經驗,準備空白電腦和手機以備檢查,為了逼真,時不時還登陸上去,留存些使用痕跡。
馮展並沒有這樣的經驗,就算有彼時也無濟於事。航司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她的簽證出了一些問題。她不能理解所謂的「問題」是什麼,她的學生簽證仍在5年有效期內。在香港機場,她反覆和美國海關溝通,對方沒有給出明確的理由,只是讓她回去等待消息。
第二天,馮展收到了簽證被撤銷的郵件。沒有檢查行李,沒有盤問,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一個在有效期內的簽證怎麼會被撤銷?」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具體的回覆,經過和同樣情況的學生交流和信息檢索,大致才鎖定為「因為本科學校在制裁清單上」。
時代的塵埃終究還是落到了馮展頭上。
在過去的學術道路上,馮展並非沒有感知到來自政治的擠壓,但她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幸運」。2018年,美國收緊了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政策,將敏感領域(航空、機器人、先進位造等)的簽證期限縮短為一年,並需要每年重新申請,此舉推翻了歐巴馬時代允許中國公民獲得五年學生簽證的政策。而就在這一年,馮展從「國防七子」畢業,開啟了自己的留學生涯。幸運的是,她拿到了五年學簽,躲過了政策收緊的影響。
2020年5月,「10043號總統令」的頒布,「軍民融合」的指控讓馮展的學弟學妹們無法辯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美國留學的大門關閉。此時馮展已經身處美國,暫時逃脫了地緣政治的漩渦。即使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混亂時期,她的研究也沒有中斷。按照原計劃,她將在今年下半年學成回國。但命運似乎並不打算繼續眷顧她,甚至讓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不僅馮展對簽證撤銷毫無準備,在那時(2023年年初),她在美國的博導、國際處的工作人員也都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後來,她才發現自己並非個例,光她認識的在返美途中被撤簽的就有五六個人,其中還有博士後,本科學校的背景都指向「國防七子」。
許多在美中國留學生提及耳聞與馮展類似的遭遇,他們對此的應對是,「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的幾年裡儘量不要回國」。
撤簽發生後,馮展想過其他辦法以延續在美國的學術計劃,但都失敗了。她實驗所需要的數據必須本人在校才能使用;她也無法提前申請畢業,因為還未達到畢業標準。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堵住,她決定退出博士項目。唯一令她感到惋惜的是未完成的課題,過去幾年為之付出的激情和汗水全部白費。沒能完成的原因,也並非她個人能力不濟。
博士三年從她的人生中被抽出、劃掉,她等了一年,選擇了國內的博士項目。「我導師和北美有很多學術交流,原本也可以推薦我過去,但加拿大安調的時間太久,也有一定概率會拒簽。我不願意再承擔這樣的簽證風險,也希望有更多機會和家人相聚」。
目前,她已經掉頭重新開始新的方向和課題。
一年前,她遠程處理了在美國公寓的行李和車子,匆匆抹去自己在這個國家的痕跡。就如同對方所做的那樣,有一隻手在一份文件上,刪去了她的名字。
迅速升高的水溫
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如果本科或研究生畢業的學校在制裁清單上,或者專業「敏感」(其中最明顯的是計算機、數學、生物、化工、航空航天等專業),那麼美國可能已經是留學交流「不可去之地」。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學院教授Paul Evans在2022年的一篇研究中提到,在美國,與中國學術交流的禁令更多來自政府高層。據《知識分子》了解,囿於資助和審查,大學和教授更多被動捲入其中,成為參與者和被審查對象。
Paul Evans告訴《知識分子》,相比美國,加拿大進入研究安全領域遲緩一些,如今,越來越多的大學受到多重壓力,成為研究審查的參與者。
「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加拿大部分地區自2018年以來,尤為關注安全議程」,Paul Evans指出,「因為大學曾是我們與中國接觸的主要渠道之一,從1980年以來,加拿大與中國的機構和研究人員展開了長期交流,且規模巨大。因此,媒體、公眾和議會都參與對大學的施壓,導致對學術交流的新審查。」
近年來,除了面對大學越來越嚴苛的審查外,申請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最常遇到的問題則是安調時間越來越長。
「當時我加了很多留學生申請交流群,其中包括加拿大。我問群主,加拿大安全調查怎麼樣,好不好過?他說,別來,快跑」,盧波向《知識分子》提到自己的申請經歷,他的方向是實驗量子計算方向。
2022年,盧波相繼申請了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美國、瑞士、西班牙、丹麥、新加坡等地的實驗室,一部分學校發來了offer,但因為多國簽證政策限制,他不得不延後兩年入學。
也正因這段經歷,盧波搜集了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留學政策,也加了許多簽證交流群,他清晰地察覺到水溫驟增。
2020年和2021年,英國提出擴大ATAS(學術技術審核計劃)的要求。該計劃在2007年推出,中國學者或學生如果前往英國研究或學習敏感項目,需要通過審核。
「我可以說是第一批感受到ATAS政策收緊的人。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覺得審查就是走過場,幾乎不會有人被拒。甚至在政策收緊後,第一時間出現的經驗分享都只是介紹如何走流程,用什麼格式填個人信息云云,而關於ATAS真正最重要的如何避開敏感點,減少風險的經驗卻鮮有討論。或許是因為早期沒有人有這方面經驗。政策突然收緊後,大家都沒反應過來」。
不僅僅是學生,給盧波發offer的英國導師在當時對此也毫無認知和準備。
「ATAS認證中有這樣幾個問題,你為什麼會對這個方向感興趣?你畢業之後打算做什麼?我是這樣寫的:我做這個是為了未來製造大規模量子計算晶片;同時,我還講述了這個領域多麼高精尖,以及如何推動人類技術發展。對於畢業之後的打算,我老實回答,打算回國工作。兩個月之後,我被拒絕了。」
「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英國的導師。他說,『是不是你吹得還不夠狠,你要不再補充一下,比如我們這個項目是英國國家量子計算的發展計劃,得到了英國政府支持,是我們重要的尖端科技支柱產業。』但當時我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別人都嫌不夠低調,他還覺得我吹得不夠。」
盧波花了10個小時給導師寫了一封郵件,通過介紹全方位的統計數據,還有其他人的經驗案例,告訴對方ATAS的現狀是什麼。「他說去了解一下,然後告訴我,很遺憾,據他所知,第一次過不了ATAS,之後基本沒有可能了,不過他們以後會注意。」。
此後,盧波又申請了法國的實驗室,對方給了口頭offer,「後來他還是拒絕了我。我打破砂鍋追問到底,對方說,我們組很想給你offer,可惜學院沒有通過,或許是因為這幾年量子計算比較敏感吧。」
在申請過程中,盧波也嘗試申請了美國的實驗室,拿到了全獎offer,但他最終在選擇offer時還是放棄了。「這是有先例的。我在歐洲讀的碩士,當時有一個學弟,他本科原本跟我同一屆,然而拿了美國的全獎Phd後,不幸簽證被卡,耽誤了一年轉到歐洲,才成了我的學弟。」
同時,對未來的不可知也讓盧波作出放棄美國offer的決定。他曾聽說過類似馮展的案例,一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讀了四年博士,即將畢業時,因為所學專業突然被劃為敏感專業而遭遇勸退。「這個案例最讓我害怕的是,就算現在過了簽證審查,也難以保證讀博的五六年間不會中途因為形勢惡化,回國過海關等因素而突然導致前功盡棄。」如此的不確定性讓他倍感憂慮。
盧波最終選擇了德國實驗室,「相比其他國家,德國不太卡傳統理工科領域,甚至量子計算等一般意義下的超敏感方向也能通過,只是各國卡的點不一樣,例如德國偏偏明確限制了中國留學生學習人工智慧。」
此外,CSC被拒範圍逐步擴大。2023年,瑞士、丹麥、德國等多地高校不再招收中國CSC學生。李霖的朋友去年還通過CSC申請去了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而據說今年該校已經不再招收CSC資助的申請者。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長聘副教授沈文欽長期關注中國留學生教育,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也證實了留學目的地的結構轉變。以廈門大學為例,2019年該校本科畢業生出國出境深造占比最高的6個目的地分別是美國(29.8%)、英國(27.2%)、中國香港(14.2%)、新加坡(5.6%)、澳大利亞(4.9%)和日本(4.4%),但到2022年轉變為中國香港(30.1%)、英國(18.1%)、美國(17.9%)、新加坡(10.3%)、日本(5.3%)和澳大利亞(4.5%)。
在一些學校,新加坡甚至成為留學的第一目的地。例如湖南大學2023年去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留學人數達46人。沈文欽介紹,吉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也出現了前往新加坡留學人數激增的現象。
學術基石遭遇破壞
留學生們似乎總會找到接受自己的地方,這需要足夠的機敏、靈活的策略還有更多的金錢和時間投入,談不上完全沒有選擇。但對於部分學科的學生而言,每一條道路自有其附帶的價值,其中的得失利弊很少被看見和討論。
「10043取消無望,郵七出身還有多大機會走學術道路?」,這是一篇留學論壇中的高贊討論,發起者是一位被迫放棄美國、歐洲在讀的博士,他的糾結和困惑如下:「歐洲的科研規模相對較小,資金也較為緊張;整體研究氛圍比較輕鬆,不喜歡追逐熱點或偏向應用領域的課題。與此相比,歐洲科研人員在發表論文和引用次數等量化指標上,競爭力往往不及美國」。
「此外,歐洲的華人社群規模較小,信息交流沒有北美或亞洲的華人社群那麼頻繁和緊密。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取得了傑出科研成果的博士生,大多都有在北美學習或交流的經歷,這段經歷對他們的科研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學術競賽的隱憂困擾了很多人。羅真最後拿到了一個英國實驗室的全獎項目,但比起美國,他並不滿足於目前的科研環境,「美國會更卷一些,可能會不自覺地推著人向前走,但歐洲更講究工作生活平衡,導師覺得只要寫完畢業論文就可以畢業」。他繼續跟著美國的導師做項目,希望能夠彌補與自己未能留在美國的遺憾。
從博士生、博士後、講師到副教授、教授,不同科研階段受地緣政治波及的程度並不相同。沈文欽強調其中年輕學者所受影響更為顯著。他解釋說,資深學者通常在國際關係出現重大轉變之前,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學術資源和資本。這些學者的緊密學術網絡往往是基於長期且深入地面對面交流建立起來的,而海外的訪問和學習經歷則是積累社會資本和建立信任關係的關鍵途徑。
沈文欽進一步指出,歷史上的交流經驗告訴我們,博士生涯中的導師、同門以及導師的其他學生等,都有可能發展成為強有力的合作夥伴。相比之下,年輕學者在政治環境變化面前往往處於不利地位,他們在科研生涯的早期階段可能未能完成必要的跨國學術和社會資本積累。
(為保護受訪者,李霖、羅真、馮展、盧波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