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線小城裡,留學生在體制內貼錢上班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回國發展。比起在一線城市的辦公大樓當白領,回家、考編、進體製成了更為吃香的選擇。
哪怕是老家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還不及留學每月生活費的十分之一。
今年過年,在老家國企上班的時一就被同學們頻頻問起:為什麼留了學,還是選擇回來躺平?
「只有到一線城市裡苦哈哈地生活,人生才值得嗎?」她很想反駁回去。何況,她也沒有「躺」:街舞、滑板、考證、做家教……
體制內的工作充滿勾心鬥角,但工作8小時外的時間都是她的,想怎麼利用都可以。
小鎮中產家庭的子女們,通過高考、留學努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後終於發現,家門口的自由和幸福也許更加誘人。
一 體制內的後宮大戲
2023年6月,研究生畢業後,我從澳大利亞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那是一座西部三線城市,沒有連綿的高樓和喧鬧的車流,十分安靜。我就住在城市東部,距離單位只有兩公里,每天用不著起早貪黑,可以睡到自然醒,掐著時間踏進公司大門,坐在辦公室,靜候到下午五點。
八小時之外的時間從來是無人打擾的。我喜歡一個人舒舒服服的窩在沙發,對電視,抓一把零食;有時也會靜下心,捧著一本書;或者到附近的舞蹈教室,跳街舞和爵士。
在許多人眼中,這樣的生活舒適、悠閒。可日子一久,我卻很煩躁。
起初只是因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
公司是國企,屬於人人羨慕的「鐵飯碗」。不過「鐵飯碗」規矩繁多,小到怎樣稱呼對方、怎樣列印文件,大到一份工作由誰來做,全是「智慧」。然而我已經在國外無拘無束慣了,習慣了直來直去的工作方式,來到這裡感覺如同被關進了牢籠。

澳大利亞的公園裡,老人們在下西洋棋
首先要學習的是「正確」稱呼主管。直呼其名,固然不行;但叫人「哥」,叫人「姐」,也不行。公司規定,要稱呼頭銜才行。
可只有領導才有頭銜,這就苦了我這樣的小嘍囉,每天不得不「經理」長,「經理」短,還刻意陪著笑,感覺就像《甄嬛傳》——嬪妃是嬪妃,答應是答應,奴才是奴才,尊卑有序,等級森嚴,時刻提醒自己位於生態鏈最底層。
倘若僅僅如此,倒也算了,偏偏我很快發現,如何幹活,同樣是一門學問。
在單位,除了分內的事情,還時常有許多額外文件要寫。畢竟大領導是甩手掌柜,嘴皮子一動,下面人跑斷腿。只是誰也不樂意跑斷自己的腿,那就需要扯皮。
扯皮是技術活。辦公室里大姐們自有辦法——先緊盯文件,推算著各部門的責任,一發現工作和其他部門有關,立馬推得一乾二淨。
剛入職幾天,我就見到了這個技術。單位派下來一份新聞稿,部門大姐馬上和其他部門的大哥開始「戰鬥」。
大姐的論據是「宣發不歸我們管」,大哥的論據是「內容和你們有關,就該你們跟進」。兩人在辦公室里鏖戰了一個半小時,最後大姐漸漸占據上峰,大獲全勝。
她得意洋洋,翹著嘴角,偷偷朝我比出一個「V」。可我卻覺得荒謬——一篇新聞稿滿打滿算三四百字,用不了三十分鐘就能完成,大家卻寧可花費大量的時間扯皮,真是毫無意義。
這還只是「明槍」,不久後,我又遇到了「暗箭」。
一次主管不在,其他部門領導突然找上門,說時一,這裡有個文件,你學問高,就你來寫吧。來不及等我開口,她便開始上思想課,說「你呀,要注意團結」「年輕人嘛,要有大局觀」。見我仍然不為所動,立馬又說:「你初來乍到,沒有業績。這件事你做好了,大姐一定跟總經理好好誇獎你。」
這份差事最終沒落到我頭上,倒不是我會扯皮,而是主管及時歸來,讓她不得不悻悻而歸。很久後,我才明白,她這是見我初來乍到,拿我當「槍」呢。
如此日復一日,公司里的同事關係就變得十分微妙。這便涉及到了第三門學問,如何跟同事打交道。

進了體制內,連出去玩都不敢大方發朋友圈
公司里任何事情都要審批,而手握審批權限的部門就是「爺」。有次只為了列印一個文件,我來來回回找了四五個部門,整整一天不停解釋,文件才列印成功,可其他什麼也沒做。
我抱怨著工作效率低下,但對桌大姐卻說這就是公司,重要的不是活幹得如何漂亮,而是如何才能不犯錯。她語重心長地告訴我:時一,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的一舉一動,別人全盯著。
秋天時我請了年假去旅遊,臨別時,經理特意叮囑,出去一定要保密,不能發朋友圈。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對著迎面走來的隔壁同事,淡定地撒謊出門見客戶。
話說出口,連自己也驚訝,轉而疑惑:不過是休假而已,為什麼好像在做賊一樣呢?
單位如同一個模具,規矩著我的行為,也規矩著我的想法。不知不覺,我學習了相互扯皮,也學會了面露友好,心懷警惕。可是一想到自己每天將時間全耗費在了這些事情上,心中難免感到沮喪。
我是單位里唯一有海外留學經歷的研究生,環顧四周,許多人學歷不如我,見識不如我,可卻一樣做著相似的工作,拿著一樣相似的3000多工資,彼此沒有任何不同。這樣平庸的感覺讓人很不甘心。
我想起來《圍城》裡的話:外面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想出去。
這座小城,就是我的圍城。
二 都市白領也要搭地鐵去上班
十年前,我在這座圍城裡讀書,從小到大,試卷上成績永遠漂漂亮亮,一直是長輩們眼中「好學生」。那時我想像,未來自己一定是在一線城市,每天出入於高聳的辦公大樓,穿著精緻,過著電視裡的「精英生活」。
我的人生軌跡也的確如此。高考考進了北京的知名院校學金融,畢業前還申請到國外的學校繼續讀研——我們專業出國的不少,父母也希望我像其他人那樣長長見識。
因為疫情,出國定在了畢業後第二年。空閒的一年時間也沒荒廢,我先去北京,後去上海,在券商里實習。
券商里的日夜容不得喘息。每天花費一個小時擠地鐵上下班,每一個人都像條曬乾的鹹魚掛在橫杆上,一路掛到了國貿和徐家匯,然後一涌而出,鑽進了一個又一個布滿玻璃幕牆的高大辦公大樓。
辦公區是一個又一個格子間,像蜂巢,塞滿了衣著考究的男女,互相不是聊著投資回報,就是爭論著財務報表上的天文數字,每一個人語速飛快,時不時就飈出幾句英文。
我每天埋頭電腦前,忙起來連口水都顧不上喝,直到肩膀酸痛,才發現已經臨近下班。不過下班也時常無法閒著,晚上十點多的線上會議,在這行里再正常不過。
幻滅的感覺開始浮現出來了,我漸漸發現原來所謂的「金融精英」也就那麼回事,尤其是底層員工。有人沉默寡言,日日加班,眼圈黑得像熊貓,看上去隨時準備暈倒;也有人聯繫客戶時才展露笑容,一掛電話,就皺起眉,不時傳來輕嘆。
見多了,我也明白了,「精英」鳳毛麟角,大部分人與流水線工人沒什麼兩樣,每天不情不願,只為工資,只是生計。

在上海實習時,一眼望不到頂的大樓
可無論如何,他們還有工資,我忙個不停,卻一分收入沒有,還要每個月花三千塊來租房,花三千塊吃飯和坐地鐵。而和我一樣,為了刷履歷的免費實習生有幾十個,彼此之間,只能自嘲為「小黑工」。
自嘲之餘,大家依然一如既往地「黑」著,因為金融行業就這樣,高高在上的人談著上億的大買賣,對最底層的人卻一毛不拔。
這樣幹了一年,我終於登上了飛往澳大利亞的航班。那時我覺得等到學成歸來,自己也會找一家券商,像大多人那樣,日子沒滋沒味。只是沒想到,國外的日子,完全不同。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見不到多少人,只有無邊無際的森林。有人將這裡的生活戲稱為出家,遠離紅塵,六根清淨。
本地人全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樣。無論男女,喜歡穿著寬鬆短褲,套著衛衣,在草地上踢足球或玩飛盤,全然不顧太陽熾烈。而像我這樣精心打扮,時刻保持優雅形象的中國女孩子們反而成了異類。
對於未來的規劃,他們同樣讓人錯愕。第一個學期我住在校內,一個白人女孩興沖沖地告訴我,自己曾經休學一年,到非洲做教育志願者,晚上住在營地,有時一開窗就能見到野生動物。後來她還感染了瘧疾,幾乎死掉。
她對此充滿自豪,可我卻目瞪口呆,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這一年,對於未來能有什麼幫助嗎?
可之後我發現,這樣的事情在國外不是例外。有人商科讀得好好的,突然轉去學文學,就算註定了賺不到錢也無所謂;也有人書讀到一半,決定休學一年跑到國外,在酒吧唱歌打工,只為了體驗不同的文化。
這麼一比較,我那所謂的GAP只是體驗了一年金融「小黑工」的生活,真是蒼白又無聊。
三 何必去外地遭罪呢
在國外的第二個學期,我搬離了宿舍,一邊讀書,一邊到奶茶店打工。
留學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一個學期學費十萬,每個月房租四五千,還要吃飯,生活費一個月要一萬多人民幣。就算父母不說什麼,我還是難為情,感覺應該自力更生。
打工不算累,每個禮拜只需去三四次,在櫃檯後,一站五六個小時。每小時21澳元,是澳大利亞的最低時薪,折合下來差不多一百塊人民幣。用來生活當然不夠,但可以自己支付房租。
老闆是個很隨和的中國人,彼此直呼其名,說話、做事也不用繞彎子,而且準時下班。有一次見我到時間沒走,他甚至責備我:「時一,你不趕緊回家,還留在這裡加什麼班啊?」
有時他也會聊自己。他說自己之前在這裡讀機械,讀完了,卻發現自己才不想做個無聊的工程師,更願意做個自在的小老闆,收入雖然馬馬虎虎,可想去哪就去哪。他時常給我看旅行照片,講他在海上逗海豚,還有在林地露營遇到了狐狸。
我說:「你有勇氣放棄做一個工程師,也真是厲害。」
他卻不以為然,「活著不就是為了快樂嗎?」
也就在那段時間,我決定獨自搭乘飛機,飛去珀斯看海。站在金燦燦的沙灘上,與世界各國的陌生人一起聽著海浪聲,聊起彼此的故事,放肆大笑,像一群鳥,自由自在,無所顧忌。

一個人飛了趟珀斯,那個很出名的海上小火車
就這樣來到了第二年,最後一個學期臨近,畢業在即,大家紛紛開始忙著出路。有人準備一畢業就去大都市碰運氣;也有人計劃一邊打工,一邊等待機會。
可我的決定是離開。
小城固然安逸,但異鄉也實在寂寞。我想念家鄉的食物,也想念父母。雖然友情能夠緩解思鄉之痛,可畢業越來越近,大家見面也越來越少,大多數時間只能獨自出門,獨自歸家。
路上陪伴自己的只有野生動物,野兔最多,偶爾也會碰到袋鼠,它們並不怕人。有一次,一隻袋鼠就站在了幾十米外,靜靜地轉過頭,盯了我十幾秒,才自覺無趣,一蹦一蹦,遠遠離開。
想到繼續留在澳大利亞,這樣的情形日日都要發生,我可不願接受。
於是最後一個學期我只選了幾門網課,在家裡兩個多月,邊應付著功課,邊給國內的網際網路和金融企業投簡歷。北京和上海的面試通知紛沓而至,生活瞬間也變得十分緊湊——白天讀書,晚上找工作,幾乎日日忙到後半夜。
可一個朋友的話卻讓我猶豫了。他在網際網路公司里做營運,雖然收入不錯,可是每天要忙到晚上十點,幾乎除了睡覺,就只剩下了工作。
忽然間,我想起了實習時的忙碌,也想起了留學時自由自在的時光,還有奶茶店老闆的話:「活著不是為了快樂嗎?」

回澳洲完成最後一學期學業,透過窗外往外看有時候有種壓抑和想家
我發現自己內心充滿了矛盾:想要在國內生活,可是又怕在大城市裡的辛勞。直到一個晚上,情緒忽然徹底崩潰,面對著怎麼也準備不完的資料,莫名想哭。
母親安慰說,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了,乾脆就留在身邊吧,何必非要到外地去遭罪呢?
我點了點頭,就在第二天,放棄了辛苦得來的面試機會。幾個月後,一拿到畢業證,從國外徑直回到了這裡,進入這間兩公里外的公司。
四 體面的人生太虛偽了
進了老家的國企後,許多長輩把我當做了榜樣,勸說著遠在他鄉的孩子回到身邊。他們說,你看時一,去了那麼遠的地方留學,現在不也回來了,你為什麼不能回來呢?
聽著這樣的話,我只能苦笑,心中五味雜陳。
的確,小城的緩慢節奏是十分養人的,可在內心深處,看著如今三千塊的收入,還不如當年在奶茶店裡打零工,十分彆扭。我很怕外人會產生一個念頭:你讀了那麼多書,最後不也只能做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嗎?
為了彌補收入上的不甘,也為了向自己證明自己,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頂著名校頭銜,每天下班後,對著初中生解釋一元二次方程以及如何製造氧化鈣。一天三個小時,每個月賺上三千塊,加上工資一個月收入六七千,在小城裡還算不錯。
可環顧四周,高中同學們全飄向了地圖上的大城市,做網際網路、做金融。只有我,學校比別人好,學歷比別人高,為了少受生活的苦成了唯一的「逆行者」。
一想到自己曾去過那麼遠的遠方,卻要困頓在辦公室,整日忙著扯皮和混日子,還是不免覺得荒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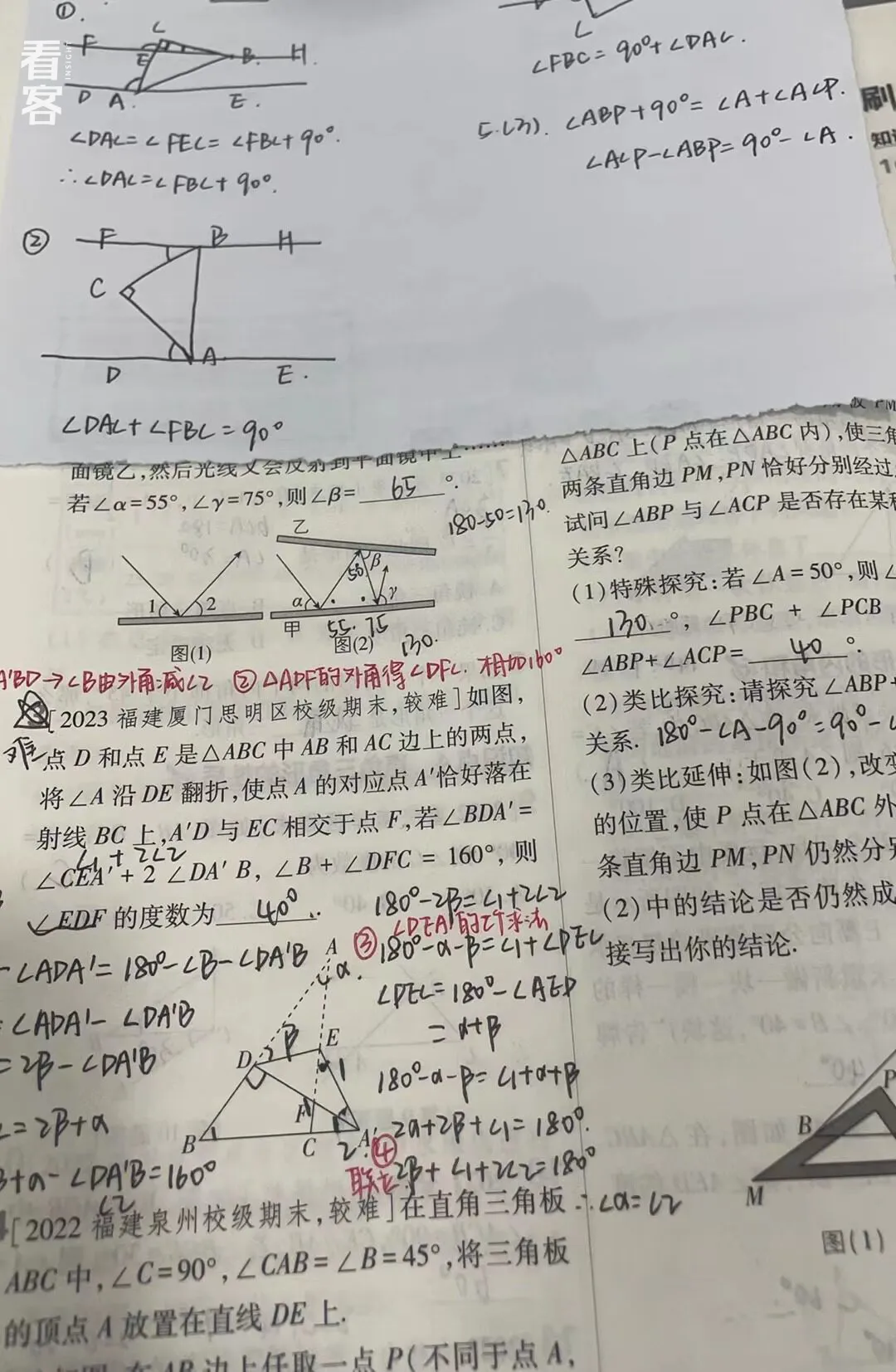
給自己找了一份家教兼職,不再為工資的事情內耗了
迷茫的感覺無處發泄,那就只能和遠方的好友互相傾訴。
那個姑娘是大學同學,在券商里摸爬滾打了許多年。她說自己很忙,經常要通宵達旦地計算著盈虧,還要每天要穿著纖細的高跟鞋和高腰裙,行走在高樓林立的徐家匯,鞋跟和地面一碰,敲出清脆而急促的節奏。
「這不是你以前想像中的樣子嘛?」我問她。
「年少無知。」她很快回答,嘆了口氣,繼續說:「年薪大幾十萬,看起來很多,可上海這地方,吃飯很貴,房租也貴得離譜,還不得不購置名牌衣服和首飾。我不喜歡這些,但沒辦法啊,必須要裝點門面。到了年底一盤算,以為自己賺了很多錢,結果帳戶上只多出了十萬塊。」
「十萬塊也不少了。」
「以後要買房的。上海房價多貴你也知道。攢上十幾年,最後才夠首付,就為了能貸款,繼續還債。還著還著,二十年就過去了。奮鬥了半天,只是為了讓自己債台高築。這就是一線城市。你說諷刺不諷刺?」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她,她忽然顧自笑了:「時一,其實我好羨慕你現在的狀態。真的,至少你的每一天,只屬於自己。」
一席話不光沒有解決困惑,反而讓人更加迷茫了。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話:北上廣裝不下肉身,三四線裝不下靈魂。那,我的靈魂是什麼?
直到有一天,在城中心的咖啡店,一個朋友興高采烈地給我展示了她的事業:畫表情包。她說她再也受不了單調重複的打工生活,有一天突然醒悟,「老娘不做了」,辭了職。從此用不著再看老闆的臉色,只要一台電腦,和一個畫板,自己也能過得很好。
我很羨慕她,一瞬間,也想到了自己。從小到大,我的人生按部就班,好好讀書,考一個好大學,然後去國外留學,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能夠看上去「體面」。但到了國外,我才發現世界那麼大,人生多種多樣,「體面」與「我是誰」並不是等價關係。
從那天起,我想明白了許多。我做了一個表格,列舉出了種種沒有做,又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1,學滑板;
2,考CPA;
3,學日語;
4,開一個補課中心,教更多小孩子;
5,去流浪,每個城市住上三四個月;
6,繼續留學,去看一看更多的人,更多的景;
……
當然,很多事情還很遙遠,需要慢慢積攢。不過前三項,倒是隨時可以發生。

利用周末和下班後的時間,時一學會了摩托車和滑板
從此每個周末,在附近的公園裡,都會出現一個27歲的姑娘。她滿頭汗水,在陽光下踩著滑板,動作跌跌撞撞,笨拙又緩慢。周圍飄來的譏笑目光她不在乎,摔得是否漂亮優雅她也不在乎,只專心致志地享受著風吹過發梢的感覺。
也許「體面」永遠也不會發生,但至少,我終於明白了「我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