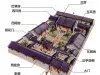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招數以百萬計的古代藝術品,其中陶瓷製品算是大宗,絕大部分是官窯瓷器,也有一部分明清兩代的地方窯品種。故宮深藏紫砂四百餘件
明代末期以來,宜興的紫砂陶器不僅受到文人墨客、官僚富紳的喜愛,而且開始受到宮廷的重視,最早進入宮廷的是以歐窯為代表的宜均,稍後康熙朝的紫砂器皿被選作畫琺瑯所使用的坯胎進入宮中;雍正朝精選各類名品進貢宮廷;干隆朝則將當時風靡社會的宜興制壺名家請進宮中造辦處,專門為皇家制壺,同時宮廷也開始分期分批地向宜興訂購紫砂,與景德鎮官窯瓷器相同,由皇家出具圖樣,統一樣式,統一規格,此種情形自干隆以後,時斷時續,一直到宣統元年清末大臣端方定製的一批刻有「宣統元年(1909年)」款識的砂壺為止,其間經歷了近三百年的漫長歲月。
目前存有1949年以前的舊藏品及解放後至八 ○年代以前新收器皿共計四百餘件,雖說數量不是很多,但品類相當齊全,有各式茶具、餐具、文房用具、清供雅玩等,另有成套的祭器、魚缸花盆、動物雕塑、仿生果品等。僅以數量最大宗的砂壺為例,就有圓壺、扁圓壺、掇球壺、瓜棱壺、包袱壺、龍鳳壺、提梁壺、包漆壺、僧帽壺、樹癭壺、六方壺、扁方壺、方鬥壺、覆鬥壺、筒式壺、菊瓣壺、蓮瓣壺、蟠螭壺、虎柄壺、延年壺、百果壺、竹節壺、梅花壺、硯滴壺、溫酒壺等。文房用品有描金堆粉山水人物大筆筒、山形筆架、桃式水盂、螭龍硯滴、圓筆洗、圍棋罐、臂擱等。陳設用品有獸耳銜環方瓶、出戟尊、仿古銅花觚、松竹梅花插、葫蘆形壁瓶、花鳥壁瓶、四系詩句大背壺、鳧形瓶、回紋鼎爐、天雞尊、鴛鴦式蓋盒、海棠式花口瓶、七言詩句對聯掛件等。還有一批宮中日常使用的花盆、魚缸等也獨具特色。有干隆琺瑯藍料彩大花盆,各式大小不等的圓花盆、方花盆、橢圓花盆、腰圓水仙盆、三折斜方花盆、六角形堆粉繪花花盆、八角式花盆、海棠式花盆。入貢宮廷的紫砂御用器
藏品中絕大部分是清代製品,極少數是明末製品,還有一部分民國初年的製品,最多見的是茶壺和茶葉罐,其次是陳設及文房用品,盤、碗、實用器具數量較少。帶有宮廷特色的官制紫砂款識一般鈐刻在器物的底部,與同時期的景德鎮官窯製品風格相一致,款識的布局、筆道完全相同,有「康熙御製」、「干隆御製」、「大清干隆年制」、「嘉慶年制」、「嘉慶四年澹然齋」、「道光行有恆堂」、「咸豐行有恆堂」、「宣統元年」等數種。名家款識的有時大彬、項聖思、惠孟臣、陳鳴遠、陳覲候、陳殷堂、陳聖恩、楊彭年、陳曼生、邵友蘭、邵玉堂、邵任遠、王南林、楊夢臣、朱石梅、黃玉麟、華鳳翔,以及季聖明、鄒東帆、楊季初、劉醒民、王竹坪、葛明祥等,還有東溪、少林、冰心道人、石庵、適園主人、仲侯、祖德、友義、海村、松鶴軒、?齋、匋齋、敬業自造、寶華庵、裴石民等。
帶有官窯年號款識的紫砂器應是當時宜興地方官入貢宮廷的御用器,有的是宮廷出樣傳旨讓宜興定燒的,有的是進呈素坯在造辦處二次加工處理的,工序包括:包漆皮、燒器座、加繪金彩、堆粉等。這批進貢宮廷的東西,從坯泥的精煉程度、制器的工藝手段、裝飾的題材內容來看,都顯示出一種超塵脫俗的皇家氣派,其真實可信的程度是不容置疑的。另外還有一部分精緻優良的茗壺,從裡到外光素無紋,質地、工藝都堪稱一流,並沒有任何款識和標記,此類製品技藝超群,也應歸併於宮廷用具的範疇。
我們發現藏品中凡帶有名人款的製品絕大部分為1949年以後新收,目前我們尚不能肯定這些是名家的真品,只能參照目前國際國內已發表的紫砂專著,對同類製品的風格逐一加以分析研究,作出客觀的介紹和分析。1982年秋,已故的宜興紫砂大師顧景舟先生曾來我院觀摩了一部分宮內收藏古代宜興製品,並給予極高的評價,肯定一部分名家製品的真實性,認為故宮博物院藏品獨具宮廷特色,極有研究價值。紫砂壺類別應含宮廷壺
不久前,紫砂陶學界有一些學者提出一個新穎的觀點,即把紫砂茗壺的等級類別進行了初步的劃分和歸屬。第一類──具有傳統的文人審美風格,講究內在的文化底蘊,提倡素麵素心,清雅宜人,或在壺體上鐫刻題銘,切壺、切茶、切景、詩、書、畫融於一壺,充滿了濃郁的書卷氣,稱為「文人壺」。第二類──具有熱烈鮮艷、明麗繁縟的裝飾效果,常用紅、黃、藍、綠、黑等彩漆或泥料繪製山水人物、草木蟲魚,或者鑲金包銀做為輔助裝飾,充滿自然民俗的市民生活氣息,稱為「市民壺」或者「民間壺」。第三類──將砂壺進行拋光處理,鑲以金口、金流、金柄,有時也用銅錫類金屬,風格脫離中國文化傳統,迎合西亞及歐洲人的審美情趣,帶有明顯的異邦風貌,稱為「外銷壺」。壺是如此,其它器具亦然。我們很贊成這種按等級類別的歸納法,但仍不很全面,建議再補充進精工細作、典雅優美的宮廷壺這一類,因為庫藏品中有許多表現當時最高工藝成就的紫砂器,不惜工本,蓋世超群,是道道地地的御用紫砂器。此類製品除了帶有濃厚的書卷氣以外,還有富貴華美的皇家氣派,社會上不流通、不得見,其製作水準與官窯一樣代表了當時紫砂製作的最高成就,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然而,進呈宮廷或宮廷向宜興定燒的紫砂製品由於受到最高統治階層審美意趣的局限性,不能充分發揮藝術匠師和設計文人的創造才華,很大程度的禁錮了他們的藝術想像力,而使製品過於拘謹、規範,出現了程序化的格局。但就砂質的精煉和工藝手法以及技巧裝飾上看,都較之其它之類的製品更勝一籌,絕非一般「文人壺」、「民間壺」所能比擬的。由於此類製品外界流散較少,因此對於宮廷茗壺及同類紫砂器的深入研究,應當是當今紫砂研究領域的新課題。宮廷紫砂器的款識
那麼,宜興紫砂器是何時進入宮廷的呢?根據現有的藏品分析,最早的舊藏品是明代萬曆前後帶釉的宜興紫砂即所謂的「宜均」,也有做為雕漆內胎收進的,有一件內胎紫砂外雕漆的方壺,壺底漆皮內有「時大彬」三字刻款,隱現其中,據漆器專家分析,從漆質、做工看應屬晚明製品無疑。另有幾件無款的砂壺砂質及工藝手法較清前期製品簡練而粗放,加工不細的質地和不考究的工藝手法非常接近南京吳經墓出土的茗壺,但由於舊藏年代久遠,已無法考察出確切的入藏時間,因此,在此只能略作一點推測。現存藏品中明代的很少,可以確認的是一些晚明的宜均,清代製品中清初康熙、雍正的也不多,干隆時製品不少,嘉道以後至晚清最多,民國也有一些,基本上能夠反映出清初至民國初年紫砂器的製作水準。事實上,無論是宮廷出樣到宜興定燒,還是由地方官員呈進,做為地方窯之一的宜興窯都會選擇當時最好的匠師,用當地最好的砂泥製作出最精良的優秀品種。這些當時被選中進京的紫砂器均不能銘刻上匠師的姓名,要麼按照官窯的格式銘刻帝王朝代款,要麼不書款,這一點也是宮廷壺與文人壺的最大區分之一,一般來說,流傳於社會的高品味、高檔次的茗壺,大多有名家題款,這樣可以「壺以字貴,字隨壺傳」,而宮廷用器的特殊性使藏品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形:在清初的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中,康熙、干隆有年號款,款識大小、布局格式與同期官窯瓷器相同,雍正朝未見官窯款識,干隆以後的其它各朝代也不多。也許有人會問:清代正值紫砂業的繁榮時期,名家高手輩出,宮廷是使用第一流的紫砂器,怎麼會多數沒有名家款識呢?
這是因為,首先,清代宜興窯畢竟是一個獨具地方特色的民間窯場,其社會地位還不如產量巨豐、朝廷重視、吃皇糧的景德鎮官窯。其次,當時社會上手工業匠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得到士大夫階層青睞的名家高手,也只能局限於文人的圈子內,社會地位仍然被限定在封建等級之中。再者,在官僚文人合作的製品中署款,近似一種廣告宣傳,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時,也宣傳了文人墨客的風流儒雅,而當初由宜興地方進貢給皇室的紫砂器是朝廷的御用品,與其它品類的御用工藝品一樣,是不能留有個人痕跡的,只能遵旨書寫帝王年號款,或者不書款,一切根據具體需要而定,書寫銘刻帝王年號款的先決條件是在朝廷有旨的情形下,奉旨書寫的,隨便書寫也是不成的,所以當時社會上再有名氣的匠人也不敢擅自在自己的製品上署名,將自己凌駕於地方官吏之上,在最高統治者面前留姓揚名的。和景德鎮的官窯瓷器不同,干隆以前的許多宮廷御用紫砂是沒有款識的,不能單純以有無款識而論其價值。有一部分舊藏品中的無款器,藏品的砂質及製作的精美程度與當時的大家陳鳴遠、項聖思、惠孟臣、楊友蘭、楊彭年等名家制器相比毫無遜色,或者更勝一籌。制砂藝匠們在給宮廷的制器中傾盡了全部的心血,生怕有絲毫的閃失,小心而謹慎、一絲不茍,把畢生的心力和智能傾注於小小的茗壺中,而製作者真實姓名由於封建等級制度的束縛而被深深的埋入歷史的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