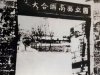沈從文與張兆和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人,著名作家。1918年從家鄉小學畢業後,隨當地土著部隊流徙於湘、川、黔邊境與沅水流域,曾正式參軍。1922年獨自來到北京,踏上文學創作之路,寫出了大量有著濃郁湘西氣息、極富個性魅力的感人作品,1927年起先後登上上海中國公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的講壇。1949年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出土文物、工藝美術及物質文化史等。著有《邊城》、《長河》、《湘西》、《湘行散記》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其中以中篇小說《邊城》享譽世界。
一
1948年11月7日,戰雲低垂,在北大校園內,沈從文和朱光潛等一些教授、學生、助教有過一次文學座談會,師生暢所欲言,平等地探討「今日文學的方向」。沈從文在發言中反覆以紅綠燈為喻談論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他提出「文學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點批評、修正的權利呢?」[1]
這大概是他1949年以前最後一次參加文學活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此時上距他踏上文學之路已有二十幾個年頭(他發表傳世名作《邊城》也足有十四年),下距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慶和解放軍完成對北平的包圍只剩下了40天。如果說,那一刻他尚未想到自己的文學生涯即將走到盡頭,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就會意識到了。12月1日,北平的戰事已進入最後階段,國民黨的失敗已無可挽回。沈從文寫信給季陸:
「大局玄黃未定,惟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近中年,觀念凝固,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加之誤解重重,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擱筆。」[2]
12月20日,他在給另一朋友炳堃的信中說:
「時代突變,人民均在風雨中失自主性,社會全部及個人理想,似乎均得在變動下重新安排。過程中恐不免有廣大犧牲,四十歲以上中年知識分子,於這個過程中或更易毀去。這是必然的。」[3]
在他寫信前的五天,北大校長胡適已南飛,北平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位於中老胡同的沈家一度也曾說客盈門,變得熱鬧起來。一方面北大校方送來了直飛台灣的飛機票,一方面北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樂黛雲及左翼進步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則先後登門,「希望他不要去台灣,留下來迎接解放,為新時代的文化教育事業出力。」[4]沈從文此時「竟只想回到家鄉去隱居,或到廈大或嶺南大學去。對於革命,除感到一種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無所知。」[5]最後,他選擇了留下。以後談到這一選擇時,他說更多的是為了家人。他沒有料到的自己將要面對的竟是這樣一幅圖畫:
左翼學生在北大校園裡貼出了全文抄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其中將沈從文定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教學樓上掛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等大幅標語。他的長子、當時只有14歲的沈龍朱半個多世紀後仍清楚地記得:「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兒,在北京四中念書,放了學就去父親教書的北大看熱鬧,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親是粉紅色的,粉紅色我覺得還可以。回到家就跟父親說。我們覺得無所謂的事,對父親的刺激卻很大。」(夏榆《100歲的沈從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
後來沈從文在給親戚的一封信中坦言:「用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國民黨混過,只因習慣為自由處理文字,兩年來態度上不積極,作成一些錯誤,不知不覺便被人推於一個困難環境中,『為國民黨利用『的阱坑邊緣。如真的和現實政治相混,那就早飛到台灣廣州去了,那會擱到這個孤點上受罪?」[6]
1948年3月,大陸戰場上勝負將分,躊躇滿志、在香港等待勝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懷著一個勝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態,在《大眾文藝叢刊》發表了一錘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動文藝》,以紅黃藍白黑的顏色對一批著名作家進行定性,指出「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沒有不臣服在他大旗下的沈從文被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是「藍色」作家,蕭乾是「黑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7]
(同一輯還有邵荃麟《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前者指出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的沈從文等作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閒文藝」,在思想鬥爭中屬於「要無情地加以打擊和揭露的」對象。後者則對沈從文紀念熊希齡的《熊公館》一文作了上綱上線的批判,指責他「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是「典型的地主階級文藝」,是「清客文丐的傳統」。[8])
沈從文的連襟、語言學家周有光92歲時回憶說:
「解放前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沈從文自己講,郭沫若對他很不好。」[9]
就郭沫若的文章而言,未必沒有「揣摩上面的意圖」成分,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還來自自負全能天才的郭沫若對沈從文的隱恨。早在1930年,年輕的沈從文就公開發表《論郭沫若》一文,對這位比他年長10歲的成名人物作了無所顧忌的評價,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麼東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適合於檄文、宣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10]1931年,他發表《論中國創作小說》,在論及郭沫若和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時,沈從文說:「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面是無多大成就的。」「但創作小說,三人中卻為最壞的一個。」「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11]
這樣直截了當的批評擱在郭沫若身上,他又如何能忘得了?1949年4月5日,楊剛到醫院看望沈從文,帶來了最新的《人民日報》《進步日報》,第二天,他在病床上寫下一篇很長的日記,他感嘆:「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12]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將登上文藝界權力頂峰的郭沫若。
此外,沈從文對政治的疏離、乃至「反對作家從政」正好與郭沫若對政治的熱衷形成鮮明的反差,也註定了他們的道不同不相為謀。
沈從文一生都游離於現實政治之外,對任何組織都保持著戒心。他從不諱言自己過去「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他從未加入國民黨或三青團,雖然他對加入了國民黨的同事朱光潛、楊振聲、周炳琳等「在一處並不覺得難受」。大約1945年,聞一多、吳晗邀請他加入民盟,他沒有答應。抗戰後回到北平,徐盈介紹他編《現代文藝》月刊,「老擔心和政治有關聯,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幹了。」[13]1948年,蕭乾邀他參與「第三條道路」的《新路》,他也拒絕了(不過他「認為對國內和平會有好作用」)。
二十多年間,他始終堅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始終不加入什麼「反動」或「進步」的文學集團,既不參加「左聯」(「左聯」成立,好友胡也頻曾邀他加入),也不是梁實秋的同道,不是文學研究會、甚至不是「新月社」的成員。他只是堅定地「爭取寫作自由」。
這位從小就當兵的作家壓根不相信戰爭能解決問題,反對任何戰爭、暴力,但他從來沒想過去台灣,或流亡異國。他的生命和他絕世的文字一樣只能屬於中國。對國民黨,他向來沒有好感。在西南聯大,「因在課室中批評到重慶,稿件受審查,有四個集子不許印行,《長河》被扣」。[14]當有傳言他所尊敬的胡適即將到南京政府任職,他也寫信表示憂慮。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最好保持不黨不偏之身,在政治之外努力,連民盟這些第三方面政治組織,他也是持有戒心的,他在西南聯大時還寫過《我們要個第四黨》的文章,結果被國民黨禁止發表,並且被昆明出的《掃蕩報》大罵了一陣。「文革」期間他在檢查中批評自己:「西安延安不分。對國民黨固然不抱什麼希望,對人民解放戰爭,也同樣抱著懷疑悲觀心情。對偉大領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15]
像他這樣的人,當天下定於一之時,他被獲勝一方拋棄乃是必然的。何況還有一朝得了勢、便把令來行的郭沫若在。
二
1949年終於不可抗拒地來了,沈從文幾乎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變得特別敏感。1月2月,他在《綠魘》文末題了一句話:「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6]18日,他在徐志摩、陸小曼真跡手書的《愛眉小札》上充滿感慨地寫下:
「孤城中清理舊稿,忽得此書。約計時日,死者已成塵成土十八年。歷史正在用火與血重寫,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17]
此時處於沙灘、紅樓的北大尚在風雨飄搖之中,而西郊的水木清華已是另一個新天地。梁思成、金岳霖等在清華任教的朋友都很惦念他,請他到清華住幾天,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氣」。1月28日(即舊曆年除夕),沈從文去清華的當天,張兆和寫信勸慰他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婦談話,多同從誡姐弟玩,學一學徐志摩永遠不老的青春氣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寫,信也是少寫為是。」[18]大約29日左右,沈從文覆信表示:「我用什麼來感謝你?我很累,實在想休息了,只是為了你,在掙紮下去。我能掙扎到多久,自己也難知道!我需要一切從新學習,可等待機會。」[19]
30日,沈從文在張兆和給他的信上寫了很多批語,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情緒:
「我頭腦已完全不用了,有什麼空想。
「關切我好意有什麼用,我使人失望本來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麼地方?尋覓,也無處可以找到。
「我『意志』是什麼?我寫的全是要不得的,這是人家說的。我寫了些什麼我也就不知道。
「給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說的全無人明白。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並不瘋。大家都支吾開去,都怕參預。這算什麼,人總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麼不妥?學哲學的王遜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當了瘋子。我看許多人都在參預謀害,有熱鬧看。
「小媽媽,我有什麼悲觀?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強附和,奴顏苟安,這麼樂觀有什麼用?讓人樂觀去,我也不悲觀。
……我沒有前提,只是希望有個不太難堪的結尾。沒有人肯明白,都支吾開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應當那麼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聞狗吠聲不已。你還叫什麼?吃了我會沉默吧。我無所謂施捨了一身,飼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樣的。社會在發展進步中,一年半載後這些聲音會結束了嗎?」[20]
「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並不瘋」一語道出了那一刻沈從文內心極度的痛苦。
同一天,梁思成、林徽音夫婦給張兆和回信,詳細匯報了沈從文在清華的生活、起居及病況。2月2日,沈從文給張兆和的信中說:
「……『我們要在最困難中去過日子,也不求人幫助。即做點小買賣也無妨。』你說得是,可以活下去,為了你們,我終得掙扎!但是外面風雨必來,我們實無遮蔽。我能掙扎到什麼時候,神經不崩毀,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運掙扎?」[21]
在清華園「老金屋子」里,他寫過一篇《一個人的自白》:「經過了游移、徘徊、極端興奮和過度頹喪,求生的掙扎與自殺的絕望……反覆了三個星期,由沸騰到澄清,我體驗了一個『生命』的真實意義。」[22]他回憶起少年時代的經歷,特別是初到北京時的掙扎,饑寒交迫,求學無門,求生無路,苦悶、彷徨,他忘不了初到北京半年裡所遇到的挫折、屈辱,但他永遠記著唯一一個幫助過他的陌生人,一個每當黃昏串街賣煤油的老頭,曾借給他兩百銅子,使他度過了一個年關,他把這份善良好意放大了,「這就是《邊城》的老祖父,我讓他為人服務渡了五十年的船。」「渡船」是個象徵,他本人就是這樣的「渡船」,他感慨——「凡曾經用我的同情和友誼作渡船,把寫作生活和思想發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學生都萬萬不會想到,這隻忘我和無私的抽象渡船,原是從一種如何『現實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現實,聽狹隘的自私和報復心生長,二十三年後北方文運的發展和培育,會成什麼樣子?不易想像。」[23]
清華七日,溫暖的友情表面上似乎緩解了沈從文的緊張情緒,林徽音有點太樂觀了,她不知道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並不能真正解決在他腦子中的過慮與陰影。他本人在1956年寫的《沈從文自傳》裡講到:
「平津炮聲一響,神經在矛盾中日益混亂。只想到胡風代表左翼,郭沫若說我是黃色作家……這些人一上台,我工作已毫無意義。情緒一凝固,任何人來都認為是偵探。
解放一來,我發現我搞的全錯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潰了。」[24]
相隔近兩年後,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的檢討中說:「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了。」[25]
四十多年後,張兆和依稀記得:
「1949年2月、3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26]
三
3月2日,在校改完《阿麗絲中國遊記》後(準備交給開明書店),沈從文在存底本上留下了這樣的題識:
「越看越難受,這有些什麼用?
一面是千萬人在為爭取一點原則而死亡,一面是萬萬人為這個變而彷徨憂懼,這些文章存在有什麼意義?
一切得重新學習,慢慢才會進步,這是我另外一種學習的起始。」[27]
大約也是在3月,他在1931年新月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沈從文子集》中寫了多則題識:
「幻念結集,即成這種體制,能善用當然可結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個真正悲劇結束,混亂而失章次,如一虹橋被新的陣雨擊毀,只留下幻光反映於荷珠間。雨後到處有蛙聲可聞。杜鵑正為翠翠而悲。」
「燈息了,罡風吹著,出自本身內部的旋風也吹著,於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當時最熟習的本是這些事,一入學校,即失方向,從另一方式發展,越走越離本,終於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見彼岸遙遙燈火,船已慢慢沉了,無可停頓,在行進中逐漸下沉。」[28]
杜鵑不是為翠翠而悲,實際上是為他而悲,虹橋被毀,燈已熄,船慢慢下沉,沈從文的世界塌陷了。3月6日,他在家中繼續寫帶有自述性質的《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這是他選擇「解放」(自殺)前的最後一篇文稿。他回憶起了一生許多不幸和幸的往事,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他一再想起美麗淳樸湘西,想起他心愛的《邊城》,他的妻子(寫《邊城》時的「新婦」):
「那裡的翠翠,秉性善良處,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當時的新婦實在相差不多。但誰也不會料到這個也就要成為預言。一切發展全如預言,在十五年後將用事實證明。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於一夜雷雨中死了,剩餘一個黑臉長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邊聽杜鵑啼喚。一個悲劇的鏡頭如此明白具體。」[29]
由「思」出發止於「知」,由「信」出發歸於「盲從」的思路註定了要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早在1949年元旦前夕,他就預見到了自己二三十年來的用筆方式「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他與家人的矛盾也來自時代轉換之際「思」與「信」的矛盾。一切都不可避免,仿佛是宿命。用他自己的話說:「外有窘迫,內多矛盾,神經在過分疲乏中,終於逐漸失去常度。」[30]
3月13日,沈從文寫信給張兆和的堂兄、烈士張璋之女張以瑛(當時是共產黨的幹部)坦呈了自己的靈魂:「我因過去生命限制,小時候生活受挫折過多過久,心受傷損。從『個人掙扎』方式中戰勝困難,支持下來,因之性情內向,難於與社會適應。而個人獨自為戰精神加強,長處與弱點即在一處。如工作恰巧和時代需要相配合,當然還可為國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縱不能用筆寫文章,即作美術史小說史研究,也必然還有些新的發現,條理出一個新路,足為後來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時代游離,並且於文字間還多牴牾,我這種『工作至死不殆』強執處,自然即容易成為『頑固』,為作繭自縛困難。即有些些長處,也不免游離於人群的進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涼。這長處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緒糾纏,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時這孤立,神經支持下去已極勉強,時代一變,必然完全摧毀。這也就是目下情形。」本來在這後面還有一句話,他寫好後又用筆劃掉了:「我的存在即近於完全孤立。」[31]
他在這封信里說到張兆和想找工作,去找錢俊瑞(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員會領導人之一),找不著。他說自己也不想在北大教書下去了,想另找一個工作,哪怕隨軍都可以。「我從否定了我自己用筆工作後[被劃了],只要有機會,不問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難去做,以為多少總可以把剩餘生命為人民做點事。但目前在這裡,除神經崩毀發瘋,什麼都隔著。共產黨如要的只是一個人由瘋到死亡,當然容易作到。如還以為我尚可爭取改造,應當讓我見一見丁玲,……如一定要照一個普通職員方式,思想弄通才許動,或只記住我過去一些文章有觸犯處,以使我神經崩毀為得,那就照你說的看醫生,也毫無用處。我在另外一種攻勢中,疲倦得已到一個程度,不是為三姑,不是還希望有機會為人民作一點補過工作,我早已長休息了。」[32]
一個「桃紅色」作家一點卑微的願望,在歡天喜地的時代大轉折中,又有誰會去理會,一種被拋棄、被隔離的無邊的孤立感使沈從文的精神危機終於在以激烈的方式爆發了,那是3月28日,幸虧在他家做客的張中和(張兆和堂弟)發現及時。張兆和4月2日寫給沈從文大姐、大姐夫等的信中說得很詳細: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這幾個月來精神不安的現象,但是這種不安寧,並不是連續的,有時候忽然心地開朗,下決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興;但更多的時候是憂鬱,悲觀,失望,懷疑,感到人家對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說,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為說的太多,我反倒不以為意。他那種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單是我,連所有的朋友都覺得他失之常態,不可救藥。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3月28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傷勢也不太嚴重,即刻送到醫院急救,現在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
他一切都很正常,腦子也清楚,只要不談到他自己;一談到自己的問題便執著某一點,一定說人家有計劃的要打擊他謀害他。他平常喜讀《變態心理學》,寫文章聯想又太豐富,前兩年寫東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誤解,心裡不痛快。社會一變動,雖然外面的壓力並不如想像的大(其實並沒有壓力),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當然,一個人從小自己奮鬥出來,寫下一堆書,忽然社會變了,一切都得重新估價,他對自己的成績是珍視的,想像自己作品在重新估價中將會完全被否定,這也是他致命的打擊。總而言之,一句話,想不開,鬧成現在這樣局面,否則好好上課,慢慢來修正自己,適應新環境,不至到這個地步的。眼前書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後必須易地療養,一定要把他觀念上的錯誤糾正過來才能保全全。」[33]
幾十年後張兆和都忘不了「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沈從文的脖子上從此留下了「刀割的痕跡」。此前也是3月的一天,他14歲的長子沈龍朱看見他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沈龍朱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
四
5月30日下午,沈從文在日記中提起了丁玲、凌叔華、《邊城》中的翠翠以及張兆和(三三)——
「很靜。不過十點鐘。忽然一切都靜下來了,十分奇怪。第一回聞窗下灶馬振翅聲。試從聽覺搜尋遠處,北平似乎全靜下來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時相近。遠處似聞有鼓聲連續。我難道又起始瘋狂?
兩邊房中孩子鼾聲清清楚楚。有種空洞游離感起於心中深處,我似乎完全孤立於人間,我似乎和群的哀樂全隔絕了。綠色的燈光如舊,桌上稿件零亂如舊,靠身的寫字桌已跟隨了我十八年,桌上一個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還像是極熟習,那時是她丈夫死去二月,為送她遺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頭上和[凌]叔華一家人照的。抱在叔華手中的小瑩,這時已入大學,還有那個遺孤韋護,可能已成為一個青年壯士,--我卻被一種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瘋狂,游離於群外,而面對這個相片發呆。
……
我的家表面上還是如過去一樣,完全一樣,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們極知自重自愛,我依然守在書桌邊,可是,世界變了,一切失去了本來意義。我似乎完全回復到了許久遺忘了的過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絕,而又不悉悲哀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對,世界在動,一切在動,我卻靜止而悲憫的望見一切,自己卻無份,凡事無份。我沒有瘋!可是,為什麼家庭還照舊,我卻如此孤立無援無助的存在。為什麼?究竟為什麼?你回答我。
我在毀滅自己。什麼是我?我在何處?我要什麼?我有什麼不愉快?我碰著了什麼事?想不清楚。
……
夜靜得離奇。端午快來了,家鄉中一定是還有龍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間中酣睡,還是在杜鵑聲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後還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難道又瘋狂了?我覺得嚇怕,因為一切十分沉默,這不是平常情形。難道我應當休息了?難道我……
我在搜尋喪失了的我。
……」[34]
他想到了四個不同的女性,丁玲和凌叔華是他的朋友,十九年以後,經歷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一個成了文藝官員、新時代的驕子,一個已去國離鄉。三三是他相濡以沫十幾年的妻子,翠翠是他筆下最可愛、最有生命的人物之一,她們分屬歷史、現實、理想(或夢境),正是這一切構成了他豐富多彩的生命歷程,成全了他輝煌的文學世界。無法守護理想的苦痛,不能被家人理解的苦痛以及連累家人的愧疚感,這一個個結他都無法解開,他的崩潰幾乎是必然的。
在郭沫若定性的陰影下,新政權的誕生帶給沈從文的難以解脫的憂慮和巨大的精神壓力,而張兆和與兩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和當時千千萬萬的人們一樣,對新的歷史劇變充滿了歡欣的期待和樂觀的嚮往。如果說沈從文心理防線的塌陷主要因為大的時代環境變化,自然不會有什麼錯,但家庭的因素、朋友的冷落同樣不可忽略,甚至有可能更為致命。本來他留下就是為了家人,2月2日他在清華寫給信張兆和說:
「小媽媽,你的愛,你的對我一切善意,都無從挽救我不受損害。這是夙命。我終得犧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這裡,本來即是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作犧牲的!應當放棄了對於一隻沉舟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35]
而張兆和那時並不理解他內心的那種痛苦,她在同一天寫給梁思成夫婦的信里說:
「希望他在清華園休息一陣子,果然因身心舒暢,對事事物物有一種新看法,不再苦惱自己,才不辜負賢伉儷和岳公、熙公們的好意。
……解放軍進城後,城內秩序已漸趨安定。大家都好。」[36]
四十多年後張兆和說:「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7]7月間,沈從文自己寫給老友劉子衡的信也說得很明白:
「一個與群游離二十年的人,於這個時代中毀廢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適因種種關係薈萃,迫害感與失敗感,愧與懼,糾紛成一團,思索復思索,便自以為必成一悲劇結論,方合事實,因之胡塗到自毀。
……有工作在手時,猶能用工作穩住自己,一擱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種聯想上,即刻就轉入半痴狀態,對面前種種漠然如不相及,只覺得人生可憫。因為人和人關係如此隔離,竟無可溝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僅將如陌生,甚至於且從疏隔成忌誤,即家中孩子,也對於我如路人,只奇怪又發了瘋。難道我真瘋了?我不能瘋的!可是事實上,我可能已近於半瘋。」[38]
沈從文被停止北大教職、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後,9月8日,丁玲、何其芳看望了他。他隨後提筆給丁玲寫了一封信。雖然他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卻是多年舊交。胡也頻被殺害後,他曾千里送丁玲和她們的遺孤回湖南故鄉,交情至深,丁玲被捕,他曾奔走呼號,在《國聞周報》《獨立評論》公開發表文章抗議。他在信中袒露心跡:
「因為心已碎毀,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來。本出於恐怖迫害,致神經失常,於氣、急、怕中逐漸加深,終於崩潰。到醫院一受『治療』,錯、亂增加,從此一來,神經部分組織,轉入變態,人格分裂,作事時,猶如條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為意。回到住處,家中空空的,處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遠陷入迫害瘋狂回復里,只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正如一瓦罐,自己胡塗一摜,他人捕手過來,更有意用力摜碎,即勉強粘合,從何著手?也可說是一個犧牲於時代中的悲劇標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瘋狂到毀滅。因生命所受挫折,已過擔負,每個人神經張力究竟有個限度,一過限度,必崩毀無疑也。」[39]
由於張兆和到華北大學接受革命教育,住校。兩個孩子讀中學,常常因參加政治集會,很晚才回家,他告訴丁玲,「每次工作後回到住處,看到家中空空的,總不能不想到一些事情,一思索到神經失常全部過程,頭腦即刻混亂成一片,我實在需要得到一點支持,才能夠不再崩毀。如你們覺得我用筆離群,離開社會發展,所致過失,必需接受由瘋狂發展到毀滅為止教訓,我除了放棄一切希望,來沉默接受,似不應再說什麼。如中共事實上還在改造我,教育我,使我明白群的偉大,革命的向前性,以及其他,用意實在否定我不健康觀念和弱點,……我覺得已面臨到一種問題上,即家庭能恢復,頭腦方有希望轉復常態。」[40]
他說:「『向人民投降』,說來也極自然,毫不勉強。」但他再三認為,「目下既然還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幫助我站得住,不至於忽然圮坍的,即工作歸來還能看到三姐。這就臨到一回考驗,在外也在內,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對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說來,我目下還能活下去,從挫折中新生,即因為她和孩子。這個家到不必須受革命拆散時,我要一個家,才可望將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獻給國家,且必然發瘋發狂工作,用作補償過去離群痛苦。我且相信這麼工作,對社會用處,比三姐去到別處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來可見見她,什麼辛苦會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離開,不問是什麼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敗感占了主位,什麼都完了。我盼望你為公為私提一提這一點。」[41]「我明白我自己神經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還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瘋狂到毀滅,方法簡單,鼓勵她離開我。(個人容或有些自私心,不知不覺常以自己為本位看事情,易受指責。但是一個集團,有時因權力在手,也會不知不覺運用到虐待個人作不必要犧牲,滿足少數,對集團既無補益反增麻煩!)」[42]
這幾乎已是他最後的企求,和生活的全部希望所在。正如他自己反覆說的「生命經過這次大變,活下來在普通得失上已了無意義」。[43]
9月20日,他在給張兆和的信中說:「我看了看我寫的《湘西》,上面批評到家鄉人弱點,都恰恰如批評自己。」他反覆說需要妻子的理解,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理解,「我需要有這種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44]
11月18日,沈從文的日記雖然簡短,卻留下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記錄。這位被「淘汰」出局的文學家和兩個滿腦子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學生兒子談話後寫下了這樣的話:
「和孩子們談了些話。恰如一幕新式《父與子》。兩人躺在床上,和我爭立場,龍龍還一面哭一面說。
很可愛,初生之犢照例氣盛,對事無知而有信,國家如能合理發展,必可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許多事!」[45]
這齣「父與子」,他在12月25日的一篇文字中寫得更詳細:
有天晚上,孩子們從東單勞動服務歸來,雖極累還興奮。上床後,我就坐在旁邊,和他們討論問題。
「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國家那麼好,還不快快樂樂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並不十分懶惰。也熱愛這個國家,明白個人工作和社會能夠發生什麼關係。也長遠在學習,學的已不少。至於進步不進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學的不同,用處不同。」
說進步不同,顯然和孩子們說受教育不合。兩人都說:「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麼社會,現在又是什麼社會?你得多看看新書,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寫文章,怎麼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
「那也是歷史,是文化!你們不是成天說打倒封建?封建不僅僅是兩個字。還有好些東東西西,可讓我們明白封建的發展。帝王、官僚、大財主,怎麼樣糟蹋人民,和勞動人民在被壓迫剝削中又還創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實,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麼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正是為人民服務!」
「既然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快快樂樂去做!」
「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要學習的。我在努力學習。這正是不大容易進步處。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說起過,學習並不簡單,知識分子改造、轉變,要有痛苦嗎?痛苦能增加人認識……」
於是我們共同演了一幕《父與子》,孩子們凡事由「信」出發,所理解的國家,自然和我由「思」出發明白的國家大不相同。談下去,兩人都落了淚,不多久,又都睡著了。政治在千萬萬孩子心中腦中如何生根發芽,我懂得很清楚。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46]
當時他的二兒子虎虎讀初一,因為要加入少年兒童隊,把自傳寫成給他看,當讀到「父親在解放時神經失常,思想頑固,母親從學校回來,就和他作思想鬥爭。」時,他說:「這個措詞不大妥。等媽媽回來看看好些。鬥爭像打架,不是我的長處。正如媽媽,即再進步些,也不相宜。」孩子說:「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個人若耽誤了,下一期還不知什麼時候再招,怎麼辦?」說著大眼淚已掛在眼角,就像10個月前到醫院看他時的情形。他知道「政治」已滲入到一個十三歲孩子的生命中,趕緊說:「好好,把你自傳意思寫得更具體些,就交給學校中老師吧。希望你得到許可入隊,向媽媽哥哥看齊,我再向你們看齊。」[47]
什麼是「瘋子」?早在沈從文1943年寫、1946年修改的《綠魘》中就有一番解釋——
「大至於人類大規模的屠殺,小至於個人家庭糾糾紛紛,一切『哲人』和這個問題碰頭時,理性的光輝都不免失去,樂意轉而將它交給『偉人』或『宿命』來處理。這也就是這個動物無可奈何處。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缺少一種哲人,有勇氣敢將這個問題放到腦子中向深處追究。也有人無章次的夢想,對偉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懷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卻已太舊,因之名為『詩人』,同時還有個更相宜的名稱,就是『瘋子』。」[48]
「我不敢繼續想下去,因為我想像已近乎一個瘋子所有。」[49]
在這個意義上,1949年沈從文確實「瘋」了,而且「瘋」得不輕。因為無法一夜之間徹底否定自己幾十年來所「思」,所以他「瘋」了。因為不明白,他才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一旦他徹底明白了自己的「極端無知」和「渺小之至」,他就坦然了。當他終於明白「政治無所不在」,並從「思」轉向「信」之後,他也就漸漸恢復了「正常」。
假如不是他本人在時代轉換之際留下了這些文字,五十五年後,我們將難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與掙扎,那場曾經驚心動魄的「思想戰爭」。在1949年9月的陽光下,當他病情好轉時,他寫過一首長詩《從悲多汶樂曲所得》,表明他開始接受現實,從崩潰的精神狀態中走出來,他回憶起了過去美好的一幕幕:
看到吳淞操坪中秋天來
那一片在微風中動搖的波斯菊;
青島太平[山且]小小馬尾松,
黃紫野花爛漫有小兔跳躍,
嶗山前小女孩恰如一個翠翠;
達子營棗樹下大片陽光,
《邊城》第一行如何下筆;
凡事都在眼底鮮明映照,
…………[50]
以後的三十年,中國少了一個作家,而北京午城門下多了一個指點解說、抄寫說明的老人,《中國服飾研究》就是其中的結晶。
【注】
[1][5]][13][14][15][22][23][24][29][30][46][47]《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90、153、112、89、271、3、19、153、27、49、40-41、39-49頁。
[2][3]《沈從文全集》第18卷,517、523頁。
[4]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2版,340頁。
[6]《沈從文全集》第19卷,20-21頁。但據汪曾祺回憶,沈從文沒有離開北平到台灣去,「其中一個原因:他過去曾資助過一些學生到延安去。另外,他還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嚴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藝界的領導人,他認為他們會幫忙說話的。」(李輝《汪曾祺聽沈從文上課》,見《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14日)
[12][32][33][36][38][39][40][41][42][43][45]《沈從文全集》第19卷,25、20-21、22-23、18、46、48、50-51、51、52-53、52、60頁。
[7][8]《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香港,1948年3月。
[9][26][37]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14、13、13頁。
[10][11]《沈從文全集》第16卷,153-160、204--208頁。
[16][17][27][28]《沈從文全集》第14卷,456、475、455、457-458頁。
[18][19][20][21][34][35][44]《從文家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149、150、151-154、157、160-161、157、162-164頁。
[25][48][49]《沈從文全集》第12卷,369、136、156頁。
[31]《沈從文全集》第19卷,19-20頁。3月20日,葉聖陶抵北平兩天後去看沈從文,「從文近來精神失常,意頗憐之。」但他們還是「雜談一切」。見葉聖陶《旅途日記五種·北行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174頁。
[50]《沈從文全集》第15卷,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