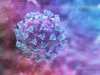我知道,揪著時代來紀念某些人物,就如進行一場心靈的撕裂。這樣的傷口有多大、痛感的尺寸能多深,自己也不甚了了。就這庚子年,從故舊的聯繫到現實的想像,在一條很悠長的軌道上,不斷地響動著你不想看或不想回頭的往事。而且,清明節說來就來,感覺就是一種鬼魅的節奏。這一回,可以預料「路上行人慾斷魂」的悽慘情景;而九州大地上,人們只要登上墳頭,那定會仰望一陣清明的天空,讓思緒飄蕩,最終聯想起庚子的病毒之災。
本以為,疫情的陰霾依然籠罩,大概許多人掃墓也難,過程的麻煩會大於一切。果然,從家鄉傳來的消息,說為了防疫安全,縣裡封山了!也就意味著所有人的家庭,都無法在清明這個時節去掃墓拜祭,成為空前的清明現象。我不能說這種決定是否又是一種極端,但或許在這非常時期可以勉強著湊合。對於依然面臨瘟疫的威脅,暫時破了老規矩的懷念故舊、寄託哀思,這樣被阻斷的不爽,大概只是冷春里的「毛毛雨」。
我是回不去了,雖閩東那老家,感覺有著最濃郁的清明氣氛。而家鄉民風淳樸、人們多為善良厚道,對傳統優良習慣的沿襲似乎也毫不含煳。紀念起祖宗先輩來,那幾分情感流露是摸得著的虔誠。每年清明,我都要努力回去一趟,尤其雙親故去之後。故鄉懷念的意義大多維繫在祈福之上,如同萬物的存在都是圍繞著人的目的。失去了親人,家鄉便成了故土;倘若沒了對故人的懷念,對活人自由快樂生存的指望,那所謂家鄉、故土也是形同虛設。
此刻,我在想像著自家從祖父手上起立的墓地。其實,祖上的那些關係親緣以及他們的過去我無一知曉。從祖母口述中,大概知道那是一撥靠耕種生活的農民,從祖父起才漂泊到這個山外之域,稍稍改變了家族的命運。對我的祖母,她做人的明理、通透,良善、大方,慈愛、關懷,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最深刻而美好的家庭記憶。在縣城西北角的山坡上,有我近30年前為祖母撰寫的碑文。如今,故土的親人變得越發遙遠,而我的死期自然也是越來越近。
人類可以坦然地面對的生老病死。現代社會,也沒太多人會去在意一個壽終正寢者的死,除非他們有什麼豐功偉績,或又是什麼名人之類,但也多出於某種的尊敬、禮貌乃至應付。至於真的悲痛,我以為也是絕少的。所謂「重於泰山」者,在今天的世界實在稀少,因為什麼時代與環境,便相應出產什麼樣的人類或人物,這很正常。像司馬遷那樣看重生命價值,而從容承受極端苦難的官員或學者、文人,彷佛一時還找不到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回不去的清明節,我就自然該寫一篇文字。來紀念一下逝者。眼下,遭遇國殤的清明,當然會將目光轉向災難中消殞的人群,特別是為無辜所施加了死神法力的人們。他們的確是不該死的,但為道義、為盡職,在一種複雜的事件推動下,讓死亡有了一層非同尋常的意義。若從社會學家的視角看,這樣的不幸,卻可以觀察出社會制度與文化的品質優劣來。但我不僅僅屬於好奇,也要加入自己的某種判斷:生命依然可以常新,可歷史沒有完全成為歷史。
近日因重讀魯迅,難免多有受先生文章及思想的幾重感染。這當然也屬於重新「中毒」,只是它更像是接種了「歷史疫苗」,具有以毒攻毒的效果。許多上了一定年紀的讀者,應該都還記魯迅那篇《為了忘卻的紀念》。那是為紀念五位「左聯」作家烈士而寫的。他們是一群先生認可的朋友,為追求真理、實現一個自由平等光明的社會,而試圖以手中的筆來抗爭的年輕人。在那「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時代,魯迅知道怎樣當一個長者與摯友。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魯迅以如此沉重的筆墨,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失望與苦悶。一個對生存清醒與自覺的人,會誕生出無窮的思緒與思想,也會生發出純粹的情緒與情感。而時代與作家,如果彼此的關係是正常的,那麼敏感與緊張便會如影隨形。或許這也是宿命。
時代的確還是有些不同了,人們也看不到舊時期兩個敵對陣營前方拼殺、後方宣傳的陣勢。一切的空間,也都是勝利者的現場。若還有所謂的「敵人」,除了對外部的假想、社會矛盾的價值觀念,餘下便是內部利益分配或佔有的噼叉。但如此這般,我等一些人,依然還是會有像魯迅先生所感慨的「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的堅持、無奈與疑問。
但有一點卻是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道真相與說真話的困境。一個偌大的足以發出雷霆之聲的世界,怎麼就一直是一個只能供養呼吸的「小孔」呢?武漢的冠狀病毒所以無限蔓延,造成另外陡增的「百分之九十五」感染者,正是缺失更多有力的「吹哨人」。如果可以立竿見影的公權力,不是時時為處在維護公民利益,守護在可能發生危險的邊緣,那麼,「為人民服務」的題中之意,就必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黨員李文亮,美好的一絲願望也難成現實。
在災難中去世的李文亮醫生,當然不是什麼特別偉大的人物。人們給他賦予一個「吹哨人」的稱號,實際上也非名副其實。他只是一個平凡但卻很正常的人,有良知,關鍵時刻能說真話。據從媒體上獲得的消息,他是被派上戰場的。當然,我堅信,即便不是被派遣,他這個有現代常識、熱愛生活的醫生,哪怕擅長的是眼科,依然不會貪生怕死而走向前線。我非常厭惡這場該死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但我還是要深深致敬與哀悼那些包括醫務的戰士。
4月2日有則新聞,說李文亮等14人被追授為此次抗疫中的首批「烈士」。是的,他們死了,在對抗瘟疫的第一線。他們原本也沒有想要當什麼英雄或烈士的,誰都會珍惜自己的生命,尤其處在和平的年代,就沒有找死的充足說法,或更無慷慨赴死的理由。特別是李文亮,處在一切正常的職業與人生的路上,竟為一場莫名的病毒來襲,一次對身邊人的忠告,被莫名「訓誡」,在背負冤屈中前往一線去救死扶傷,然後再於染病中含冤離世!
對於烈士們的評價,人們自然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再關注,而最痛心的莫過於他們的至愛親朋。雖然他們都是瘟疫的受害者,但這其中的李文亮,在這清明節里,卻是最值得單獨而特別的追悼或思考的。人們當然不會忘記2020年2月7日那天晚上,幾乎是整個武漢城都在為他點起了蠟燭。這是一種情緒,或是一種精神。它是民間的,也是純潔的。直到今天,他的死、他的悲,依然還籠罩著一層無法捅破的神秘。也並非「烈士」就能夠蓋棺定論。
李文亮終於也成了「烈士」,這是我所完全沒有料到的。他是從「小丑」變更為英雄、從屈辱逆轉為榮光的。這也是當代人類少有的奇蹟現象。在14人的烈士名單中,人們讀到一段外加的特殊說明。這如同對突然爆發的疫情採取緊急舉措一樣,也屬於一種亡羊補牢。顯然,已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那道如天崩地裂的痕跡,不是簡單地留在晝夜的大地,而是刻在人們心靈的世界。歷史也將會不斷疑問:怎麼會有像李文亮這樣的烈士呢?
但這樣的疑問,似乎也不能一樁了之。近日在武漢,居然又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戰疫「慶祝活動」。我之前就曾發出過告誡:對於瘟疫的發生,人們只能努力減災。那失去的一切都已無法挽回!面對災難,我們沒有勝利,只有結束!那麼,為什麼又會有慶祝呢?其實這是常識。江城的慶祝我以為是不能被接受的。慶祝也難免要鼓勵喜悅的。而我們,面對那些無辜的上千,不,也許是更多更多不幸的死難者,何以喜悅,褪去晨露一般的滿園悲傷?
終於,國家的公祭來了!今天,4月4日,全國哀悼。我聽到窗外的一陣汽笛聲。我不知道遠在武漢主場的人們,會以怎樣的心情融入這場紀念中。我上網極力搜索相關的資訊,但是卻看不到太多私人悼念的場面。只是幾張排隊等領骨灰的殯儀館的長龍。還有一段對話文字:「阿姨這是哪裡?我們來這裡幹什麼?」王阿姨忍住眼淚:「這裡是殯儀館,我們來接爸爸媽媽回家。」孩子雀躍著,「太好了,爸爸媽媽可以回家了!他們好了嗎?」
埋怨,憤怒;憂傷,絕望,抑或是更強烈的希望?我不知道這裡面的具體成分、比例。在我的腦海里,此刻有太多以往不同災難的歷史匯合。尤其是那些之前死於政治鬥爭運動、之後亡於類似礦難這樣人為事故的無辜生靈。一個國家在默哀之後,是否從此凝聚起一股與國民血乳交融的狀態,共同拒絕人為的悲劇;是否一道理解所有平凡生命同樣珍貴,讓一次次相似的、黯然神傷的眼淚不再掉落?假如不能刻骨銘心,公祭的汽笛又是為何而鳴?
在今天微信中,遇見了這樣對這個意外紀念日的表達:「和所有的公祭日不同,這次,我不僅悼念死者,同時也悼念我們自己······悼念所有書本里描述的世界和未來;我們悼念越來越遠去的真理,悼念我們這一代人、幾代人付出過的打拼;我們悼念每一條小溪、每一朵浪花,悼念我們棲身其間的這片土地;我們悼念激勵過我們的召喚、悼念我們歡樂時刻的每一滴淚水······」這樣富有色彩的悼念描述,讓人們更能體驗某種無法填補的紀念的空洞。
人類發生的數次大瘟疫,也許我們只能回顧那些死亡的冰冷數據,卻無從體驗史上所經歷的慘痛程度。但是,對剛發生在自家門前的庚子年瘟災,則是能真實面對、觸摸其間傷痛的點點碎片。武漢作家方方所提供的,只是其中的構成,也許並非最不堪最悲慘的那部分,畢竟更多的現場無從想像。可從她的視角,再加之各種流露出來的具體傷害過程,或還有理性冷靜地分析推斷,這場天災加人禍,足以讓人們思考:人類為什麼會如此無辜與脆弱?
如果說一場瘟疫會造成天怒人怨,這背後原因自然值得深思。客觀說,我們所經歷了讓病毒肆虐並傷害無窮的事件發生,證明了某種冷酷的存在,這等冷酷直接來自人性與常識的重大缺陷。它還以蔓延全球的姿態,來表明這種災難依然在考驗著這個最新的世界。八十年前,作家加繆就將瘟疫比作與戰爭一樣的人類災難。在他的《鼠疫》中這樣說:「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能夠對抗瘟疫的,就是正直。」
我們顯然沒能看到事件發生時,加繆所指的「正直」的強大。甚至在不斷地忽略,不斷地漫不經心,以一種謬誤掩蓋著另一種謬誤。就如事後許多人都意識到的:如果提前三個星期,或再提前一兩個月,人們就無須承擔今天這樣的驚天大災,無須勞動巨大的人力物力、時間金錢,去應對一場無謂的、傷筋動骨的病毒戰爭!不是嗎?就為一條數人間傳遞的真相與疑慮資訊,便有了從「訓誡」到「全國警示」的大動干戈。隨後接著隱瞞,接著擴散!
最近一段時間,越來越多的知識界人士開始回過神來。不少學者也開始認真檢討,從社會學或文化學乃至經濟學的角度,來重審這場瘟疫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也有人忘不了那在嚴冬的災難中掙扎的場面,感慨武漢城中流動的酸楚、艱難與絕望。同時也感歎於那麼多的以外的人,對重災區投注了真實滾燙的熱情、以勇敢的生命拯救危險的生命。災難如同一劑激素,注入人們的精神肌體,使人類真相的呈現也判若兩面:善良與邪惡。
有篇新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學SPACE學院劉寧榮教授。他對眼前發生災難後的社會反應這樣寫道:「我們已經好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在同一個時刻、為同一個人、為同一件事發出我們謙卑的聲音,吹起我們的口哨聲?而這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希望類似的悲劇可以再少些;希望我們無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懼之中;希望這個民族無論何時都是被人敬重的。」這種覺悟,當然不止局限在對瘟疫的防範,而更是人類對自身責任當擔的期待。
冠狀病毒的氾濫成災,已令近日的世界渾身哆嗦!因為它,百萬人的身體已受到感染侵害,甚至又導致了中外不同程度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此,是否能夠瘟疫及時發現、消息及時發布和手段及時實施,人們正重新從文化與制度層面,進行優劣不同的追蹤和思索。問題甚至深入到民主與威權的體制比較。儘管我並不贊同所謂「多難興邦」的簡單說法,但是,對已發生的災難,果真痛定思痛、刨根究底,斷除孽緣、革故鼎新,方可真正民福邦興!
災禍的蔓延引發了所有思想者們的高度關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本世紀最大的全球危機,其造成了廣泛深刻的巨大影響。」他還進一步認為,「迄今為止的國際合作嚴重不足。如果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不能擱置誰應該為這場危機負責的口水戰並轉而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那麼這兩個國家的信譽可能都會受到嚴重損害。」這種警告,足以讓人為之警醒。
如果一場巨大的災難與死亡,都無法喚起一切必要的思考和改變,那麼這樣的民族真就沒了指望!可以肯定的是,眼下對災難問題的思考遠未形成規模與深度。尤其從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來看,即便是這樣「就事論事」的探索反思,未來也同時會伴隨更為複雜的是非,甚至是悖論。其原因在於:我們有一個並不太清新的思想界。對於常識,對於邏輯,對於人性,對於文明,似乎都缺乏進入社會體驗層面上的共識。
相信今日之公祭,能安撫那些罹難者的在天之靈。末了,作為卑微的個人,我也依然要跟隨著,給以他們深切的哀悼。而對說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的李文亮醫生,我還是自己的那句話「有一種悲壯,是他自己給的;有一種無辜與屈辱,卻是社會的無情饋贈。」我期盼著,因為他和其他人的死或犧牲,使所有的社會信仰與主義走向真實,開始學會向每一個生命的尊嚴低頭。而不是依然那樣高高在上,雲里霧中。
2020.4.4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