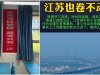2000年8月中旬,離我們村十來里地,有個跟我同屆畢業的女生瘋了。她高考發揮失常,一直挨著父母的罵。這天早晨,她拎著一壺開水倒進臉盆,一把一把掬起那水洗臉。
被人們拉離後,她喊著,「我要洗臉,水不燙。我要洗臉,水不燙……」
她在縣城重點高中讀書,被家裡寄予了改換門庭的重任。可是,她失敗了。
她的故事只流傳了一個月不到。20年過去了,我沒有再聽說她的任何消息。
在她瘋掉4個月前,我一個初中同學,在縣城一高讀書,因為違反紀律被班主任開除。馬上就要高考,母親捨不得,據說向班主任下跪求情。還是不行。
幾天後,人們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里,找到了他的屍體,旁邊放著一個敵敵畏的空瓶。
他幾乎是我十幾年讀書生涯中,最聰明的同學,一手好字無師自通,字形頗像趙孟頫。我們倆都復讀了一個初三,然後都又失敗,再次考入鄉鎮高中。
那是1997年秋天,他家湊了三千多塊借讀費,送他進入縣城重點。我家沒錢,我只好滿腔自責和屈辱,灰溜溜地去鄰鎮報到。
聽到他死訊時,我剛參加完高考體育測試,正在鄧州市新華路原四高中的校門等待返校的中巴車。
回到高中的第二天晚上,幾個跟他初中同學的朋友湊在一起,想為他維權。我讀文科班,平常又喜歡寫點東西,就被推舉為執筆人,負責寫一封信投給《大河報》,訴說這位同學被班主任逼死的委屈。
20年過去了,我至今沒寫這封信。我曾對不起的人很多,這位姓宋的兄弟算得上一位。在一些疲累焦灼的時刻,我也會想起他。他更像是去遠遊了,或許會在哪個午夜來訪,對床夜雨,或許也是一個極佳的寫作素材。
他是死去的我,我是活著的他。
高考體檢時,我只有110斤,比現在輕四十多斤,那是一種任何人看了都會擔心的瘦。只有故作漫不經心、玩世不恭的傻笑,才撐得起這具軀幹。
我幾乎每周都要忍受口腔潰瘍的折磨,高考前兩個月,口腔里一次長了五六個潰瘍,都是黃豆面大小,喝口水都疼得面目扭曲。我去校醫室,請求給我點硝酸銀溶液,以燒蝕潰瘍面。這是我們當時能想到的祛痛最快的辦法。
那位老師不敢弄,「你整個口腔都爛了,都點上,說不定會感染……」所有去火消炎的中成藥和低端抗生素,我都吃了一個遍,甚至聽說越苦的東西越能去火,就去藥店買來黃連,泡在開水裡當茶喝。
在高考前一個月,我又一次口腔潰瘍,就去校外診所里打點滴。青黴素摻雙黃連注射液,不到十分鐘,身上直打冷戰,心臟緊縮,渾身抽搐。打了3倍於成人劑量的強心針後,心率很快飆到140多下。
我被埋在兩層厚棉被下,開診所老闆,一位衛校畢業生說必須發發汗,半昏迷中,我聽到門外有一位同學的聲音,就讓老闆趕緊喊那位同學過來,被老闆拒絕。
我就自己扯著嗓子大聲喊。多年後,我回憶起這個場景,細思恐極。我真要默默死在這個診所里,同學和家人都不會知道。
鄉村里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命。任何人的生死,都難以驚天動地。在高考前大概半年,本校一位老師的夫人因為抑鬱症自殺。她是個大學畢業生,分配在鎮政府工作,聽說每晚都會失眠。
她發現只有做蜂窩煤球,才能緩解她的焦慮,於是家屬院裡都把蜂窩煤球讓她做。而蜂窩煤球終有做完的一天。
她的丈夫很是淳樸踏實,妻子死後他很快頹廢下去。
這個噩耗讓學生們也難過很久。我們難以理解,你「卡片糧」都吃上了,還能有啥想不開的?
出生於貧困,又習慣性匱乏的我們,對人生和世界的理解,都來自鎮上小書店裡的盜版書,以及閱報欄里每周會更換一次的《中國青年報》。對於世紀之交狂飆突進的繁華,我們知道得不多。
身處本縣排名倒數的高中,我們有升學的念想,卻無升學的壓力。我們的未來,就像一張兩塊錢買來的彩票,即使次次空獎,也不至於尋死覓活。縣城火車站,下廣州的火車每天都有好幾趟,誰都可以擠進去。
臨近高考那幾天,我們竟前所未有地輕鬆起來。大部分人賣掉了所有書本和教輔資料,換來的錢都去大街上聚眾吃喝。收廢紙的老頭一天要上下無數次教學樓,編織袋塞得滿滿的,到最後,我們見了他打招呼,「老表,你又來了?」
南陽方言中的「老表」,指的是表兄弟。我們無意羞辱這位老人,我們只想放縱一下。
大多數同學都買來硬皮封面的校友錄,互相寫寄語。我沒有買,也沒有找任何人題詞,不過卻挖空心思製造金句。
有一位身高超過1米85的同學,為另一位身高接近的同學題詞,「相似的身高,讓我有了結識你的衝動……」
我拿過本子,在「衝動」前邊加了一個大字,「性」。
2000年7月4日,天陰將雨。最後一節課,數學老師講了十分鐘之後,停了下來,「看來大家都不想聽了,那麼,我們下課吧,你們快收拾收拾東西回家吧……」
我騎著自行車沿著249省道狂奔,離開公路上土路,突然狂風暴雨,淋濕了後座上捆著的紙箱。我在泥濘里,推著自行車沿著路邊的草叢滑行。
我推了5公里才回到家裡,我在暴雨里破口大罵,又哈哈狂笑。
兩天後,我們幾十號同學,住進縣城兩家小旅社裡,兩三個同學擠一個屋,每人每天不到30塊的住宿費,你別奢求太多。
有個房間有台17寸的黑白電視,接著有線信號,大家圍坐在一起看陳小春版的《鹿鼎記》。班主任每隔十來分鐘就過來提醒一次,讓大家能看會兒書就多看會兒書,高考完有看不完的電視。
沒人理他。

我們高考住的倆旅社,2014年路過
這個旅社很難睡好,大家等到過了午夜才消停,早上五六點,就有人起床,在天井旁邊的水龍頭洗漱,接著便老和尚念經似的開始背書。
那幾天,我每晚只能睡兩三個小時,白天也不困。到最後一天考英語,頭有點懵,在進考場前,我在校園的水龍頭使勁沖頭,然後攬起襯衫擦頭,又將腿翹到水龍頭上沖,十幾塊錢買的皮涼鞋很快淪陷,每走一步,就「唧唧」往外噴水線。
高考結束後三天,我突然開始劇烈腹瀉,躺了三四天才好。每一次睡去,都會做關於高考和出路的夢。我夢見我拿到試卷後,一道題也看不懂;我夢見我塗錯了答題卡,或者鋼筆滴了一大坨墨,洇壞了試卷;我又夢見我赤身裸體坐在考場裡,求人借條短褲都不可得……
二十年來,這些橋段隔三差五在深夜潛入。真正的高考,我卻超水平發揮。我高考作文得了58分,使得語文原始分大概在14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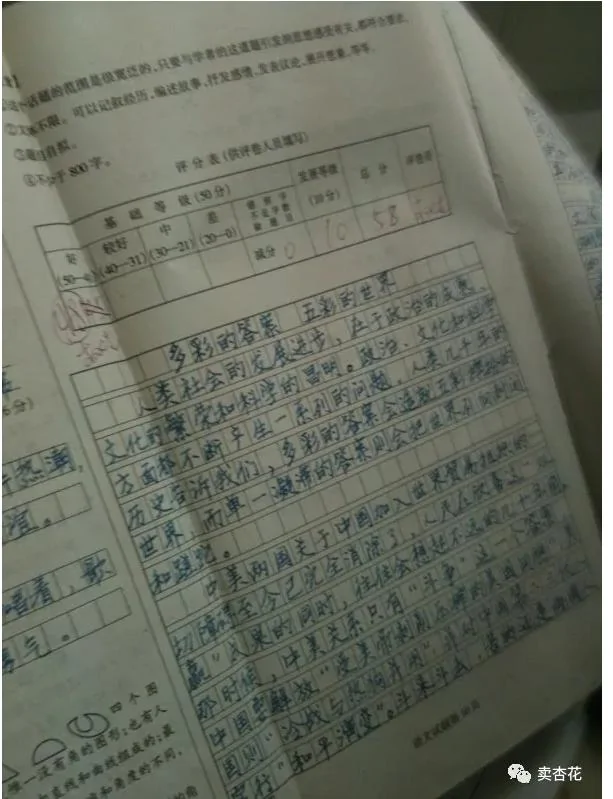
我的高考作文試卷,來自個人檔案
當年實行標準分值,有一課特別拔尖,總數會很占便宜。於是我混入了一本線。
可我很清楚自己的斤兩。所以,在關於高考的夢裡,只有一次接一次的失敗。我不聰明,更不勤奮,我只是靠一場考試中的僥倖和投機取巧,混到城市裡裝腔作勢。掀掉強作光鮮的面子,只有一個在狂風暴雨里推著自行車,一挪一步的窮小子。我隨時會被扒光一切。
高考住的那個旅社,我後來又進去過一次。2014年,老家有位農婦因為土地維權,數年上訪未果,就自立一個市政府,結果被以偽造公文罪判刑。她家就住在旅社後邊的巷子裡,我穿過旅社去她家,旅社主人問我住店不,我說不,他顯得非常惱怒。
我的高中,後來又有兩次出名。先是暢銷書《中國在梁莊》中,姦殺八旬老嫗的少年,就來自這所學校。
幾年之後,比我晚兩屆的一位校友,當兵又考上軍校,在汶川地震救災現場犧牲,高中校園裡,樹著他的銅像。他靜靜注視著校園大門外的世界,臉龐年輕堅定,就像一個永遠不會長大的少年。

武文斌銅像
三年前春節,我和十幾個同學回到高中,遇到了當年的語文老師。老師告訴我,我們的高中差點被撤併,事實上曾被撤過幾年。人過中年的老師們很想留守這個學校,就進京反映情況,他們知道我做了記者,卻沒找到我的電話號碼。
我趕緊把現在的號碼留給他。據說,現在的老師們都可懷念一二十年前的學生們,他們再調皮,也會對老師和長輩保持基本的尊敬。現在不了。
有一堂課,語文老師讓一男生背一段孟子,對方支支吾吾,他隨口批評了一句,就見勢頭不對,忙讓這學生坐下。
「再耗一陣子,他肯定會打我。」老師嘆氣,「這又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