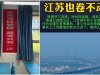1963年暑假,距離高考不到一年了,該加油了,卻趕上河北省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
傾盆大雨持續不停,據資料記載,短短几天內,阜平這個冀西山區小縣平均降雨量608毫米,胭脂河上游超過700毫米,引起山洪暴發,河水猛漲。大沙河洪峰流量高達3380立方米/秒,胭脂河為1914立方米/秒。全縣淹死15人,受傷二百多人,倒塌房屋1.9萬間。
我的家鄉小村位於大沙河和胭脂河的交匯處,形似半島。下游二十多里處的王快水庫大壩已經完工,尚未蓄水。這個小村屬於庫區,必須搬遷,全村的其他住戶都已遷走,到處都是殘牆斷壁。我家沒有勞力,無力搬遷,成了該村唯一的留守戶,孤零零的一座小土房佇立在一片廢墟中。每天夜晚,整個村子漆黑一片,沒有雞鳴狗叫,更沒有人聲,死一樣的寂靜。
大雨滂沱,聽得見不遠處大沙河的奔騰咆哮聲。屋頂漏水了,用幾個瓦盆接水,叮叮咚咚響個不停。困在孤房中已經9天,靠接雨水勉強度日,只要有點糧食,人就可以活下去。
1963年8月10日深夜,屈身在煤油燈下,趴在炕沿上練習化學題。化學是我的弱項,需要下功夫,否則在高考中將會吃虧。
當我從一道難題中回過神來時,忽然感覺外面的雨聲有些異樣,向外張望,伸手不見五指。找到幾根麻秸杆,點火向屋外照看,只見四周都是水,很快就要漫入屋內,吃驚不小。按照水庫的設計規劃,到1964年才會淹沒這裡,本來打算熬到高考後再著手搬遷,想不到大水猝不及防提前來到,事先沒有任何通知或消息。事後得知,為了保水庫下游,保住海河和天津,王快水庫提前蓄水,而且一夜之間蓄到了最高水位205米高程。
大難臨頭,首先逃命,叫醒已經熟睡的小弟,冒雨涉水奔向附近高坡。
俗話說破家值萬貫。我的破家,唯有幾件破破爛爛的生活必需品,值不了幾貫,卻是過日子必不可少的,還有一點可憐的糧食,也是維持生命的熱量來源。趕快找到已經搬遷到山坡高處的鄉親,求他們搶出一點生活物資。
有人在雨中一遍遍呼喊:「XX家遭水淹了!快來救人吶!」悽厲的喊聲劃破夜空,劃破雨霧,在山中迴響。
樸實、善良而又貧窮的鄉親們冒雨前來,奮力搶出少量主要物品,眼看水位在迅速上漲,立即著手拆房,搶出房木。這些房木,是我家的主要財產,如果被水漂走,則再也沒有能力蓋房了。自己動手拆除賴以生存的住房,心如刀割。
天色微亮時,大水已經淹沒到半牆,土坯壘成的牆壁被水浸泡軟化,幾聲巨響,轟然倒塌。
黎明時分,大雨停了。當我扛著一根房木,忍著腳掌被扎傷處的疼痛,艱難跋涉上山時,回頭一望,只見一片汪洋,房沒了,那個生我養我的家沒了。今後的日子怎麼過?想活下去,怎麼活?
回味平生,不曾做過缺德事,不曾對不起什麼人,不知為什麼老天爺給我這樣的懲罰,落了個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爹沒了已經10年,娘沒了已經5年,賴以生存的兩間房又沒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欲哭無淚。那一刻,死的心都有。
轉念一想,如果我早睡一小時,或者大水晚來一小時,則我已熟睡,後果不堪設想。既然從大水中逃了一條命出來,說明天不滅我,就應該活下去。看著小弟依賴的眼神,更應該活下去。雖然只有17歲,已經意識到我是這個家的台柱,不能倒下。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做飯吃飯。鍋灶沒有了,沒有辦法做飯。搬來三塊石頭支起一個破鍋,湊湊合合也能做飯。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睡覺。房沒了,炕沒了,沒有地方睡覺。好在天不冷,大地為床,蒼天作被,也能睡覺。颳風下雨時,驢圈、羊圈都可以遮風避雨。
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貓狗都有一個窩,人更需要一個窩。再過幾個月,天氣就要冷了,沒有窩難於生存。要活下去,首先必須蓋房壘窩,上學成了不敢奢望的夢想,我第二次輟學了(第一次是小學三年級時)。
遭此大災,沒有任何政府官員過問,更沒有任何救濟,只能自己救自己。
十多天後,水退下去了,原來的房子,只剩下一堆泥土和矮矮的殘牆斷壁。扒開泥土,挖出幾件沒有毀壞的日常用具,清洗一下還能用。之後的半個多月,帶著小弟挖房基,把房基石頭挖出來,用作再蓋房的基礎石料。
東山牆房基被挖成一個深槽,我和小弟曲身在深槽底部,埋頭撬動一塊大石頭,忽見槽壁的砂土無聲滑落,拉起小弟急逃,剛出深槽,兩側塌下填平了深槽。謝天謝地,沒有被埋在裡面。
除了自己每日辛苦勞作,要蓋房,還必須雇用木匠、泥瓦匠,脫坯、搬運房木和石料還需要力工。雖然是建造簡陋的土坯房,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尋找合適的施工人員,談施工要求,講價錢,訂立合同,交訂金,做監工,為施工人員挑水燒水,檢查施工質量和進度,驗收付費等等,這些建築施工中的各個環節一樣都不能少。17歲的我,常常感覺腦子不夠用。
水庫移民搬遷補償費少得可憐,每間房120元,每畝地60元(歸生產隊),每個碾子15元(歸生產隊),房前屋後每顆大樹1元,小樹2角。就是這些少得可憐的搬遷費也沒有及時發放到位,靠拿到手的搬遷費重建家園,遠遠不夠,只能因陋就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能夠自己幹的事情,儘量自己出力,蓋房過程中還學會了一些木工和泥瓦工手藝。
腳上被扎傷處已經發炎,疼痛難忍,狠心花了1毛7分錢,買了一包消炎粉,撒到患處很快治癒。這是我18歲前所花的全部醫藥費。
每日忙忙碌碌,無暇掛念上學的事。將近四個月後,在不遠的高處,一座簡陋的土坯房拔地而起,雖然還四處漏風,但可以避雨,又可以安家了。有了房,有了家,想上學的念頭又萌發了。高三的第一學期已近期末,加把油也許能夠趕上去。心一橫:上學去!
把家中安排了一下,讓年邁的瞎眼姥姥照看小弟,為他們磨了面備了柴挑了水,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毅然走上返校的路,心中掠過幾分淒涼。
往常每年冬季,在王林口南面的大沙河上會建一座臨時的草橋,過此橋到縣城只需步行40里路。1963年冬,因為特大洪水和水庫提前蓄水,沒有搭建這座草橋,只能繞道南路多走六七里路,經倪家窪、崔家莊再翻越一座山,由縣城西大橋跨越大沙河,才能返回學校。
漫天大雪中奮力前行,走過北果園村後,又向西走了一段路,覺得該上山了,天地之間一片白茫茫,看不到路也找不到人,茫然四顧,雪地里只能看到自己留下的腳印(那個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因為不熟悉這條路,該從哪裡上山,犯糊塗了。好在從山的走勢,還能辨別方向,認定只要翻越右手這座山,就能到達大沙河沿岸,就能找到縣城。心中有了數,毅然上山,沒有顧慮,沒有悲哀,只知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向前走。翻過山脊後,看到了遠處的大沙河,心中一陣敞亮,一塊石頭落了地。
回到了學校,回到了班級,老師和同學親切的目光和問候,溫暖著我那顆孤苦的心。雖然每天都要餓肚子,這個集體也是一個家。只要能夠活著,就要好好地活著;只要有學習機會,就應該努力學習。
耽誤的課程,奮力自學趕上,把所有的作業用破紙演算了一遍。除作文外,老師從來不要求我交作業,這是高中3年的慣例,因為我買不起作業本,只能用破紙做練習。由於高中幾年考試成績突出,兩次數學競賽都獲第一名,所以老師們對我這個特殊學生格外開恩。物理和化學老師還安排我單獨補做了實驗。
某次補做一個電學實驗,物理課老師李明智向我說明了實驗要求,並叮囑我做完實驗別忘鎖門,之後就去忙其他事了,實驗室中只剩我孤零零一個人。很順利地完成了實驗,看到220V交流電源來自一個調壓器,於是突發奇想:我把電壓調低一些,會有什麼現象?調低電壓不應該發生任何不良後果。手握調壓器手柄向低端一調,大事不好,只聽「啪」的一聲,所有的指示燈和照明燈都滅了,任何地方都測不出電壓。我知道闖禍了,不知燒毀了什麼東西。
我很害怕,燒壞的設備或器件我肯定賠不起。鎖門後,戰戰兢兢地把鑰匙交還李老師,沒有告訴他發生了什麼。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不誠實。
好幾天惶惶不可終日,就怕看見李老師。但是李老師並沒有找我麻煩,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那時李老師教物理課之外,還擔任我們班的副班主任,我知道李老師喜歡我,因為我學習成績好。猜測李老師在包庇我。
很久以後,我才弄明白我為什麼闖禍。那時山區供電很不穩定,多數情況是電壓太低。為了能夠正常實驗,李老師把調壓器反接,即把輸入、輸出端對調,以把電壓升到220伏。我降壓的操作,實際上是升壓,結果把保險絲燒斷了。
1964年元旦,我所在的阜平中學高中11班舉行了聯歡會,同學們或唱或跳或逗樂,表演的節目五花八門,校長到我班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我用笛子吹奏了一曲「紅梅贊」。置身於一個集體中,真好。
7個月後,迎來了決定終生命運的高考。又過了一個多月,1964年8月24日,帶著老師贈我的計算尺和數學手冊,帶著遍體傷痕,背起一個簡單的行李卷,第一次坐汽車,第一次見到火車並乘坐火車,來到北京來到清華園,第一次見到樓房並住進了樓房(1號樓),開始了大學的學習和生活,宛如鯉魚跳入了龍門。
大學的助學金比中學時多了近兩倍,雖然仍舊吃不飽,但比中學時好多了,購買教科書和其他學習用品是有保障的,偶爾還可以吃點肉,也能把假期回家的路費節省出來。開始學說普通話,還學著城裡人的樣子,開始刷牙、洗澡和理髮(班上同學互理),結束了剃光頭、不刷牙、不洗澡的歷史。這也許就是後來的文革中所批判的「一年土,二年洋」,但「三年不認爹和娘」批不到我頭上,因為沒有爹娘可認。
一段死裡逃生的經歷,一段艱難的歲月,刻骨銘心。幾十年後回首往事,心中仍有幾絲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