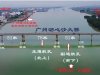大海從桌上放著的紅雙喜香菸盒裡抽出一根,吸了一口,緩緩靠向椅背。他坐著的這家咖啡館露天茶座不遠處,是內環道高架橋。車流聲持續不斷地傳來。
咖啡館距離廣州小北地鐵站步行約五分鐘,價格低廉,是大海平時和別人「談事情」的地方。
「事情」多數時候指的是生意。「Fishing」,短暫停頓後,他蹦出了這個詞,隨後又用中文「捕魚」解釋了一遍——這是他看到的新商機,然而受疫情影響,他幾乎一整年都沒有工作了。
大海來自索馬利亞,那是位於非洲大陸東部,在非洲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他的真名叫Dahir,當察覺到自己名字對中國人來說不好發音後,他乾脆取了一個發音相近的中文名。
今年是Dahir住在廣州的第16個年頭,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主要工作是給非洲商人做翻譯。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廣州的小北和三元里一帶逐漸形成非裔商貿社區,據多年研究廣州非裔社區的美國人類學家麥高登估算,頂峰時,在穗非洲人人數在1.5萬至2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據去年4月12日廣州市政府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的信息,2019年年末時,跟Dahir一樣的在穗非洲人的常態數據是13652人,而疫情出現後,2020年4月的統計人數僅為4553人。

今年1月中旬,三元里的通通商貿城
做服裝批發的中國商人Linda曾見證三元里的鼎盛,她告訴全現在,「以前商貿城裡,黑壓壓一片,全是黑人,要不然怎麼叫巧克力城?」「巧克力城」是中國人對三元里、小北一帶的暱稱,以巧克力的顏色來形容黑人聚集。
近年來,有學者研究發現,廣州的非裔商貿社區自2008年起漸漸進入退潮期。Linda也感覺到,非洲商人逐年減少,疫情之後,由於不少非洲商人無法到廣州,外貿城更顯冷清。
賺錢
媒體和學者常常用「淘金」和「追夢」來描述來穗經商的非洲人。Dahir說得更為直白——賺錢。
Dahir出生於索馬利亞的中產家庭,30多年前到北京留學時還不會說漢語。從經濟管理專業畢業回國後,正趕上索馬利亞內戰,他長期沒能找到發展機會。2005年前後,他再次到中國,這次的目的地是廣州。
但他「來得太晚了」,彼時已經有不少非洲商人占了「先機」。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被認為是非洲商人轉移至廣州的關鍵契機——受金融危機影響,那些原本在東南亞和香港的非洲商人,轉向中國大陸尋找新商機。而彼時的廣東省正在成為「世界工廠」,省會廣州自然成了他們的落腳地。1997年之後,廣州的非洲商人呈現爆炸性增長,而他們在廣州最早的聚集地,便是Dahir現居的小北。
在早期規劃里,廣州的對外商貿中心應是名為「淘金」的商圈,那裡坐落著白雲賓館、花園酒店、友誼商店等亮麗的城市「門面」;而在廣州火車站到「淘金」之間,則計劃發展出廣交會商圈。然而,廣州火車站到「淘金」有四公里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兩點之間還有大片待開發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本設計的廣交會商圈演變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商圈——「淘金」的高端國際商圈,和以廣州火車站為中心的中低端服裝批發商圈。
小北正好地處上述兩點之間。上世紀90年代,小北一帶陸續建起酒店、商務大樓、批發城等商貿功能建築,但在地理位置上,它仍屬於廣州的城鄉結合部,且不在市政發展的重點範圍,因而形成了低物價、墮胎雜亂的區域。
此外,當時香港至廣州的廣九線終點站就是廣州火車站,對於香港北上的非洲商人來說,已有一定規模的廣州火車站服裝批發商圈自然是方便的選項,而距離火車站只有兩公里遠、又物價低廉的小北地區,便成為廣州最早的非洲商人聚集地。

三元里一外貿城的進門處
「我們的年輕人,就是勇敢。」Dahir口中的「我們」,指的是非洲大陸。在他看來,不同於被保護得好好的中國年輕人,十幾歲的非洲少年只要看到機會,便敢於到世界各處去。即便在新冠疫情爆發後,仍有非洲商人願意到中國尋找商機。
Boniface來自奈及利亞。2020年2月,中國疫情稍有緩和的時候,他就獨自到中國買貨——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5月,廣州某高校一個叫二糖的大學生,拍攝了奈及利亞班機撤僑的紀錄片,記錄了Boinface的這段經歷。
根據二糖的介紹及Boniface的訪談影片,25歲的Boniface理著一個平頭,體型健碩,會說流利的英文,做皮革材料採購生意。他本來盤算的是,材料會因疫情而變得便宜,是一個值得冒險到中國入貨的時機。然而到中國後他發現,疫情供應短缺反而讓材料漲價了。
他在紀錄片中如此描述這趟經商旅程:對自己失望、憤怒,繼而很傷感。2020年4月,廣州市針對外籍人士的疫情防控加強,他需要進行自費的集中隔離,隔離結束後便要準備回國。他沒有足夠的時間採購材料,最終也未能以心儀價格購入貨物。
「就像你口袋裡原本有1000美元,而現在你沒有了。」即將離開中國時,Boniface作了這樣一個比喻。

去年五月搭乘撤僑航班離開廣州的奈及利亞商人。圖片由二糖提供
Boniface的類型屬於短期商人,他們還有一個形象的代稱——候鳥商人,在廣州非洲商人的群體中占比最大。
候鳥商人通常會在廣州以低價購入商品,再賣給非洲商家,從中賺取差價。他們每次來廣州,一般停留十幾天至數月,完成進貨後便離開,像候鳥一樣定期往返非洲大陸和廣州。據廣州市政府統計的市內各口岸數據,2017年至2019年,非洲國家出、入境的人次均超過32萬人次,且呈增長趨勢。
同樣來自奈及利亞的青年Lawson也是一名候鳥商人。他在2018年年底初次到廣州,做鞋類買賣,如今已經是一名老練的買手,每周到商貿城選貨兩到三次。
1月中旬的一天,Lawson在三元里的通通商貿城拿貨。他能說流利的英語,但中文則只會最常用的詞,例如「小北」——那是他住的地方。不過,這不妨礙他和中國老闆討價還價,用著「Colour」等簡單的英文單詞,配上手部和眼部動作,似乎就足夠理解彼此的意思。
買賣最初沒有談成。Lawson轉身走出店門,開始打包已經買好的貨。過了一陣,老闆又走過來,他朝Lawson瞪眼,又用手指指了幾處,兩人來回「談」了一會,最後老闆讓步了。當Lawson再走回店裡時,門口已經擺好兩箱貨,等著他拿走。
採購很順利。不到一天的時間,Lawson已經買下五六袋貨,它們裝在綠色編織袋裡,堆起來比他還高。「如果沒有疫情,我現在可能在非洲,但現在我只能留在中國。」Lawson說著,用油性筆在編織袋上寫下收件人信息。
「一年零六個月。」他清楚地算出無法回家的日子。
2020年受疫情影響,奈及利亞直到8月底才恢復國際商業航班,彼時想要回國的奈及利亞商人只能搭乘撤僑班機。在二糖拍攝的奈及利亞人撤僑影像資料中,撤僑航班一度延期。她的一名拍攝對象在航班計劃起飛當日才接到通知趕往機場。
機場裡,有人帶著編織袋包裹的貨物,有人在候機時和家人視頻。「他們都很開心,終於能回家了的樣子。」二糖對全現在回憶。

在機場內,準備回國的奈及利亞人正在與家人視頻。圖片由二糖提供
外貿城停滯的一年
搭乘撤僑航班回國的大多是Boniface這樣的短期商人,他們本身沒有常駐廣州的打算,而且手持的簽證時間比較短。
但隨著廣州非裔商圈的發展,相當一部分非洲人也在外貿城中開店,成為固定在穗的商人。武漢大學教授李志剛在2012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及,外貿城中的非裔批發商店通常扮演著雙重角色,店主在自己國家也有店面,又通過在廣州開店與中國商家建立聯繫進貨,同時熟悉整個流程,可以為其他非裔行商牽線。
非洲商人到來後,廣州火車站服裝批發商圈衍生出專門為非洲商貿服務的外貿城,而非洲商人的聚集地也延展至火車站北面,廣園西路沿線交通便利的三元里。直至現在,小北和三元里仍是他們的主要聚集地,被俗稱為「巧克力城」。
「巧克力城」的外貿城開業於2005年前後,在2007年達到了非裔經濟的鼎盛發展期。
這裡的格局大多相近——底層有大片空地,方便貨物裝卸;高層則是酒店,候鳥商人們進貨時可以就近入住。商鋪招牌常常混合著不同顏色,店門資料和聯繫方式多是英文。非洲商人的採購範圍很廣,從門窗五金到汽車零件都有涉及,同時也衍生出專門服務非洲人的理髮店、餐館等。

小北一帶的街頭
2021年1月,全現在在廣園西路沿線的外貿城走訪時發現,仍在開業的商鋪不足四分之一,部分僅作倉庫用,有的外貿城已全面停業或裝修。大部分樓內里貼有「減租」告示,告示多以「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開頭,有的商鋪門口還遺留著去年的催租通知。
Lawson進貨的通通商貿城,是三元里的老牌外貿城。據去年4月15日的通報,通通商貿城有兩名零工工人被確診為新冠患者,該商貿城也被認定為高風險場所。現時的通通商貿城,一層仍在開店營業的商鋪不足十家,二層的鞋城同樣冷清,一家鞋店整個下午的客人不足20人。
烏干達商人Joe在通通商貿城做批發生意。他告訴全現在,整個2020年,由非洲到中國採購的商人很少,以致他們難以拓展新客戶,生意只能依靠原本熟悉的客戶維持,用電話或網絡完成交易。據他透露,這一年的利潤下降了40%。
少了來採購的候鳥商人,店主們的營業額隨之下滑不少,一些人逐漸把生意轉到了線上。一名在通通商貿城開店的非洲老闆向全現在展示了他目前的工作模式——把一組商品圖上傳給客戶,客戶再挑選合適的。這個下午,他坐在商貿城空蕩蕩的走廊上,對著手機回了兩個多小時信息。
商貿城外牆是一張衣索比亞航空的廣告,配圖則是亞非歐區域地圖,地圖的中心點是衣索比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廣州則是另一個被特別標註的點。亞非大陸之間,有四架飛機的圖標及數條虛線,顯示兩地有密集的航班往來。正是交通上的便利,使得這種被學者稱為「低端全球化」的非洲商人經商模式得以實現,然而由於疫情,過去暢通的交通幾乎停擺。

外貿城的出貨處
Dahir認為,有些非洲商人在疫情後不再到中國做生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機票票價和物流價格上漲;二是入境後的隔離政策——兩者都讓經商成本倍數增加。
長期在廣州非裔商貿社區進行田野調查的馮啟迪告訴全現在,每年春節是非洲商人回家休息的時期,2020年疫情爆發,部分在去年提前回國的非洲商人,至今仍未能回到廣州,因此,外貿城裡一些空置的商鋪里至今還存有貨物。
Dahir最近常常收到這類非洲老闆的信息,向他打聽廣州現狀。「別回來,」Dahir告訴他們,「回來也沒有生意。」他指了一下身後,示意周邊很多商鋪已經倒閉。
目前仍留在廣州的非洲商人則不敢回家,比如Lawson。廣州飛奈及利亞的航班已經重啟,但他擔心回去之後,便再難回中國。「回去可能是容易的,但再回來就很難了。」烏干達商人Joe也有一整年沒有回家。他不擔心簽證和航班的問題,但烏干達仍有新冠新增病例,他害怕再次入境時遇到困難。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的限制,但在受訪過程中,這些仍在廣州的非洲商人均表達出和Joe類似的擔憂。人類學家麥高登對全現在分析,這和疫情期間本身的不確定性有關,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的限制措施也在隨時變化。
不過在疫情之前,政策因素也影響著非洲人到中國的經商意願。《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一書的合著者楊暘向全現在透露,她所認識的一些非洲商人在2015年後陸續離開了廣州。除經濟原因外,簽證政策是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簽證時間縮短後,他們就需要離開或者轉型。
暨南大學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博士後牛冬及教授張振江在《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8)》中發表的一篇分析提到,以2013年7月和9月開始實施的《出入境管理法》和《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為契機,廣州非洲人在華簽證續簽難度有所提高,在涉及違法犯罪時所面臨的處罰力度增加,體現了比以往更加嚴厲的管理、規訓與懲罰。

外貿城中空置的商鋪
學者李志剛和杜楓在期刊《人文地理》發表的論文中分析,2008年以來「巧克力城」的發展轉向衰落,與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的新變化有關,這些變化包括:宏觀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大事件下的國家簽證控制、地方媒體的負面報導和本地政府管制的強化。
論文中舉例提到:「2008年奧運會從三個方面客觀影響經濟區的發展,一是簽證困難,阻礙了部分黑人到廣州經商,墮胎減少;二是取得簽證的商人在廣州停留時間縮短,來回成本高,挫傷其積極性;三是已到廣州的黑人由於簽證過期變成三非人員,成為警察的嚴控對象,他們的經濟在逃逸中進行,經濟質量下降。」其後,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後,也出現過一輪簽證嚴查。
一部分人非洲商人也格外關心政策變化和時政新聞——Dahir經常轉發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視頻;不常發朋友圈的Joe會特意轉發世貿組織任命非裔女性為總幹事的消息;Lawson則會在國慶節時髮帶有中國國旗的朋友圈慶祝。
廣州過客
大多數來「淘金」的非洲人,並沒有打算定居於此。
外貿城的一些短期商人直接否認自己「住在廣州」,哪怕他們已經住了好幾個月。馮啟迪在田野研究過程中也注意到,不少非洲商人只把這裡作為「工作場所」或短暫停留的地方。而包括Lawson和Joe在內,相當一部分非洲商人長期住在酒店裡。
Joe對此解釋說,他到中國是要做生意的,因此必須選最舒適和省心的住所,才有精力賺錢。而且作為一個外國人,住酒店能省去很多麻煩。
「從非洲到廣州來,他並不是想留下來的,那他的目的是什麼?是先賺錢,賺錢之後,往已開發國家跑,比如加拿大、美國或者南非(編註:不屬於已開發國家,但在非洲大陸經濟發展水平高)、歐洲。很多時候,他們把中國,或者其他開發中國家當做一個跳板、中間站。」袁丁告訴全現在。
袁丁是人類學博士,從事非洲研究多年,他進入該領域的契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當時,中國張開國門,歡迎世界各國的來賓。「要找非洲人最容易的辦法,就是世博會期間,非洲館裡,基本上各個非洲國家的人都能找到。」
他用「過客」的概念來理解這些非洲商人,「過」既包含來來往往的意思,隱含流動的意味,同時它在中文裡又有「過錯」的意思,意味著一種「危險性」——頻繁的流動性與強調穩定的中國社會文化不同,自然會引起當地人的防備心態。
既然不尋求定居,那麼就有相當一部分非洲商人不會主動學中文。奈及利亞商人Jason在廣州住了九年,也沒學到幾句中文。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他並沒有興趣閒逛,每日生活就是起床、工作、回家、睡覺。對他而言,這個城市無異於一個大型辦公室。
對於未來,Jason沒有明確計劃,能明確的,就是不可能定居廣州。他把手舉到眉毛的位置,示意著在廣州買一套房的錢,已經夠在他家鄉買一棟樓。按照他的「計劃」,賺夠錢了就會回家,只是這項「計劃」既沒有具體日期,也沒有具體金額。
Dahir也處在這種狀態。在廣州十幾年,他用「一半一半」來描述自己目標的達成程度。他回答不出賺到多少錢才算得100%完成,而是反問道:「有誰會說錢賺夠了?」
Jason的朋友Inno是一個想主動融入廣州的人。兩年前,他來到廣州做服貿生意,如今已經能說不少中文,還會主動跟中國女性搭訕。「我就要留在廣州,我喜歡廣州。」Inno指著地板,用普通話說。喜歡的理由很簡單——這是一個能讓他賺錢的好地方。

外貿城中展示的貨物商品
但要以不同的膚色融入到這個城市裡,也並不容易。
Dahir說起,有時他用普通話問路,路人卻說聽不懂。他也聽到過有人議論他的膚色。在他看來,這算不上歧視,更多是不了解或者好奇。
袁丁透露,實際上,在廣州的日本人、韓國人這些亞裔群體,數量上多於非洲人。然而受到社會關注的卻是非洲群體最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是具有「可見性」的他者。
「非洲群體大多數都是比較深色的皮膚或者黑皮膚的,你很容易發現他是一個他者,是生活在你周邊的不一樣的人。」袁丁說。十多年前,國內學界對廣州非洲人群體的研究還很少,而在2008年之後,開始有西方學者關注到這一群體。這些研究被引介入國內後,國內的學者和媒體紛至沓來,「正因為他們很容易被發現,以及後來被關注到了,所以才成為了一個(研究)問題。」
還有一部分非洲男性商人會與中國女性結婚。據《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一書中講述,非洲男性商人認為,中國女性在生意上更能幫助他們,且婚後在中國活動會更加方便。在外貿城裡,時常能看到這種組合家庭的混血小孩在玩耍。
北京人Linda的丈夫就是奈及利亞人,十多年前因為讀大專而來到廣州,兩人結識後,一起經營服裝批發。Linda告訴全現在,她知道社會上不少人對非洲人是有偏見的,這種偏見也會波及到他們這種組合家庭。「出去吃飯時,有人會用那種異樣的目光看著我們,感覺好像你圖他們(非洲人)什麼的,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的,就兩個人的感情嘛。」她側著頭,瞪了下眼睛,斜看著右前方,做出「歧視的眼神」。
另一個讓Dahir不能理解的場景是,經常有人跟他說,今天見到你的一個「老鄉」,其實那個所謂的「老鄉」只是同樣有著黑膚色的非洲人。「他的語言我不懂,我們的文化也完全不一樣的。」Dahir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很多中國人看到黑人就覺得都是一樣的,「其實非洲很大,有很多不同的國家,人們之間的差異也很大。」
袁丁透露,非洲大陸內部是比較複雜的,不同國家間也有複雜的歷史關係,例如在廣州,最大的非裔社群是奈及利亞人,但有很多非洲其他國家的人會刻意與他們區分開來。
不過在外貿城的小圈子裡,膚色的特殊性會被日常沖淡,黑皮膚的非洲商人也不過是普通的「老闆」。大多數在外貿城工作的中國人不會以「黑人」來稱呼非洲人,而是叫他們「老外」。一個廣州本地人店主發現,這些「老外」並不想被別人注意到,只想在中國安靜地過日子。
登峰街道是小北最有生活氣息的非洲人聚集地,不同於白天的外貿城——那裡的非洲人總是提著包行色匆匆,登峰一帶的非洲人則經常三三兩兩地走著,在水果攤、雜貨鋪里選上一袋食物,路上看到有相似膚色的人經過時,他們會主動放緩腳步,打量一下是不是熟人。相熟的人會站在路邊,聊上一會兒再回到各自的酒店或出租屋裡。

登峰街,原本的非洲餐廳現已停業
疫情以來,Jason的生意變得很差。無事可做時,他會坐在電腦椅上發呆,偶爾用手機和朋友語音聊天,腳邊的CD機放著歌。來串門的保全會用他聽得懂的中文詞和他調侃,例如「有麻煩」、「老闆」等,中國商家則會用英文拜託他代看一下貨物。
「非洲人。」一個中國小孩踩著滑板車經過,衝著Jason喊。Jason抱了小孩一把,用普通話回了一句「非洲人」,小孩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