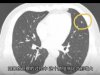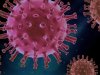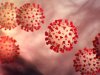孫波打了地鋪,晚上睡在街上居委會為他搭的簡易棚下|澎湃新聞
4年前剛到上海的時候,孫波的朋友圈裡出現了一棟夜色下燈彩霓虹的高檔酒店。從那裡往南一公里外的弄堂里,孫波和妻子安家在一間8平方米的閣樓,跑起了快遞運輸。
隨著這輪疫情爆發,孫波成了運送保供物資的司機,在核酸陽性之後,他在駕駛室里待了6天等來轉運。當孫波結束隔離,回到一直生活的建國東路39弄,弄堂的大門從裡面被反鎖了起來。
孫波不得不開始了一段露宿街頭的日子,期間他又去弄堂口溝通過幾次,但門裡反對他進去的居民從沒減少過。過去的半個多月里,所有人的立場都沒有鬆動。
孫波堅持自己回家的權益,居民們怕復陽、傳染、延長封控,不能接受一個在別處感染的「外人」帶來隱患。居委會說,在給居民講了政策和醫學知識都沒奏效後,他們也沒什麼辦法幫孫波進入弄堂了,他們還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把防疫工作繼續下去。

剛到上海時,孫波興奮地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貨車
39弄的8平方米閣樓
孫波的老家在安徽滁州來安縣,一個距上海300多公里的村子。到上海前,孫波靠運輸謀生,在各地跑零活。2018年9月,孫波貸款十幾萬買了輛廂式貨車,簽了五年合同,成了中通快遞盧灣二部的一名貨運司機,開始在上海跑市內的快件運輸。
來到上海幾天後,孫波的朋友圈裡出現了一棟夜色下燈彩霓虹的高檔酒店,從那裡往南一公里外是建國東路39弄康益里,弄堂里一間8平方米的閣樓,成了孫波和妻子在上海的家。
他看中了老房子房租便宜,附近的樓房月租都要四五千,這間閣樓只要1300元,離工作的網點又近。閣樓在三層,二十多平方米被分開租給了三家人,孫波和妻子住在面積最小的一間。頂著斜下來的天花板,「總是磕到腦袋」成了孫波住在這裡的苦惱。
著名作家巴金也曾暫住在建國東路39弄,他後來在作品中回憶,身處這樣逼仄的環境,睡在床上,常聽到房東夫婦在樓下的打鬧聲。同樣住在這裡,孫波不會聽到夜晚的吵架聲,他的生活是典型的晝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跑車。
剛到上海不久,孫波還在朋友圈發出過,他那輛滬E牌照廂式貨車的照片,配文「發財就靠你了!」那天他顯得很興奮,隔不久又在下面的留言裡說,「朋友們有時間來上海玩,我帶路。」
孫波確實需要「發財」。妻子成瑩在瑞金醫院做保潔員,每月進項四千多一點,兩人每月要還老家三千多的房貸,還要負擔油價連漲後每月三千多的油費,一千塊的車輛掛靠費、保險,再刨掉兩千多的房租和生活費,孩子上大學一千多的生活費,能攢下來的錢很有限。
這樣辛勞奔波的日子持續了四年,直到今年3月12日晚上,孫波又從家裡開車出去載貨,第二天一早回來,39弄所在的建一社區已經封控了。孫波去了附近的外甥家借宿,他以為,這只是疫情中的一次小波折。

孫波的保供通行證
待在駕駛室里的6天
往後幾天,上海疫情繼續蔓延。孫波也在3月20號前後拿到了一張編號為183的青綠色《上海生活物資保障通行證》。他運送的貨物從平常的快遞包裹變成了保供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每天任務就是從總部把物資運回盧灣二部網點。
這樣的保供運輸生活沒能持續太久。上海市要求保供司機每三天進行兩次核酸檢測,3月31日晚上5點多,孫波接到通知,他早上做的核酸結果異常,並詢問了他所在位置。就在幾天前,孫波所在的網點已經有一名客服人員核酸陽性。
孫波這時已經到了公司,遵照疾控人員的要求,他把貨車停在門口,人也待在了車裡。到了第二天,才有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趕來,他們沒有立即將孫波轉運,而是在他的貨車周圍拉上了警戒線,車門也貼上了封條。
等待轉運的日子很難熬,開始時,孫波靠同事從車窗遞進來的蛋糕、泡麵解決吃飯問題。之後幾天,同事中感染人數越來越多,網點也被封閉,他又靠著居委會工作人員的接濟撐了幾天。
這段時間裡,孫波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車裡解決,小便還好說,但駕駛室空間有限,上大號成了難題。他儘量少喝水、少進食,但兩三天總要解一次大手。最後實在沒辦法,他只能把車門打開一點,在車門旁用塑膠袋解決,然後再用車上的酒精消毒液消殺。
「我們開的中型廂式貨車,不比私家轎車,駕駛室里是站也不好站,躺也不好躺。」那段時間資源緊張,孫波的同事單師傅在車裡等了十多天才被轉運,他形容,人好像被「卡在裡面」似的。
孫波數著日子等到了4月6日,救護車把他轉運到一家被改建成隔離收治點的酒店。到後來孫波才意識到,這段在酒店的隔離生活,成了最近兩個月里,他過得最好的日子。

被攔在弄堂門外的孫波
被反鎖的弄堂
4月20日上午,孫波拿到了《解除集中醫學隔離證明》,他回到建國東路39弄門口,做好抗原檢測和信息登記後準備回家。
在孫波的描述里,回家過程中的第一次「不愉快」就此開始。弄堂的卡口裡走出來一位居委會工作人員,當聽到孫波不是從39弄被轉運隔離的,他表示,既然不是從本小區拉走的,就不能進去。「你是從哪裡被隔離的,就回哪裡去。」
孫波向正在建國東路上巡邏的警察求助,警察說他可以回家,讓他到居委會找工作人員。孫波去了居委辦公樓,在那裡,他遭到了一位黃浦區下沉駐點的幹部的質問,「問我是怎麼進來的,我說自己是小區居民,來報到是為了回家。但他又打電話叫來幾個人,還說要把我扔出去,邊說邊拎著我的東西往外扔。」
爭執過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核實孫波的身份,需要房東出具的租房合同。孫波是從二房東手上租的房子,第二天才能拿到合同。於是,孫波托居委會工作人員把妻子成瑩準備的被褥拿出來,4月20日這晚,他在街上露宿了一宿。
前述黃埔區下沉駐點的幹部告訴深一度記者,那天發生爭執,是因為孫波未穿防護服,就擅自闖入了居委會辦公的封控區。當時也不能證明他是住戶,所以當晚沒讓他進入小區。
4月21日,孫波將各種證明備齊,晚上8點多,社區通知孫波可以回家了。妻子成瑩先把他的鋪蓋拿上樓,不到十分鐘後,成瑩再次下樓,發現弄堂門被居民從裡面反鎖了。「孫波就在門外,門裡有二三十個居民,拼命喊著不讓進。」
孫波說,他隔著門向居民解釋,自己是運輸保供物資的司機,也是為了上海防疫。但依然有居民喊道,「你從哪個車隊來的,就回哪個車隊去!」
孫波也激動起來,他沖門裡喊:「你們沒有資格、也沒權利鎖門。居委會和警察都在這,你們說了也不算,我說了也不算。」但在場的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孫波,門被居民鎖起來,她也沒有辦法。
事後,這位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她曾向居民解釋,既然孫波隔離回來,就說明沒有傳染性了。但居民情緒很激動,當晚沒讓孫波進去,也是為了孫波的人身安全。「如果他當時強行進入,說不好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居委會要把這個風險預見到。」
那晚,僵局持續到近11點。孫波堅持,按照政策,自己回家是正當的。但居民們一直態度堅決,不肯開門。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他們和駐點民警都在給居民做思想工作,但他們太激動了。居民們主要擔心兩點,第一是孫波從方艙回來有可能復陽,繼續傳染。其次,弄堂從3月12日開始封控,孫波是在外面感染了新冠,所以覺得他進來不安全。
這名居委工作人員嘗試分析居民們的心理,截至4月21日,39弄內部還沒有出現過陽性病例,是乾淨的。「他們擔心再有新的陽性病例出現,會拉長封控的時間,大家都希望早點解封。」
孫波不得不繼續露宿,次日凌晨,居委會工作人員幫孫波在39弄對面的街上搭了簡易棚。孫波做了當時最壞的打算,政策要求居家健康監測7天,那自己就在小區外睡上一周。「小區居民不是怕嗎?那我就再等一個星期,這總行了吧?」
妻子成瑩很不理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麼多居民阻攔丈夫回家。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解釋,39弄是成片的老房子,屬於二級舊里,本地居民大多是幾十年的老鄰居,都很了解彼此的情況。
回想在39弄生活的這四年,孫波說,他本身話就不多,又是晚上幹活、白天在家休息,和居民沒什麼交集。居委會工作人員也說,在39弄住著110位居民,租客與本地居民約各占一半。孫波夫婦都是打工者,早出晚歸,平常和鄰居們沒有矛盾。但孫波有一點很介意,在弄堂口阻攔他的,大多是本地居民。
4月22日,孫波本來不想再和居民接觸,但居委會工作人員勸他,還是再試著和大家溝通溝通。
在居委會工作人員錄下的視頻里,孫波又站到了弄堂口,他向居民們展示著自己的《保供通行證》,解釋說:「我是一個駕駛員,為了上海疫情運送保障物資,也是為了上海市民。」
一個上了年紀的男性居民入鏡,打斷孫波,「上海市民大了。你不要藉口你住在這裡,你老婆是在這裡。但3月12號我們第一次做核酸,就沒看到你這個人。你就不要講了,也不要拿這個報告來(說)。你作為一個駕駛員,進去方艙醫院,(出來了)你去找你的車隊去。你說你支援上海,你是哪個車隊的,回去找你們領導去。」
聽了這話,孫波也激動起來,不斷重複:「你們就不講道理!」
一個女性居民嗆聲道,「怎麼就不講道理了,你不講道理還是我們不講道理?我們第一次做核酸的時候就沒看到你。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
直到孫波最後轉身離開弄堂口,他身後居民們的反對聲都沒停下。

孫波的解除隔離證明
被加重的牴觸
4月23日,孫波露宿街頭的第三晚,建一社區所屬的打浦橋街道黨委副書記給他打來電話,說可以提供應急隔離點作為暫住地。孫波聽說那裡不提供餐食,拒絕了這個提議。
孫波說,睡在小區對面,離家近還算方便。他又不會下單點外賣,到了隔離點更麻煩。他之前請別人幫忙訂過外賣,下午五點多叫的,八點多才到,還是夾生的。孫波和妻子使用智慧型手機都不熟練,之前物資緊張的時候,兩個人搶菜都困難。
最初住在街上的幾天,商鋪都不開門,妻子給孫波送出來一點八寶粥、方便麵,一天吃一兩頓飯。沒有熱水,他只能去附近公共廁所接一點自來水,用冷水泡麵。有時候,附近的大白如果工作餐有剩餘,會好心勻出一點給他。
4月24日,孫波的妻子成瑩也因為核酸陽性被轉運到了新國展方艙。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成瑩感染後,居民們認為,這是她給孫波送飯導致的,對孫波的牴觸更大了,度過「7天觀察期」後,他還是沒能進入弄堂。
雖然建一社區有過陽性,但成瑩是39弄內部的第一例陽性。居委會工作人員覺得,社區里按弄堂分時段做核酸,互相傳染的可能性很低。但成瑩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說,每次給孫波送飯,出門和回來時都會噴好幾遍消毒水,她更認為,自己的感染可能源於一次核酸檢測。那天輪到她做核酸時,工作人員正好要清點採樣管數量,沒在第一時間給她採樣,她也忘了把摘掉的口罩提起來。
5月1日,成瑩從方艙回到家裡,她進入弄堂時沒受到什麼阻攔。前述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從科學上來說,孫波夫婦情況一樣。但從居民的情緒上來說,成瑩封控期間就一直在弄堂里,是不一樣的。
就在妻子回來當天,孫波已經快一天沒吃飯了。在他的印象中,露宿街頭的半個多月里,建一居委會一共給他送過三次食物。第一次是4月21日晚,遇到居民阻攔後,陪在一旁的居委會工作人員送了一份工作餐。第二次是某天下午3點多,工作人員給他送過兩個包子、一個雞蛋,此外就是妻子在方艙期間,社區發物資,孫波分到過一隻鴨子、一塊牛肉和兩根火腿腸。
剛回到家,成瑩就做了飯,送到弄堂對面丈夫那裡。晚上,居委會工作人員帶著民警找到成瑩,說有居民投訴她在居家健康監測期間外出。民警提醒她,要居家七天,一次核酸陰性後才能出去。
成瑩反問民警,「政策要求是七天監測,孫波已經在外面待了十幾天,一直參加小區組織的核酸,兩天做一次,一直是陰性。為什麼還不讓他進來?天天吃方便麵,他現在聽到方便麵都要吐了,吃那麼多方便麵哪個人受得了?」
自這次之後,成瑩再沒出門,但居民們還是知道了送飯的事情。弄堂里本來地方就不大,打開窗戶看得一清二楚,現在被封了這麼久,更是都眼巴巴地盯著堂子裡的情況。居委會工作人員也對成瑩有「埋怨」,說本來想等成瑩七天居家結束後,再做一次居民的工作,爭取讓孫波回家,「但她這樣一弄,思想工作就難做了。」
總還是要回去的
建國東路是打浦橋街道和淮海中路街道的分界線,孫波露宿的那一側,已經到了淮海中路的地界。那天一個巡邏的警察知道了孫波的情況,對孫波說,如果是在他的轄區,一定會把孫波送回家。旁邊的人也跟著應和,說這個警察已經把20多個進不去小區的人送回家了。
這位警察走後不久,孫波住的簡易棚被淮海中路街道的城管人員拆除了。在建一居委的協助下,孫波把棚子搬到了39弄東南兩百米的路口,繼續他的露宿生活。
孫波的同事單師傅告訴深一度記者,之前網點感染的十幾名工作人員現在都已經出艙,回到了各自小區,只有孫波還流落在外面。
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在5月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解除集中隔離後的復陽人員不影響所在小區的「三區」劃分。深一度記者也向居委會工作人員證實了這項政策的存在。但他們表示,居民們的態度一直沒有鬆動,居委會也沒有辦法,估計要等到解封之後,孫波才能回家。
對於居民是否有權阻止孫波進入弄堂的問題,黃埔區下沉駐點的幹部沒有正面回答,他轉而談到了關於「穩定」的問題,弄堂從3月12日開始封閉,他們需要所有居民配合做核酸、配合各種防疫工作,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我們覺得穩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也希望他能進來,但如果他進來會對弄堂造成很不必要的不穩定情況,我們也要去花很多精力去處理。」
5月7日,孫波露宿街頭的第18天,他在附近的公共廁所遇到了一位警察,幫他聯繫了民政部門,把他接去了臨時救助站。救助站是一個倉庫改建的,擺著一張張鐵架床,能提供熱乎的飯菜。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告訴孫波,只能暫時收容他一周,一周過後,還需要再申請延期。在孫波離開街邊的簡易棚後,居委會工作人員曾給他打過電話,詢問去向。
孫波說,他還是更想回家,「我家屬是個急性子,我在小區對面睡,她一推窗就能看到我,還會安心一點。如果看不到我,整夜都睡不好覺。」
他習慣用「家屬」稱呼自己的妻子。這幾年在上海,每天早上4點半,妻子就會起床,簡單收拾後去瑞金醫院上班。下午四點半鐘下班後,又買菜做飯,喊孫波起來吃晚飯。晚上七點多,孫波就要出去工作。再回來就是第二天早晨了。一個早出晚歸,一個晝伏夜出,他們兩個人相處時間的很少。
孫波之前對上海的印象很好,覺得這裡環境整潔,有文化底蘊。但這次的經歷,讓他覺得遇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遇到了不講道理的鄰居。
孫波已經想好了,明年9月份合同到期,他也53歲了,就離開上海回老家。但在這之前,如果不遇到什麼阻礙,他總還是要回建國東路39弄住上一段時間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成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