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是有風險的,堪稱平凡人的英雄之舉」。
——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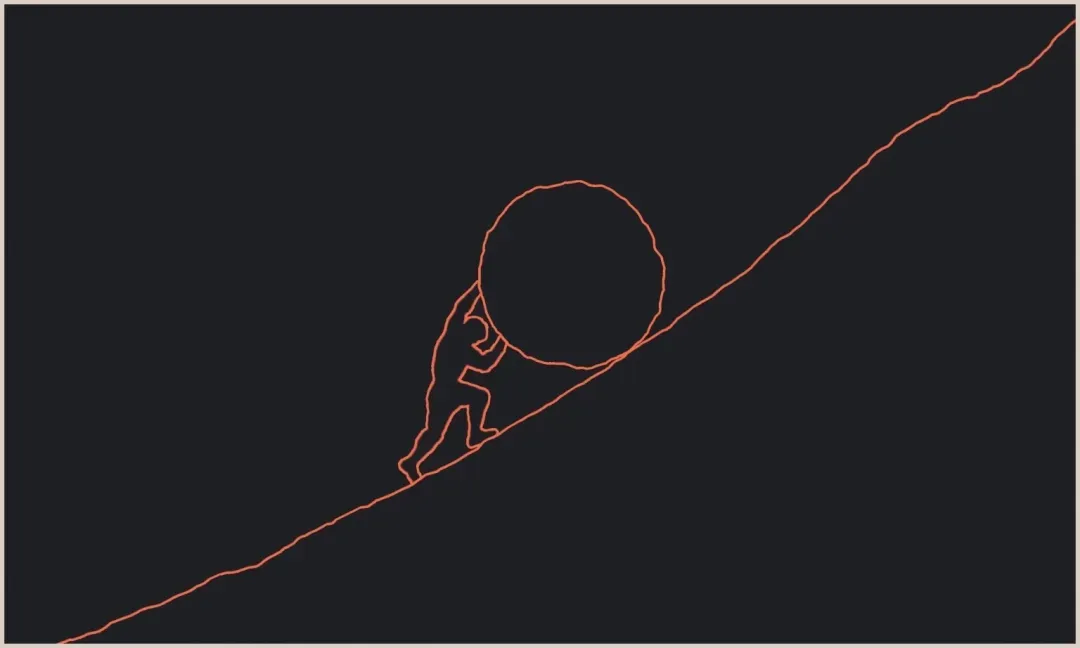
被封了近兩個月,現在鄉下很多老人也想開了。以前他們還指望著養兒防老,至少自己病重時有照應,但現在,別說是得病,就算是死了,再孝順的兒女,也被封在上海回不來。
母親說,很多老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活糊塗了,不知道這過的是什麼日子,但又好像看清楚了,能好好地過一天是一天,別的都是空的,兒孫都是身外事,連原先幾個最積極催婚催育的老人,都覺得無所謂了。
這種困惑和頓悟都是真實的,對中國人而言尤其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吳飛在《浮生取義》中曾說,中國人所理解的「過日子」與西方那種「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最根本不同,在於它是一種家庭內部的存在狀態和政治狀態,人們是在家庭中理解人性並活出人樣的。
現在,防疫作為一種勢不可擋的外部力量介入到這一有機的生活中,迫使人們獨自面對一個陌生而龐大的無機物,那是一種卡夫卡式的困境:人們忽然發現自己被扔進一個根據直覺無法理解的邏輯所建構起來的世界裡。
那就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例外狀態「能在一切語境下打散各種生命形式,終止它們與形式生命所保持的結合」,使所有人的自然生命直接暴露在主權暴力之下。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機紐帶遭到大規模隔斷之後,個體的人赫然發現只剩下了自己,連繁衍血脈這樣對中國人來說近乎宗教的信念也已喪失了意義。

《芙蓉鎮》劇照
當然,我也看到一種說法:「赤裸生命」總比「沒命」要好,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有時出自一種頑強的本能,但也有的時候,正是這種求生欲塑造了中國人的無底線的順從和忍讓——只要能活下去,沒有什麼是我們不能讓渡的,甚至還不乏有人指責那些不肯讓渡的人「矯情」。
5月5日,普陀區成為上海第一個社會面清零的城區,桃浦的居民領到出門證後,為首的舉個牌子,20人一組,像小學生春遊一樣到指定的小超市購物,每人限購不超過300元。買完了,再原路返回,不能脫離隊伍。
在鄭州,有些市民因為未能遵守防疫規定,被要求在馬路邊罰站,承認錯誤並背誦防疫規定。在一段北京防疫貼封條的短視頻中,對比了兩戶人家:一位大姐極力阻撓,非常不配合,而另一戶男主人就非常「顧全大局」。
像這樣的場景,這些天來已不鮮見,常常是作為笑中帶淚的段子。這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成年人,無論他們內心是否真正認同,都像是被規訓得相當乖順的小學生。活著,在此意味著要成為一個遵守共同體規則的合格成員。
不論人們是否意識到,這難免會在他們的生活中造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張力,因為這種重負威脅到人的完整性與本真性——為了滿足自己所渴求的安全本能,你不得不屈抑自己,無法公開、充分地展現自我。這是一種「半自由之身」(half free)。
那就像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別里科夫:「現實生活讓他總是感到心神不安,讓他害怕,為了同世人隔絕,不致受到外界的影響,他總想給自己包上一層外殼,給自己製造一個所謂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艷陽天出門他也總是穿著套鞋,帶著雨傘,他的雨傘、懷表、削鉛筆的小折刀等等。」

上海永康路一位倒立的年輕人
在此,「做自己」是有風險的,甚至堪稱平凡人的英雄之舉。在馬路中間的倒立、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捍衛,並不僅僅是衝動或矯情,它是某種讓我們體驗到自己存在的瞬間,由此確認:我還活著,還活得像個人樣。
有時弔詭的是:人們體驗到自我,往往並不是因為他們主動做了什麼,而是他們發現自己喪失了太多,以至於只剩下了自我。也正是在此時,他們赫然發現,自己的順從、配合,並沒有換來作為一個人存在所應得的最低限度的承認。他們被無視了,也正是在這種被無視的狀態中,他們看見了對方眼裡自己的形象。
個人尊嚴就像空氣:在稀薄的時候我們才充分意識到那是生存之本。在一個不斷縮小的空間裡,人們被迫專注於自我,有時是重新發現了自我。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樣用某個社會身份標籤來界定自己,雖然他們也許還沒真正想明白現在需要成為什麼人,但會越來越認同「我就是我自己」。外面那個宏大而喧囂的世界逐漸變得像是熒幕上的一齣戲劇,不知不覺中,我們的經驗感知發生了可能是不可逆的變化。
伍爾夫有一句名言:「在1910年的11月,或者大致在這個時候,人類本性便發生了變化。」她以一個文學家的敏銳,捕捉到先於世界大戰的那種風暴:隨著一個相互協調的公共生活崩塌,現實變成多元異質、主觀闡釋的私人體驗,人們只能在最小的私人圈子和個人處境中,在弱音(pianissimo)中,感受一種精神性體驗,並由此重建人的價值。
也許多年後回望,這場疫情將被證明為我們社會的一次脫胎換骨:沒有人能逃脫這樣的體驗,每個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在迷茫、掙扎和覺醒的陣痛中,有些人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次出生。那是一個新的自我。
「人的尊嚴」看似老生常談,但在中國思想中其實是新事物。如果說西方是經歷了文藝復興的洗禮,在脫離了神的束縛之後才出現了「人」,那麼中國的「人」從何而來?也許五四時是對「家」,衝決「家」的網羅才出現了獨立人格意識,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人的尊嚴」主要是對抗外部主宰力量時而言的。
我知道,很多人把當下的自我屈抑當作一種戰術性的隱忍,想著「回歸正常生活」之後「重新做回自己」,但歷史不可能只是簡單的重複。疫情前的那種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何況現在人們所想的也是一個建構出來的過去而非真實的過去,就算我們想著「往回走」,事實上也還是在「向前走」。
無論疫情是否過去、怎樣過去,個人的覺醒和自主選擇是唯一的救贖之道,這需要我們每個人充分體認到對生命的尊重,活出人樣。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里,當你真正意識到,沒有什麼能真正凌駕於人的尊嚴之上時,會獲得一種平靜的力量,我想,那就是孔子所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