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10:48,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先後在推特、微博上宣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去世。CCTV等各家媒體隨即跟進轉發,此事在網上迅速傳開,但11:17袁隆平的秘書出面說明仍在治療,人民日報等官方渠道出面闢謠,輿情頓時反轉,到11:57,CGTN表態「對此前報導不慎深表歉意」。話音剛落,消息又傳來:袁院士於13:07去世。這次是真的了。
像這樣的輿情再三翻轉,這兩年也早已不鮮見,耐人尋味的倒是在「闢謠」之後許多人的反應:他們並不是質疑各路媒體的新聞素養,而是懷疑這「傳謠」是受「境外勢力」操縱的破壞性行為,譏諷「CGTN是不是收了美金」,甚至連「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樣的話都搬出來了。
當然,這些話或許也不免有戲謔的成分在裡面,但國內近些年的公共事件,到最後往往都不免牽扯到那個神秘的「境外勢力」。連前不久成都中學生墜亡事件之後的悼念活動,也有人這樣言之鑿鑿。不管聽起來多麼令人匪夷所思,確實有一大票人深信不疑。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有那麼多國人在遭遇公共事件中大大小小的問題時,容易歸結為「境外勢力」?
一百年前,美國傳播學家沃爾特·李普曼就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指出:公眾的反應其實並不是針對真實世界,而是對自己頭腦中的那個「虛擬世界」。他說:「如果對一件事情產生了強烈憎恨,我們很容易就會把它同我們所強烈憎恨或恐懼的絕大多數事情聯繫起來,認為它們之間有著因果關係。」

這其實是人的本能。如果你所接收到的信息一直告訴你需要擔憂某件事,那麼一旦有什麼事發生,你自然會第一反應聯想到它。前些年,有隕石在西伯利亞墜落,半夜發出巨響,一位當地老婦事後回憶,她第一反應就是:「美國人終於打進來了!」
人們據此相信,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壞事,正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神秘勢力所為。只不過,中世紀的人們會詛咒是魔鬼在搞破壞,近代的西方人歸結為神秘的共濟會和猶太人的幕後黑手,前些年川普和他的擁護者則譴責那個操縱美國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
至於我們中國人,以往多是指向「階級敵人」,而近些年來則越來越多地訴諸「境外勢力」。這種矛頭的變化,本身就體現出中國社會一種深層次的結構變遷:「我們」從一個按階級紐帶(「親不親,階級分」)連結的共同體,轉變成了一個邊界之內的緊密整體。
既然破壞力量本質上都來自或從屬於「境外勢力」,那麼隱含的推論勢必是:「境內」的我們必須保持團結一致,因為任何異議、抗爭,都可能被視為是在有意無意中「遞刀」,剛好方便了敵人「從內部分化、肢解」的陰謀。只要這種情緒喚起,它的見效是如此之好,以至於成了一個終極大殺器,一旦祭出來,幾乎總能立竿見影地讓人閉嘴。
這種社會心態的轉向,與1990年代「告別革命」之後的趨勢是一致的。那意味著「中國轉向自身」,從國家、民族、文化中尋找自我身份認同。這樣,既然「國家」是一個緊密團結的整體,那麼理論上破壞力量就只能來自外部了。
實際上,這非常接近一個封閉的傳統大家庭里提防「外人」的家長式心態。也就是說,一家人應當不分彼此、絕不能向著外人,而有任何事,都只能是外人的挑撥離間所致。因而與這種對「境外勢力」的指控相一致的是,很多人極為反感任何在他/她看來是挑起社會「撕裂」的行為,因為那就破壞了自己心目中那個和諧的整體。

在國內網上時常可見對「白左」、「聖母」的嘲諷,這或許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是注入某些普遍主義元素(如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相反是隨著「天下」的崩塌和對「公理」的失望,經歷了對普遍主義元素的幻滅與剝離,這與許多國家大相逕庭(如美國的民族主義是普遍主義的面目出現的),倒是與拿破崙戰爭後的百餘年裡德國的思潮類似,即將普遍主義視為帝國主義統治的遁詞,而主張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與道路。
自近代以來,「愛國」話語就已成為超越不同政治立場、主張、思想背景的共同基礎。日本學者吉澤誠一郎認為,這與報紙、雜誌等近代媒體的流通關係密切,使民族情感被廣泛地共享和再生產,進而意味深長地指出:與其說愛國主義主張有著邏輯說服力,不如說是因為訴諸感情。
在一個危機年代,出現這樣的主張是不必意外的。20世紀初,右翼的「法蘭西運動」領袖夏爾·莫拉斯就曾提出「重建民族主義」,認為法國作為一個大國,在面對德國、英國這樣強大的外部敵人,必須放棄共和。他傾向於回歸古典秩序,將保守的天主教會作為穩定的基石(儘管他本人並不信仰),而把猶太人、新教徒這類「非法國」的因素從一切有影響力的位置上清除出去。
反觀中國當下,這種防禦性的反應也可見個體命運是與共同體緊密捆綁在一起的,尤其取決於其高度穩定,而不容任何「破壞」。這或許比朝向內部敵人要好,但在強化凝聚的同時,也不知不覺中轉向了自我封閉,因為外部世界已經被視為一種無法掌控的威脅。
這倒也並不是說這全然是空穴來風,但這個含糊曖昧的指稱其實是難以證實的,也因此更是無法證偽的——對於相信的人來說,永遠能找到無數「證據」來支撐自己的結論。這就會出現一種對峙的局面: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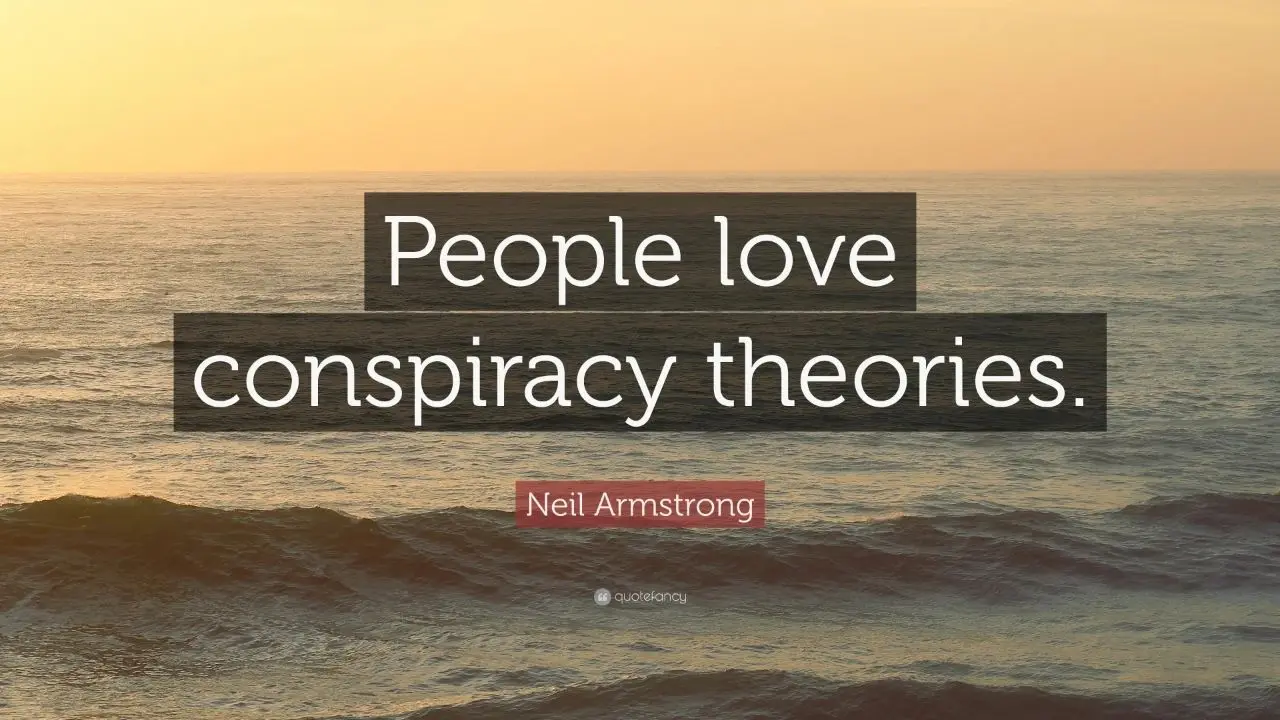
透過這種稜鏡來看待世界的個人,也因此很難成為一個獨立的、自主自決的主體,而類似榮格所說的「無意識的主體」,他對環境的認知,其實是一種建立在虛幻關係上的投射,這會導致自閉,因為他會「夢見一個其現實永遠也無法達到的世界」。這種無意識因素遮蔽了世界,編織成一個繭,最終將他自己封閉在裡面。
公平地說,在不同社會中,這樣的現象多多少少都有。在登月被民間渲染為一場「好萊塢拍攝的陰謀」之後,太空飛行員尼爾·阿姆斯特朗也曾感慨過:「人們熱愛陰謀論。」
若說中國有什麼不一樣,那或許在於,一方面,中國社會其實是陰謀論的沃壤;但另一面,很多人甚至都意識不到「境外勢力」的說法也是一種陰謀論。它創造了一種讓也許是大多數人舒服的幻覺:「我們」所有人都是緊密無間的,那些異質的聲音都是有意無意受外部敵人操縱的結果,從而也就避免了痛苦的自我反思。
但是阿倫特說過:「只要有人呼籲團結,就會有人窒息而死。」曾發誓「永不離開波蘭」、親歷波蘭社會在「告別革命」之後轉向「國家、教會、傳統」的亞當·米奇尼克也曾表達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才是真正的波蘭人。」很難說中國社會將如何演變,但如果能有所變化,那或許應當從我們每個人勇於自我反思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