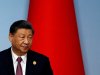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喜歡重刑。
漢文帝的時候,有一任廷尉(相當於大法官兼司法部長)叫張釋之,有一次有個盜墓賊偷竊了漢高祖廟裡的玉環,被衛士抓獲。漢文帝十分惱怒,於是就責令張釋之嚴懲此人。
張釋之審了半天,依照當時的相關法律,奏請文帝判處他棄市。
文帝一看這個結果就大怒,說我把這個人交到你手上,為的就是讓你判他個夷滅三族,你居然只把這個人砍頭了事,你這也太糊弄領導了吧!
漢文帝的意思就是,這事兒我很氣憤,所以你必須搞株連。
張釋之一看到天威震怒,就脫帽叩首說:「皇上啊,依照法律,棄市已是最高處罰了。如果您覺得盜竊個宗廟器物就要誅滅全族,如果以後有人偷挖長陵上的一抔土,又該如何處罰呢?」
漢文帝很聰明,一聽這話,就有點醒悟,回家跟老媽薄太后商議了一下,就批准了張釋之的判決。

我覺得,相比那些動不動就要「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看鐵蹄錚錚,踏遍萬里河山」的「大有為之君」們,漢文帝這個人,好歹算是個有點人味兒、會說幾句人話的君主。他有的時候真的能俯下身子,站在平民百姓的視角去審視問題。
你看他想修個露台,一聽說要花費十個中產之家的財產,立馬就不幹了。
這在中國古代的王侯將相中,是一種大熊貓一般的稀有性格,後世帝王,大概也就宋仁宗又靈光乍現了一回,其他帝王將相想的更多都是「我的計劃很大,你們忍一下」「再苦一苦百姓」之類的玩意兒。

而漢文帝的這種平民視角尤其體現在他對司法的量刑主張上。
漢襲秦制,本來法律是相當嚴苛的。可是有一次,齊地的官員淳于意犯了罪,依律要執行肉刑,他的女兒緹縈就給文帝寫信,說:肉刑這個刑罰實在是太殘酷了,肢體被砍掉了,就沒辦法再長出來,以後犯人即便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過原來的生活了。身為女兒,她請求文帝不要讓父親接受這種刑罰,而作為代償,她願意自己賣給官家做奴婢。
漢文帝接到這封信之後就深為感動,同年就下詔廢除了肉刑。不僅如此,他還舉一反三,覺得一人有罪,親屬鄰里連坐這個刑罰似乎也沒有什麼道理——淳于意犯罪,為什麼要把他的女兒賣為奴隸呢?所以文帝又幹了一件後世非常少有的舉動,那就是廢除了先秦以來一直沿用,已經被視為天經地義的「連坐法」(首孥連坐)。
如果按照法家那種「老百姓就是欠管,不重刑就會亂」的理論,文帝朝的大漢應該是一個狼煙四起,各地盜賊紛紛扯杆子造反的時代。可是歷史的事實證明,文帝時代,恰恰是秦漢帝國、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帝制時期治安、民生都最好、經濟恢復最迅速的時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一直到今天都被拿來吹牛。這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三個正經當了幾年皇帝(之前是秦始皇和漢高祖)的人,漢文帝開創的這種(相對而言的)輕刑主義思想,其實是行得通的。
然而,這裡面有個問題,那就是文帝開創的這種輕刑主義傳統,在古代中國終究只是曇花一現,連坐、肉刑等制度在他死後很快就被他的子孫景帝、武帝那裡被恢復了。到了司馬遷因為說錯一句話關鍵部位挨了一刀的時候,太史公雖然覺得自己這一刀挨得很冤枉,但已經無法像當年的緹縈小姑娘一樣,說出砍掉的肢體不能再長出來,所以肉刑不對這種有樸素的法理學認知的話來了。
整個中國古代其後的刑罰發展史,基本上就是沿著用刑越來越重,株連越來越廣的方向去演進。株連範圍從最開始的「夷滅三族」、發展到後來的「誅九族」、「十族」乃至「瓜蔓抄」。而殺人的方式,從最開始的砍頭、棄市發展到了後來的腰斬、凌遲……
我曾經一度非常奇怪,為什麼我們古代歷史上明明有漢文帝那樣有人情味、知道「節刑」的上位者,卻依然拉不住法律的韁繩,讓法律朝著重刑的一邊絕塵而去呢?
直到後來,我又重溫了漢文帝與張釋之的這個故事,我才看出了一點端倪。你看,在這個故事中,漢文帝本來是個非常注重節制刑罰的皇帝,但聽到有人偷了他老爹廟裡的玉環,氣血上涌的時候,他依然高喊著要夷滅這個人的三族,完全忘了不株連、輕刑罰本來是他自己的主張。這當然可以理解——泥人還有三分土性呢,誰聽說別人辱及自己祖先時能不發怒呢?
在古代帝制的那個系統下,「天子一怒」是容易被縱容,而很難被掣肘的。漢文帝的幸運,在於他碰見了一個敢抬槓的張釋之,斗膽把他的衝動頂了回去,讓皇帝恢復了冷靜。可是,在中國古代史上,真正能像張釋之那樣直言敢諫的臣子有多少呢?像文帝那樣能在盛怒之下聽得進不同意見的皇帝又有幾個?至少到他孫子武帝那裡,就早沒有了這樣的雅量,張釋之若是生在了武帝朝,這樣跟皇帝頂牛的結果,多半是和太史公一樣,被一刀了斷了是非根。
所以重刑主義是所有人在憤怒時共同的衝動,而當一套體制沒有機制遏制這種衝動、對法律進行回調時,司法向著重刑滑坡就會成為一種必然。
這種滑坡,讓人想起了生物學上的「左牆定律」——一個醉漢,蹣跚的走在一條路上,左面有一堵牆,右面有一道溝,他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早晚會調到右邊的溝里,因為這個進化模型中一個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種在隨機進化過程中,早晚會走向相反的那個極端。
中國古代的法律進化史,其實也高度遵循這種「左牆定律」——由於憤怒的皇帝與憤怒的公眾總是將張釋之那樣試圖節刑、輕刑的司法官員視為「為犯罪者開脫」,司法者為了趨利避禍,在兩千年的演進中傾向於用越來越重的刑罰去懲治犯罪者、若犯罪者這一條命還不夠「解恨」,那就只能株連他的家屬,於是司法只能向著重刑主義的極端絕塵而去。
而張釋之在勸諫漢文帝時警告的另一件事,其實也在千年後應驗了:「如果您覺得盜竊個宗廟器物就要誅滅全族,如果以後有人偷挖長陵上的一抔土,又該如何處罰?」
「挖長陵(漢高祖墓)的一抔土」其實是造反的一個委婉說法,所以張釋之問的問題其實是:如果因為一些小罪就輕易動用重刑,那麼真正遇到大惡時,又拿什麼來進行懲罰呢?
這其實是一個重刑主義必然導致的「刑罰金屬疲勞」問題,以重刑去嚇阻某種輕罪,搞到最後大家都對重刑脫敏了,最後刑罰反而失去了其應有的威懾力。
這樣的故事在古代史上也曾一再發生,比如明代曾經是株連、保甲、戶籍制度都最嚴苛的朝代,犯罪者家屬一旦被抄沒淪入賤籍,基本上就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了。如果你的鄰里、親戚當中有人犯上作亂,除非你及時出首立大功,想不跟著吃瓜撈甚至砍頭基本也不可能。朱元璋曾對他定下的這套「剛猛治國」術非常得意。
可是到了明末我們看到,這種「剛猛」對平定和恢復社會秩序基本沒有起到任何正向效果。相反,李自成、張獻忠這些人至少在起事初期都會採用最酷烈的手段去對待明朝的官民,所過州縣屠掠無遺。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對於「流寇」們來說,既然從扯杆子造反那一刻起,就註定要被誅滅九族,那何妨把事情做的更絕一點呢?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張獻忠
於是殺人在明末淪為一種像吃飯喝水一樣大家都司空見慣的東西,最終社會從重刑主義、株連主義中除了讓人們習慣了遍及社會的普遍性殘忍,沒有收穫任何治理效果。
而重刑主義在古代中國的千年發展、延續,還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影響,那就是很多平民百姓,在長期的「熟讀歷史」當中也養成和大多數帝王一般的「帝王心術」,在他們看來,社會不夠安定、有人作奸犯科,那就是因為治的還不夠狠、殺人還不夠多。治理什麼什麼犯罪「逮住就斃」、甚至抄沒家產、讓其子孫淪為二等公民,管准就好了。

這樣的人應該會非常神往自己能穿越回古代,也能坐在把龍椅上發號施令,沒有現代社會諸多常識的掣肘,他們幻想起來一定更爽。只可惜,他們常常忘了,現實中的自己,真的穿越到了那種時代,往往更可能成為被治、被殺的平民。
所以想起來也很感嘆——你想想兩千年前的漢文帝劉恆,那是一個有帝王命、卻經常站在草根角度操一下心的、還算溫柔的人;而兩千年後的很多網民,卻明明有著韭菜的命,操著帝王的心,他們明明沒有九五之尊,卻比歷史上的秦皇漢武們更心如鐵石。
這樣的轉換,我不知是怎樣發生的。但我知道,重刑主義思想給他們造成的那種越來越拿人不當人看的影響,一定在這種千年轉換中居功至偉。
昨天《「貪二代」們再混蛋,也證明不了羅翔呼籲錯了》談到輕刑主義和重刑主義。本來我在這兩種刑罰主張之間是沒有個人偏好的。但想起了歷史,我總覺得,幾千年的重刑主義傾向搞下來了,現在我們需要一點反向的教化,以便讓很多認知錯位了太久的人,稍微清醒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