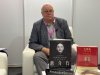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叄一年)七月至十月,第叄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63]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毀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叄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叄省匪軍著手。[64]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叄叄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叄月,長城之戰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剿匪計畫,對江西匪區,采「叄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著著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叄年(一九叄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及至二十叄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縮緊其包圍圈,而其內部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來到,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叄年,在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改革」、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岡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州里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攻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叄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成立「廣泛的抗日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略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67]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叄十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匪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68]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著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叄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69]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行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叄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政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畫,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叄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叄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布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叄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叄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叄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西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叄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布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70]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著「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著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圍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占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叄原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71]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占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