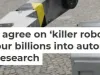圖:為了提高效率,李玉榮特意買了汽車,也要用它接送家人,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圖:李家人吃飯時,陣勢不小

圖:海參崴華商聚居的83和85號樓

圖:李玉榮把包下的房子分成小間,供越來越多的家裡人居住

圖:每天下班時間,李家人浩浩蕩蕩從市場排隊出來

圖:貨櫃市場位於海參崴市郊區,目前的生意已經大不如前
巴士和船正在將無數的中國人運往彼岸,俄羅斯人坐不住了。
一座被中國人稱作「海參崴」的俄羅斯濱海邊疆區首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人的生意已經滲透到它的各個行業,深深影響著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通過迅速擴張的生意和家族式的遷移,中國人在海參崴的人口和生意一起膨脹。
雖然在海參崴生活多年,但這座長滿了哥德式建築的俄羅斯城市對在那裡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這麼近,又那麼遠……
從中國黑龍江省綏芬河邊境口岸過關,有公路和鐵路通往俄羅斯聯邦遠東地區的每個城市。綏芬河國際客運站發往烏蘇里斯克、格城的班車20分鐘一趟,哈爾濱和牡丹江等城市每天也有多趟國際班車發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羅斯遠東的城市與中國東北城市的陸上客運頻繁,和中國內地城際客運非常相似。
於是,中國內陸省份正在進行的「春運」被複製到了俄羅斯遠東。每天,提著大包小包的中國男女填妥一張俄文的入境單,緩慢通過幾位中年發福的俄羅斯女邊防安檢官員的檢查,走過一個擺放著蘇制坦克、大炮的兵營,前方就是窄窄的公路,國際班車等在那裡,重新出發,俄遠東的荒原招手在望。
這條公路正在演繹著一場名副其實的中國版「春運」,在中方和俄方的巴士上,俄面孔的人成了「少數民族」,中國男人們操著東北腔說著笑話,巴士如同他們自己的家。烏蘇里斯克車站是一個中轉站,中國人占據了幾乎全部的站台,俄文的標牌提醒外來者,這不是在中國的縣級城鎮。
中國版「春運」同時在其他的中國通往俄羅斯腹地的道路上進行。冰封的黑龍江阻擋不了路途,那些買了180元船票的人,把一筐筐青菜、保鮮的草莓,從中國南方運到的香蕉,吃力地裝進江面上的氣墊船里。每艘搭載20-40人的氣墊船10分鐘開出一次,但滯留在海關的人並不見減少。
巴士和船正在將無數的中國人運往彼岸,俄羅斯人坐不住了,早前,俄羅斯著名的《獨立報》刊發文章《是的,我們都是亞洲人》,作者擔心幾年後在遠東的中國人將達到800萬至1000萬。俄羅斯外交部公布了一個10萬人的數字,遠東經濟研究所則評估說是20萬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羅斯聯邦濱海邊疆區的首府,中國稱之為「海參崴」,一座在許多中國人的常識中曾經屬於中國的城市。據俄官方的統計,目前,該城市有1萬中國人居住和經商。中國人的生意已經滲透到海參崴的各個行業,深深影響著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
一個家族的遠東遷移
那是前蘇聯分裂後的饑饉歲月,「修一條拉鎖要100多元人民幣。」李家的生意從一個修鞋攤裂變了。生意的裂變加速了家族人口的遷移,2000年後,李家在海參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樣膨脹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座可以看到電廠煙囪的山上,一幢老式樓房的一層,一半住著中國的留學生,一半被一個叫李玉榮的中國人承包了。
李玉榮將包下來的房間分拆轉包給在海參崴做生意的中國人,留下一些房間給自家人住。「弟弟、姐姐、堂弟幾家,還有我雇的工人,我和愛人住在這裡」,這個住處是2006年底找到的,是他在海參崴13年中搬的第20次家了。「以前,我們住在一個廢棄的廠房裡,沒有暖氣,一大家幾十口人擠在一起受凍。」他這個家最多時達到100人以上,「海參崴今年還沒有向中國人發過一張勞動許可的邀請函。」一些人返回了國內,等待著新的勞動許可證簽發。
每天早上,李玉榮和弟弟們開車把家人和僱傭的工人送往海參崴城內的各個市場,他們在那裡擁有攤位、飯店。李家擁有一個叫「榮達」的公司,「其實,公司是為來幹活的人辦身份用的,」所有的家人和工人都是榮達公司的員工,老闆是李玉榮。晚上,老闆和員工一起在幾張拼起的長條桌子上吃飯,大家又是一家人。
「這裡有一所學校,中國人叫它『九專』,我在這個學校上過學」,李玉榮33歲,細瘦的身子在樓道昏黃的燈光下拖著長長的影子。1994年春天,來自中國吉林省安圖縣鄉下的李帶著8000多元錢來到這裡學俄語,「錢是家人湊的,借的,頭年就想來,可是,把牛賣掉還是差兩千多元。」
「我在這個學校讀了三個月的俄語,其實,沒有怎麼讀書。」他真正的目的是出來掙錢,「接下來,就給黑龍江東寧縣的天平公司在這裡打了兩年工。」一個月是七八百元人民幣,一年後,他還上了從家出來時借的外債。
「我後來就出來了,跟一個同學回到綏芬河,跑到一個修鞋攤上」,「我們在那泡了一個星期,看師傅幹活就學會了。」他花了100多元買了一套修鞋修鎖的機器,重返海參崴。「我們是這個城市第6家修鞋的攤位。」他們在遠東海軍體育場的空地上拉起一塊棚布,算是圈了一塊屬於自己的攤位。修鞋的頭一個月,他賺到了1500美金。
那是前蘇聯分裂後的饑饉歲月,更換國名不久的俄羅斯成了一張白紙,市場上任何生活所需都稀缺到了極點。「修一條拉鎖要100多元人民幣。」李玉榮說,全城一個正規市場都沒有,體育場的空地誰都可以去占,「大清早起床搶地方,先到就能占好位置。」這是他追憶的一段黃金時光,空白的市場給搶先一步來到這裡的中國人得到了意想不到多的金子。
父親在兒子賺錢後來到了海參崴,接過了修鞋攤,兒子將從哈爾濱購進的貨物拿到了體育場。「利潤高得驚人,又沒有攤位費。」李家的生意從一個修鞋攤裂變了,安圖縣那個小村莊的俄羅斯遠東家族移民開始了。
這幾乎是一個被無數次複製的中國人向外遷移的模板,從吉林舒蘭四合村的波及全村的集體遷移到安圖李家的家族移民,都是以血脈關係、次之世居關係的親朋感情為基礎的,在唯血統論的俄羅斯人為多數的環境裡,他們複製了在故土上的生活圈子,在俄羅斯的土地上綻放。
2000年,李玉榮娶了只見了兩面就訂下婚事的宋吉坤,他是海參崴第一個大擺婚宴的中國人。「這年,我們在市場的攤位已經有了六個,父親建議砍掉了三個」,媽媽和新婚的妻子也留在了海參崴,「我和弟弟決定分家,最好的攤位給了弟弟。」他給弟弟留下四萬元的貨物和起家的攤位,搬到另外一個市場重立門戶。生意的裂變加速了家族人口的遷移,2000年後,李家在海參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樣膨脹。
即使分了家,在海參崴,人們還是習慣把所有和李家有親戚關係的生意看做他的。
「黑」在海參崴
「辦旅遊簽證,跟旅遊團來,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最早來到海參崴的中國人幾乎都經歷了非法勞工、非法滯留的過程。「在人多起來之後,黑幫捕手,對市場進行了管理」
一張2002年版的「財神到」年畫貼在牆上,這是一個住了4口人的房子。周俊,42歲,是他們中最早來到海參崴的人,年畫是他在5年前的春節回鄉時帶回的。帶回「財神」的那個春節後,周俊再也沒有回過黑龍江密山縣老家,雖然,家就在國界線的那邊。「回去,就過不來了。」
他沒有護照,如果他踏過國界,就很難再回到海參崴,那麼,他留在中國人叫做二道河子市場上的攤位誰來打理呢? 「2002年,我是拿商務簽證過來的,沒有勞動許可證」,那是不能在市場上從事零售業的,也就是不能站在屬於自己的攤位前招攬顧客,「移民局檢查,給我的護照蓋了黑章,乾脆,我把護照扔掉了。」他不擔心沒有護照被警察或移民局的人抓到,「抓住了交罰款就是了,如果有護照而沒有勞動大卡,那要罰得更多。」
這是一條在海參崴的中國人普遍遵守的規則,在警察和移民局檢查時,如果護照手續不全,千萬不要拿出來。「給盧布或者美金就行,如果護照被他們拿住,掏的錢更多,」周俊曾有一次付出過慘痛代價,2005年夏天,他被移民局查住,「檢查官當即要填單子,我趕緊掏出了錢。」 周花了15000盧布才得以脫身。許多中國人承認,向警察和移民局官員妥協助長了他們索要錢財的邪氣,於是有人說俄羅斯的警察腐敗是被中國人「慣」出來的。「若非如此,我們能怎樣呢?」要繼續留在這裡掙錢,又沒有合法的居留與工作手續,周俊似乎沒有選擇,他只能一次次妥協,在從二道河子市場到居所十來分鐘的路程中,一次次小心翼翼,一次次遮遮掩掩。
最早來到海參崴的中國人幾乎都經歷了非法勞工、非法滯留的過程,那是他們與當地管理部門都傷腦筋的黑暗階段。「我最早來也是辦旅遊簽證,跟旅遊團來,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李玉榮在「留學」九專時所持有的也是旅遊簽證,「後來,到市場上擺攤了,還是那樣跟旅遊團走,一個月回去一次,有時半個月就要回去一次。」回去,是指回到中方的綏芬河,在那裡,重新加入一個旅遊團,再入境進入海參崴,旅遊,是一個幌子,練攤賣貨才是正事。
持有的旅遊簽證過期是經常發生的事,很多人只能「黑」在海參崴。從吉林琿春來到海參崴開計程車的王師傅認識一個中國人,「本來是來旅遊的,到賭場去幾次後,就留在這裡不走了,一下子『黑』了七八年。」當然,這是個極端的例子。
[next]
2002年是一道分界線,之後到來的中國人逐漸齊備了合法的手續和證件,他們談起海參崴的市場,很少有人知道楊貴興、高清成,「還有我弟弟,他們三個是二道河子市場上最早的三個人」,周俊先是為做建築工人而來,他在工地上做工,當地人對那個市場有一個俄文的名字,翻譯過來的意思為「盧斯卡亞」, 「來的人多了,形成了市場」,周俊後來不做工了,他也在二道河子購買了一個攤位,「一位姓崔的中國朝鮮族人和俄羅斯人聯合,把市場管理了起來。」
海參崴的市場基本上都是這樣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現今規模最大的體育場市場也是由「黑」著的中國人烘托出的。越南人跟著來了,烏茲別克人、亞塞拜然人、塔吉克人、朝鮮人、韓國人,也相繼從陸路和海上來到海參崴,在那個看台塌陷了一半的體育場擺起了攤位。
「在人多起來之後,黑幫捕手,對市場進行了管理」,在李玉榮曾經擺過修鞋攤子的地方,已經是一排排整齊的鐵皮箱子的攤位。市場的「法律」也隨後誕生了,當然,這不是經過濱海邊疆區或海參崴市杜馬通過的「法律」,它由管理市場的黑幫制定,規定了不同位置的攤位交納的租金數目,還有每個月1000盧布不等的「保護費」。
黑幫制定的「法律」在所有的市場通行,「在此擺攤的各國人不用向海參崴的商檢、工商、稅務交納費用,只要交了錢,他們的公司全部管了。」李玉榮說,但是,「公司」對商戶收錢不限於租金,「比如,下了這場大雪,每戶都要交納800盧布的清雪費」。可是,等下一場雪下來時,上一場的積雪已經堅硬如冰。
海參崴中國印記
鞋子壞了找中國人修理,在附近的中餐館吃當地幾乎最便宜的午飯,在市場上購買價格與中國內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國人打交道,年輕人也不例外
前蘇聯解體不久就來到海參崴併入了俄羅斯國籍的薛桂林,在這個他「心目中可以居住一輩子」的城市已經生活多年。「我曾聽一位俄羅斯老大娘講起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早上醒來,能聽到中文的叫賣聲。」他踏訪過一片已經廢棄的居民區,那是1930年代中國人在海參崴的聚集地。
是的,哪怕是海參崴官方提供的資料都這麼說,中國人在當地的聚集曾經鼎盛一時。「那時,30%的海參崴居民由中國人組成。」現今,市中心保留了中國街的遺址,當地人稱為「百萬街」。
安德列·尤利耶維奇,海參崴市對外聯絡與旅遊委員會主席,手裡拿著中國和俄羅斯的小國旗,等在市政府9樓的電梯口迎接來自中國的客人,「30年前,我的媽媽告訴我,中國的商品質量是最好的。」他說,那是前蘇聯時期,家裡有幾條中國產的毛巾,總是用不壞,媽媽給了那幾條毛巾很高的褒獎。
「中國的商品,特別是食品,救了我們這座城市,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可能就完了」,安德列先生在介紹完海參崴的地理、旅遊後,動情地說,「我們應該感謝中國和中國人。」他追憶起中國人在海參崴的歷史:「小型的中國貿易很早就有了,比如20世紀早期的小餐廳,小店鋪,還有手工業作坊。」在斯維特蘭斯卡雅大街上,還有一座「綠磚屋」,那是中國商人陶則明的故居,他的工廠影響著海參崴的衣食住行。
安德列說,現在的中國商品依然影響著海參崴人日常生活:「一些家用電器,還有建築材料,全市的裝飾建材幾乎都是來自中國的。」
如果一位退休金不高的海參崴老人想增加收入,他可以把空餘的房子租給從西部邊界到來的中國人,「我們住的房子一個月要600美金。」周俊說,這要比老人的退休金多幾倍。如果這位老人的鞋子壞了,他可以去體育場市場北門,找那位叫劉維新的中國人修理,接著,他可以在附近的中餐館吃當地幾乎最便宜的午飯,隨手在市場上購買價格與中國內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甚至可以買到產自中國廣東某縣的牙籤。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國人打交道,年輕人也不例外,因為他們需要時尚而便宜的服裝,哪怕他從烏茲別克人手裡買到,但產地一定是中國。
「來這裡旅遊的中國人也很多,去年是17萬人次,他們的到來給我們的經濟帶來好處,但這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量。」安德列先生主管海參崴的旅遊,他更喜歡中國遊客湧來,「比前幾年,人數是下降的,對此,俄羅斯和中國都有問題,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政府禁止公務人員出境賭博,」他說,「海參崴的賭場是很出名的。」
安德列列舉了海參崴和中國內地城市的關係,證明和中國悠久而友好的關係,「大連,長春,煙臺,上海,延邊,都和我們是姐妹城市和友好城市關係」,他說,「我們不僅需要中國商人在這裡出售中國商品,也需要來自中國的投資,他們可以把錢投入到城市的道路建設,可以建中國城、娛樂場所,藝術工作者也可以來這裡搞繪畫,我們的城市是歡迎的。」
「瞧,我這是在中國做的西服」,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拉林先生每年要去兩三次中國大陸,「我很喜歡中國的商品。」
「也有人不喜歡中國貨,認為中國商品都是劣質的,害了他們。」康斯坦達公司經理劉鳳星的住處衛生間馬桶壞了,需要換一條管子,「樓下的老太太告訴我,一定不要用中國的。」
封閉的「中國小社會」
「中國人是單獨住的」,「中國學生和中國商人之間沒有來往,中國人之間彼此也是獨立和封閉的。」調查和研究表明,封閉的結果是,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當地時間每天下午6點,一撥一撥的中國男女從體育場市場裡走出來,這是市場打烊的時間。等大部分的商鋪拉上了卷閘門,維持秩序的保全用路障攔住了每個市場分區的通道。「到點必須走,這是規定的時間」,一位中年人邊鎖門邊說,「走晚了也不安全啊。」
一些人鑽進二手的日本車裡,那是他們在海參崴購買的便宜車輛,「自己開車相對安全多了,不用怕警察,也不用擔心搶劫。」李玉榮是每天例行著接送家人上下班的,他守時地將一輛商務車停在距離弟弟飯店不遠的路口。
一些人走到北門的有軌電車站,等候幾分鐘一趟的6路電車咣咣駛來。兩站的路程很快就到了,他們會在一幢黃色的樓房前下車,跨越軌道,上了一個緩坡,一幢雕刻著鐮刀斧頭前蘇聯共產黨徽標的樓房,巨大的阿拉伯數字顯示是85號樓。他們拐過去,進入到相鄰的83號樓里,打開長長的樓道兩側一扇扇房門,這就是他們暫居在海參崴的家。
那晚,住在83-B樓的郭良濤恰逢生日,他的朋友都趕來了,提著蛋糕、塑料瓶裝的啤酒、青菜、魚肉和雞。很快,在一個半間屋子被床占據的房間裡,幾張簡陋的桌子拼在一起,幾個男人張羅著,女人坐著聊天,嗑著瓜子。酒席轉眼準備好了,11個人舉起酒杯,祝一道從國內來又一起在市場上做生意的夥伴生日快樂。很快,一瓶瓶2升裝的俄羅斯啤酒下肚,他們喧鬧起來,聲音衝破了房門。
這是住在這幢樓里的一個中國群體,六個男人結為兄弟,老大叫余軍,一個人人都可以開他玩笑的、性情活潑的中年男人,他邊喝酒邊跳舞,「其實,我們很久沒有這樣高興了,平常也不會這麼快樂。」余軍說,「我們之間很熟,是這樓里關係最緊密的。」「那你們不出去消遣嗎?」 「很少,賣貨、進貨、回家、吃飯、睡覺、上班、下班。」
他們的歡鬧聲沒有帶來鄰居的麻煩,這幢典型的「中國樓」里,高峰時期曾有數百中國人居住,每天晚上,他們緊閉著屋門,「警察敲門也不開。」一位胖胖的女孩說。
周俊和劉景路是市場上交下的朋友,劉是瀋陽人,他的娛樂是經常到周的住處串門。周俊試圖想到外邊轉轉,但他沒有護照。李玉榮已經在海參崴生活十幾年,但放下生意後,他最好的去處還是回到家裡,跟兄弟姐妹們在一起。「說實話,這些年並沒有交下真正的俄羅斯朋友。」
「中國人是單獨住的,我們研究所曾經調查過這個問題」,拉林先生對在海參崴和遠東的中國人群體產生過興趣,「5年前,我在寫一本書,調查中國人在這裡的生活怎麼樣,同時訪問俄羅斯人怎麼看待中國人。有一個測驗,由一個基金會提供支持,是在莫斯科和海參崴同時進行的。」
拉林在一所大學授課時,問課堂上的中國留學生,是否和當地的中國商人有所交往,回答是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學生和中國商人之間沒有來往,中國人之間彼此也是獨立和封閉的。」他的調查和研究表明,封閉的結果是,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從中國來的人很多不把這塊新的土地看做家鄉,我問他們,是不是想在這裡住下來,他們的孩子想不想留下來」,拉林說,中國人的回答是,不,不會留在這裡。雖然在海參崴生活多年,但這座長滿了哥德式建築的俄羅斯城市對在那裡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這麼近,又那麼遠。
他們的道路
從綏芬河到烏蘇里斯克再到海參崴,是傳統的中國人陸路通道,也是中國貨行銷遠東的主要路途。靠著能吃苦,任勞任怨,他們忍受著孤獨,擔驚受怕,但掙回了在家鄉意想不到多的美金和盧布
巴列瓦體育場市場的電是在當地時間下午7點停的,這時,市場上全部的店鋪幾乎關張,在一個拐角的鐵皮房子裡,一些人還在忙碌著。李玉榮,他的姐姐、姐夫、弟弟,幾個幫工,在一盞小小的手電筒燈泡的照耀下,整理著貨物,塑料桶、小刀、指甲剪、玩具、拖布,等等,他們分類碼好,列在大門的兩側。「這些都叫小百,甩貨」,李玉榮指揮著大家幹活,「這個房子本來準備開理髮店的,這邊的邀請函拿不到,找好的人辦不了勞動許可證,從國內來不了。」耗費了4萬多美金做好的店遲遲不能開張,只能轉做他用。
七點半,收工了,李家人魚貫而出,市場的大門已經鎖上了,李玉榮帶頭翻上高高的鐵門,年輕人們跟上翻門而出。
「可以說,市場上的東西我幾乎都賣過」,李玉榮回首10多年的海參崴歷程,「什麼賺錢賣什麼,也被人騙過」。他為給僱傭的人和家人辦在海參崴的勞動身份,「找一個俄羅斯人幫忙,他說能弄5個名額,我給了他2500美金,可最後那人打電話說,辦不成了,錢也沒退,現在連人都找不到了,那人是一個律師。」為申請勞動名額,他又花了7000美金托人辦理,「一直都未能辦下來,移民局說外國人勞動邀請暫不辦理。」雖然,他的手裡已經拿到了莫斯科的批件,可以辦20多個人的名額。
需要的幫手過不來,李家生意損失慘重。「加上弟弟的,各項生意的損失加一起快10萬美金了」,他很著急,擔心再次像1998年金融危機時那樣,「那年盧布貶值,賠了幾千美金,又買了車,花3000多美金辦了駕照,到1998年底,身上還剩下2200美金的本錢。」
一位綏芬河的朋友在關鍵時刻幫了李玉榮,「他有一個箱子(攤位),本來可以賣1350美金的,他800美金給了我。」這個攤位就是後來留給弟弟的地方,李玉榮藉此重新起家。
在巴列瓦、盧斯卡亞、阿嘎多瓦等市場上,聚集的中國商人是海參崴中國人的主體,他們走了一條與李玉榮相似的道路。這些大部分來自中國東北鄉下的人,複製了第一撥來到此處中國人的生意模式。「貨賣完了,可以到烏蘇里斯克批發,也可以從綏芬河直接上貨」,83-B樓的老大余軍打理著檔次稍高於巴列瓦的一個鋪面,「有時要自己去拿貨,自己開車,哪怕是冬天,跑很遠的路。」
從綏芬河到烏蘇里斯克再到海參崴,是傳統的中國人陸路通道,也是中國貨行銷遠東的主要路途。
「我們就是膽子大,在國內都是沒有出路的人」,劉景路在盧斯卡亞賣建材,他認為是海參崴給了他們機會,「市場上的中國人沒幾個文化水平高的,很多都是小學沒畢業的,可我們在這裡成功了。」靠著能吃苦,任勞任怨,他們忍受著孤獨,擔驚受怕,但掙回了在家鄉意想不到多的美金和盧布。
他們在此賺錢,生活。2005年,海參崴共有24對中國新人舉行了婚禮。
中國人的俄遠東機會
一方面是觀察家分析說,莫斯科正奏響振興遠東經濟計劃的前奏,中國企業會有很多機會;一方面是「2006年只有6個中國人獲得了在濱海區的居留權」
海參崴官方提供的數據說,在濱海邊疆區,共有一萬登記的華人在此經商、做工、學習和生活。「這裡的中國人還是不夠多,而且,大都是和市場有關係的,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中國移民的需求會一天比一天高,因為,每年的中國勞務根據合同在增加。」拉林先生說, 2005年,在遠東地區,按勞動邀請來的有26000名中國人。
2006年12月中旬,俄羅斯媒體以複雜的口吻報導說,有6名濱海邊疆區的中國人加入了俄羅斯工會。當濱海區農業工會主席將會員卡發給這6位中國人時說,中國人吃苦耐勞,為豐富地方農產品市場做出了貢獻。
也是在去年底,中國駐海參崴的領事代表卻接到了一家中國企業的投訴,雖然已經辦理了中國勞務引進許可,卻無法獲得入境簽證。這與上述的景象成了衝突。
3月,濱海州和海參崴政壇發生地震,多名高官被莫斯科解職,有黑幫背景的海參崴市長尼古拉耶夫在出差莫斯科時,被安全局拘捕。尼古拉耶夫此前的身份是地方上一家規模較大公司的老闆,一本專門描述遠東黑社會現狀的書仲介紹說,他外號叫「維尼熊」,涉嫌殺人越貨,強占他人資產。
俄羅斯的觀察家分析說,對尼古拉耶夫等人下手,是莫斯科對振興遠東經濟計劃的前奏。「2012年的APEC會議將在海參崴召開,我們要建起幾座 5星級酒店,要改善交通,架大橋將俄羅斯島和大陸連接。」安德列先生說,這些僅靠中央政府承諾的40多億美金不夠的,中國企業會有很多機會。「同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我們很看重和中國的合作,比如,曾經計劃開通海參崴到中國延吉的航線,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執行,但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實施。」他透露的意思是,像這樣的合作,還可以談下去。
「2006年只有6個中國人獲得了在濱海區的居留權」,對海參崴和遠東的大開發,薛桂林認為中國獲得的機會並不樂觀,「在前蘇聯剛剛分裂時,我們失去了進入遠東地區的最佳時機。」濱海區在組建「移民事務委員會」時,薛桂林也是發起人之一,「但在這個委員會成立後,我卻不是委員」,濱海官方給他的答覆是,這裡不存在中國移民問題,也就沒有必要吸收一個中國人進來。
「中俄兩國的商務談判,總是各說各話」,薛桂林擔心中國在遠東能夠獲得的機會不會太多,「這裡沒有太大的中國企業,只有一個礦規模稍大,很多大集團來看過,但都沒談成。」
曾經幫海參崴渡過難關的中國商人也正面臨著勞動限額的困局,這些,在薛桂林看來,是中國人在遠東的機會被壓縮了。
「對這個地方,我們和你們的認識不同,中國的一些書上還寫著,這塊土地以前是中國的。」拉林說,這是雙方認識上的問題(根據我國歷史記載, 1860年沙俄強迫滿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致使包括海參崴在內的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給了俄國。1862年,沙俄政府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翻譯成漢語就是控制東方)。
而俄方在介紹海參崴的資料上說:「19世紀中葉,俄羅斯與中國簽署『北京-愛琿條約』,開始允許遷移入濱海邊疆區南部以及海參崴。當時,還不屬於任何人的濱海邊疆區覆蓋著未經開墾的森林。」
100多年後,中國人一批批來到曾「不屬於任何人」的海參崴,跨過了國界的大門,可能還要跨過俄羅斯人心理上的門檻。
深度郵箱:shenduduzh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