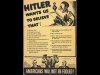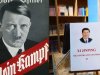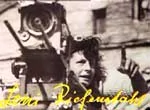
(左)《奧林匹亞》劇照/(右)萊妮·里芬斯塔爾
「女人,是不被允許犯錯誤的。」 ──萊妮·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
萊妮·里芬斯塔爾,是一個優秀的舞蹈者、出眾的演員和天才的導演。作為導演,她一生中只導演了7部影片;作為演員,她出演的影片數目大約是前面那個數字的2倍───但讓她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細細計算,她輝煌的時代加起來只有短短几個月。在這幾個月里,她創造出來的美,超過了此前一切時代電影紀錄片的總和。然而就是因為這幾個月,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因為她為希特勒拍攝的紀錄電影《意志的勝利》以及紀錄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紀錄電影《奧林匹亞》,在二戰後她連遭幾個國家數次受審,受盡牢獄之災。在世人的詛咒中,這位年過五旬的女人以照相機為伴深入非洲的黑人部落,幾本畫冊使她成為不折不扣的專業攝影師;八旬的她又對海底五彩絢麗的世界迷戀不已……。一個神話追求者,最終將她的生命編織成神話。一生酷愛運動和美的美麗女子,究竟錯在哪裡,罪在何處?
萊妮·里芬斯塔爾,1902年出生於德國一個商人家庭,起初是一個跳芭蕾舞的演員。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鐵里看到了阿諾德范克博士導演的《命運山峰》海報,電影鏡頭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種異常的美,她在這種美里沉醉了。不久,她向范克毛遂自薦,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後,萊妮雷芬斯塔爾已經成為德國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經執導過《藍天使》的馮施登堡甚至說:「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個瑪琳黛德麗。」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黨上台了,萊妮雷芬斯塔爾的命運要改寫了。
1932年,萊妮·里芬斯塔爾在德國電影前輩的指導下,導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藍光》。次年她為納粹黨大會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這部影片的拷貝從未問世,但萊妮·里芬斯塔爾在拍攝紀錄片方面的天才卻已嶄露頭角。於是在1934年,當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紐倫堡舉行閱兵典禮時,32歲的萊妮·里芬斯塔爾被選中,擔任全部紀錄電影的拍攝工作。
納粹黨為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會為之咋舌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製組,36架以上的攝影機同時開工,包括16個攝影師,每個攝影師配備一個助手,再加上無數的聚光燈隨時聽候調遣──希特勒投下這麼多的馬克,為的就是要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萊妮·里芬斯塔爾做到了這一點。 這部紀錄片後來被命名為《意志的勝利》。《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意味。它以希特勒的專機從茫茫大霧中顯現為開端,充滿了遊行、集會、震耳欲聾的吶喊以及如林的舉手禮,最後在華格納恢宏的史詩音樂里告終。 無與倫比的拍攝條件讓瑞芬舒丹首創了電影史上的很多攝影技巧;在大場面的把握上,至今沒有一個導演可以超越她。這部影片後來獲得納粹國家獎,威尼斯電影展金獎和巴黎電影節法國政府大獎等一系列獎項,成為紀錄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萊妮·里芬斯塔爾在影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表現手法,在希特勒驅車檢閱遊行隊伍的場景中,她打破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完整構圖原則,希特勒的頭部在畫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這樣就使他的背影占據了整個畫面的一大半,而遊行隊伍則變得相對渺小,而且仿佛是從希特勒舉起的手臂下面魚貫而過。
雖然全片只有一個半小時,連一句解說詞都沒有,可是主題思想極其鮮明和通俗易懂,有很強的衝擊力,至今有些反法西斯的青年在看的那一瞬間還會受它的感染。其中有一個鏡頭就是攝影機仰拍前推大樓前掛著的一列長條萬字旗,推到最後一面旗的時候,攝影機同時下搖,搖到旗子完,正好是希特勒的座車處於中景,向前開過來。意思表達得很清楚,而且觀眾感到意外,感到震動。另外一個是最後的紐倫堡大會。鏡頭從大俯拍始,希特勒一行從畫框底邊入畫,他們向前(即縱深),攝影機慢慢抬起頭來。最後攝影機搖在希特勒一行的前面,抬頭,講台正中一面大萬字旗。
曾經有人評價《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記》中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度過紅海,前往流淌著蜜與奶的地方。
此後的幾年裡,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在未來的10年之內,這個蓄著小鬍子的人將指揮他們前往世界各地,然後死在北非,死在諾曼第,死在史達林格勒。
|
   (左)《意志的勝利》DVD封面/(中)意志的勝利劇照/(右)柏林奧運會會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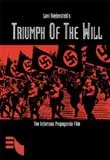  《意志的勝利》DVD封面 《奧林匹亞》成了體育紀錄片的聖經 無論萊妮·里芬斯塔爾願意與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為是納粹黨最有力量的宣傳機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託為奧運會拍攝紀錄片。這部後來被命名為《奧林匹亞》的紀錄片,幾乎成了所有體育紀錄片的聖經。里芬斯塔爾在其中創造的許多拍攝技法被無數後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機位拍攝跳遠運動等。 與此同時,這部影片在畫面審美方面同樣達到了極致,影片開頭的古希臘奧運會賽場廢墟,讓人感覺每一塊石頭都具有著驚人的美;繼而,幾個裸體男女手持各種運動器械的鏡頭和「擲鐵餅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現。戈培爾把這組鏡頭闡釋為「優等種族」理論的圖解,但是它所紀錄的人體之美和儀式之美,又的確讓以後的電影人嘆為觀止。 1938年4月20日,《奧林匹亞》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歲生日。她的這份輝煌禮物後來在電影史上得過4個大獎,但同時也永遠地成了她的污點,因為在當時和現在的眾多影評人看來,她「把奧運會轉化成了法西斯儀式,旁白中不斷出現的『戰鬥』、『勝利』字眼,都透露了創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但這已經是戰爭的前夜了。1938年,里芬斯塔爾出訪美國,為她的《奧林匹亞》進行宣傳,但是好萊塢卻給了她這樣的歡迎詞:「萊妮,滾回家去!」───製片商們都不敢見她,怕從此影響公司的聲譽。最後她竭盡所能主持了一場《奧林匹亞》的非公開放映,好萊塢不少圈內人在黑暗中偷偷溜進影院。 美國評論界畢竟無法忽視《奧林匹亞》的成就,《洛杉機時報》曾這樣評論道:「這部影片是攝影機的勝利,是銀幕的史詩。」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一年後,戰爭爆發了。整個戰爭期間,里芬斯塔爾匪夷所思地沒有參與任何納粹宣傳片的拍攝───或許她此時已經刻意地與希特勒拉開距離。 40年代初,她拍攝了自己最後一部故事片《蒂芬蘭》,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後的罪狀。因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普賽人,戰後再沒有人相信她關於自己對種族滅絕計劃一無所知的辯解。 希特勒垮台之後,里芬斯塔爾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電影人之一,並被定名為「納粹同情人」,幾次遭到逮捕(期間她成功地越過一次獄)。她被指控為第三帝國神話最潛在的製造者,大肆頌揚納粹帝國的超人概念,卻視而不見納粹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1949年,她終於結束了牢獄生活,但是輿論和評論界的牢獄更迅速而紮實地圍困了她,而且她作為導演的生涯隨著帝國的覆滅也永遠結束了。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裡她再沒有執導或演出過任何影片。在各種文獻記載中,她被說成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後的里芬斯塔爾曾經前往非洲大陸,出版過一本有關土著生活的攝影集,72歲時她又開始學習潛水和海洋攝影───熱帶魚和珊瑚,也許它們畢竟不像人類那樣危險吧?然而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過她。 1997年,德國漢堡舉行了一次「里芬斯塔爾劇照和攝影展」,立即有抗議者打出了「納粹展覽!」、「不許兜售法西斯美學!」的標語。為此,里芬斯塔爾憤怒地說:「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在一次接受《泰晤士報》的採訪中,里芬斯塔爾感嘆地說:「歲月不饒人,我現在健康狀況很成問題,特別是我的脊柱總是疼得要命,要吃許多止痛片才稍微緩解。」 但當記者問到,二戰結束後因為和納粹的牽連而被迫終止她熱愛的電影事業,她是否感到不公平的時候,她顯得有些激動:「對,我100%地覺得不公平。在納粹時期拍的那些電影都是『藝術』,我不應該為過去做的那些事情遭到這麼多譴責。」她稱自己不關心政治,感興趣的只有藝術。但國際社會的共識是:她那些刻意漠視道德的作品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 里芬斯塔爾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曾經給了她巨大榮譽然後又將她唾棄的人群中間。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當年曾經同樣為納粹充當宣傳工具的許多藝術大師們,包括羅貝爾多-羅西里尼,薩爾瓦多達利,馮卡拉揚都在戰後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而且名聲依舊顯赫。《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在經過長時間的禁止後,重新發行了DVD並在電視上公映。 她在這兩部紀錄片中創始的技法,被無數後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覆模仿著。史蒂芬史匹柏和喬治盧卡斯都曾公開地向她表示過同行的敬意。在這個意識形態對立逐漸淡化的時代里,人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很多教授電影的學院教授們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他們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我的學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 好萊塢著名導演和演員朱迪·福斯特,一直對萊妮·里芬斯塔爾——這位備受爭議的電影導演的成就佩服得五體投地,早就計劃著將她的故事搬上銀幕。不料朱迪·福斯特的這一構想卻「激起爭議無數」。當這個消息被披露以後,「猶太保衛聯盟」組織在派拉蒙電影公司的大門外高舉著標語牌示威抗議,標語牌上寫著「朱迪·福斯特想對納粹分子致意!」「停止朱迪的拍片計劃!」 面對種種非議,朱迪·福斯特自有說法。她說,「我希望人們相信我是個是非道德觀念很強的人,完全有能力掌握分寸,這部電影絕對不會對里芬斯塔爾的非常人生加以美化或者醜化。」 「想想看,如果我打算拍一部關於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的電影,他們恐怕就沒這麼多意見了——瑞芬舒丹讓很多人惱火的原因很簡單,第一她是個女人,第二她從不曾為自己所做的事情道歉!」 然而這一切對於里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歷了60年的流放之後,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於藝術而屬於上帝。一種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為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里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 「那是因為《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里芬斯塔爾的故事為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與非美,罪與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價?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氣和色彩?對於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
Leni Riefenstahl - scene from "Triumph of The 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