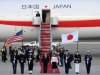日本水俁病確認五十周年之際,母親帶著孩子悼念當年逝者。
一位日本母女用2000個廢鐵罐做成燭台,呼籲身邊人保護環境
日本鄉間街頭的垃圾收集點,垃圾被嚴格分類,以利於焚燒或回收利用。 (南方周末記者 何海寧/圖)
在新江東焚燒廠,透過玻璃,可以看到焚燒廠各個工序幾乎所有的運轉信息。
記者赴日深度調查:他們為何比中國更「乾淨」?
中國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專題)「失去的十年」,今年8月,終於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國的經濟總量首次超越日本(專題),位列世界第二。在綠色浪潮來襲的今天和未來,我們究竟超越了日本(專題)什麼,又落後了日本什麼
日本社會環保意識得以固化並傳承,這得益於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業污染的教訓,得益於不斷完善的法律,得益於日本人習慣於遵守規則的國民性格,這使得整個社會如同工業流水線一般程序化運作。
日本遺憾,中國警醒,但數字上的高下,並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實。
南方周末記者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會,遍訪各界,還原真實的中日差異。「超日之思」專題將以上下兩輯的篇幅,超越數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環保、低碳等綠色領域的成敗利弊,以資後來居上者中國借鑑。
日本水俁病確認五十周年之際,母親帶著孩子悼念當年逝者。
東戶山小學的環保烹飪課
在四十餘雙眼睛的注視下,65歲的村井安成老師要在學生們面前變「魔術」----他要把烹飪台上的苦瓜變成一個個「甜甜圈」。
苦瓜是這些四年級小學生們春天種下的,如今到了收穫的季節。苦瓜生長時,7名小學生還利用垂下的藤條,製作「綠色窗簾」,在教學樓外面遮擋陽光,降低室溫。環保烹飪課前,這些小學生站在講台上,舉著室內外溫差記錄表,講述他們的成功實驗。
這是位於東京新宿區東戶山小學綜合學習時間的一項內容,幫助學生親近大自然。綜合學習時間是日本中小學環境教育的重要載體,每周兩小時,讓小學生自行選擇喜歡的調查內容。
「有30%多的學生選擇環保。」位於東京的環境保護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說。
與中國環境教育注重科學知識不同的是,日本的環境教育更傾向於「體驗」。這種環境教育有很強的實踐性。為此,有的學校在校園裡開闢一塊田地,學生們種植水稻;有的則帶領學生到垃圾處理廠參觀廢品回收發電的過程。「這樣,小孩子長大之後就不會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說。
東戶山小學校長國分重隆在記者面前攤開一份詳細的課程安排計劃,每個科目都有環保內容。「最難融入的是數學。」他說。即便如此,老師也設法讓學生在校園裡各自找一棵樹,自己計算樹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與記者談話間,他便接到一個環保組織的電話,向他推薦在工業課、農業課里融入環境教育的活動。
現在,文部省(相當於中國教育部)每年都會制定環境教育大綱,各個地區的教育機構進一步細化,到了國分重隆手裡就是詳細列舉每個科目、年級和學期的具體活動表。
「日本人對環保的要求已經根深蒂固了。」國分重隆指著手裡的文部省的「環境教育指導資料(小學校編)」感嘆道。
那一場日本教育大辯論
當了40年教師的村井安成如今在東京都新宿區立環境學習信息中心工作。這所民間組織類似於環境教育的仲介機構,負責登錄環保組織信息,然後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區各個學校推薦。
村井安成的辦公室色彩斑斕,擺置著許多小學生作品,有環保小屋的模型、昆蟲標本,還有一個太陽能收集器。一塊展板上貼滿學生日記,其中一張記著:「今天在電車上,我看到有人穿長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裝。這在夏天是很不合適的,浪費空調。」
這所信息中心隸屬於新宿區政府的環保部門,通過招投標合作,每年獲得政府一千多萬日元的活動經費。在全日本,這類非盈利組織有數千所。
環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這源於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場大辯論:日本教育缺乏什麼?爭論的最終答案是,日本學生記憶很拿手,但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從各個科目中削減了上課時間,增加了綜合學習時間。這恰恰給起步的環境教育提供了載體。
1980年代中後期,日本正經歷著著名的經濟泡沫時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場盛行投機熱潮。「所有人都覺得做什麼都能成功,房貸利息6%都覺得能還,現在2%都不敢買房子。」38歲的東京婦女早川美妙子說。
如今司空見慣的企業環保廣告,當時幾乎沒有。一名東京市民唯一記得的是一家地鐵公司做的環保廣告,它將塑料瓶變成纖維,製成員工制服。
經濟崩盤之後,日本開始反思。這意味著國民意識的轉變,教師、學者開始專注於環境教育。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環境教育論壇成立。這個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性論壇前身是清里論壇。1987年,在距離東京市區約2個小時車程的小鎮清里召開了第一屆環境教育論壇,這成為全國各地教師、學者交流的平台。
一位日本母女用2000個廢鐵罐做成燭台,呼籲身邊人保護環境
日本環保啟蒙運動
9月15日,學習院大學教授走訪哲郎從書架上抽出兩本教科書,其中一本是幾年前的小學課本,上面沒有現在熱門的低碳、地球環保知識,而是講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業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發於1960年代,這是日本環境污染時代的標誌。
1970年代,公害病的醫學認定工作持續多年,受害居民和企業激烈對抗。雖然四大公害只發生在日本偏遠地區,但抗議活動和隨後曠日持久的訴訟震撼了整個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時代正好是水俁病訴訟激烈的時候。當時他的課本並沒有相關環保內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會癢。」
10年之後,當法律認定企業責任之時,村井安成從學生變成教師,課本上也開始出現了公害教育。
在這期間,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國民性使得自然保護教育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特別在都市圈快速發展期間,普通市民更加渴望親近自然。一種「自然學校」的民間組織、企業開始為這種需求提供服務。
如今,「自然學校」被賦予了環保理念,有解說者專門進行環保宣傳。「七八年前,自然學校有兩千多所,現在有四千多所了。這意味著家庭與自然接觸的意願在增加。」走訪哲郎說。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對於日本人的環保意識,染野憲治更願意相信是環保法律確立所致。這名東京財團政策研究員原來在日本環境省(相當於中國環保部)就職,參與水俁病賠償工作。他拿出一張帶有坐標系的講解稿,縱坐標是時間,橫坐標代表從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變。時間越靠近現在,帶有鼓勵、促進性質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從1967年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項環保法律經歷了政府、民間力量和企業之間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類環保法令和產業標準都比較完備,連保鮮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屬鋸條,都有企業更換為更加有利於垃圾分類的代替品。最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類,種類區分在各地不盡相同,但每個地方至少能看到5個並列擺放的垃圾桶。這已具體到了每一個飲料瓶上。製造商要標明可回收標誌,瓶蓋、瓶身、包裝紙分為3類垃圾分別回收。為方便消費者撕下包裝紙,生產商還特別製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開始有規範,企業也開始遵守,人們才慢慢了解環保。」村井安成說。
環保正成為企業促進消費的招數。屋頂綠化成為潮流,就有商家開始廣告推薦大象糞便是絕好的肥料。有人在看電視時會走開或者不知不覺打瞌睡,就有生產商開發了可以感應觀眾是否在場,或者是否睜眼的電視機,就算閉眼睡覺了,電視機都會自動關閉。
「企業是給了我們很好的正面影響。」家住東京高尚住宅區的園山京子說,「比如買冰箱、空調,就會注意不含氟氯烷。」
「環保意識現在是一種fashion(潮流)。」愛知大學教授大澤正治說,大概5年前,他在歐洲看到環保袋時,就感覺這將會風行日本。如今,這果真已是年輕人喜歡的一種「潮品」。
矛盾的環保社會
早川美妙子家裡有10個環保袋,幾乎每買一宗商品都會送一個,這成了浪費的環保品。「商店裡也賣環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變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細觀察日本人的環保意識,會令人心生矛盾。無論誰踏足這裡,都會讚嘆它乾淨的街道、精細的垃圾分類。不過,當入夜時,看到滿街密如叢林的霓虹燈整夜通明,商店裡精美包裝的商品,又會糾結於這個消費社會的奢侈浪費。
許多垃圾桶放在飲料自動販賣機旁邊,與數十種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裝容器回收法」,認為塑料瓶的回收技術已成熟,允許企業生產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回收。」廣瀨稔也說,「這是站在企業發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廣瀨稔也住在橫濱市,家裡垃圾分為8類,牛奶紙盒必須剪開、洗淨、攤平,才能送去回收點。這個過程要用水電,他與一些家庭婦女一樣迷惑,這到底是環保還是浪費?
馬桶是另一個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馬桶水箱的進水口是水龍頭,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環用於沖洗馬桶。它同時有舒適的額外設置,方便之後有噴水口沖洗肛門,馬桶圈會常年通電發熱,保證如廁人士裸露的屁股不著涼。這顯然有些不環保,於是,有商家生產了感應發熱的馬桶,避免無人時的「浪費」。
許多餐廳提供免洗筷、餐巾紙。如果發給顧客4張餐巾紙,只用了1張,但是最後清理時,嚴謹的日本餐廳會扔掉所有餐巾紙。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環保,這並不是為了減少消費。」染野憲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說道。
走訪哲郎有時會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學三年級測試上,有30%的大學生不會把英語的「生物多樣化」、「全球變暖」翻譯成日文,在小學學習過的蜻蜓、蒼蠅幼蟲,也有很多人不認識。「日本的環保意識整體是很高的,但兩極分化很嚴重。現在有一些『宅族』,只關心自己的事情,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
「像我們這個年紀,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較年輕人,他們接受了系統的環境教育,應該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廣闊的視野。」村井安成說。
垃圾焚燒大國日本,正成為中國各地政府面對垃圾圍城難題時,競相取經的對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對策的權威學者卻高呼,「千萬別學日本!」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應該學習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開,尊重民意,權責界定,應該摒棄的是,一燒了之的依賴路徑。
日本鄉間街頭的垃圾收集點,垃圾被嚴格分類,以利於焚燒或回收利用。 (南方周末記者 何海寧/圖)
日本是個名副其實的焚燒國度,至今仍擁有超過1400座垃圾焚燒爐,作為世界上最早應用垃圾焚燒技術的國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進焚燒爐,這一數據在世界遙遙領先。
然而,專門研究廢棄物處理的名古屋大學岡山朋子博士卻對來訪的中國人提出了忠告:千萬別學日本!
在她看來,中國和韓國民間源於對二惡英恐慌而發生的反垃圾焚燒浪潮,在日本並未出現過,因為當二惡英問題被發現時,日本的垃圾焚燒廠早已遍布全國,「日本的焚燒歷史太久了,發展經歷也太特殊了。」
透過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麼辦。」
本橋勝照是東京新江東垃圾焚燒廠(下文簡稱新江東)管理課事務系的系長(類似於中國的科長或小組長),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參觀。
在日本,到焚燒廠參觀是每個小學生的必修課,而作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燒廠,新東江總是參觀的首選。這座位於東京灣沿岸的建築,單從外觀上看,很難相信竟是一座日處理垃圾1800噸的焚燒廠。隔壁的訓練場上,東京都警察機動隊正在集訓,廠區周圍既沒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見路面被污損的痕跡。
焚燒廠的一樓大廳,是一個專門用於介紹廠區概況的報告廳,這個報告廳耗資近億日元(約800萬元人民幣)之巨,每個座位前都設置了投票器,小學生來訪時可以通過大屏幕進行智力問答,優勝者還會有獎品。為了吸引孩子們的興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採用了卡通造型。
本橋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記著參觀預約,其中不乏中國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預約中已有三個中國的團體,分別是中日友好協會、專家學者考察團和安徽省一正籌建垃圾焚燒廠的地方政府。「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麼辦。」本橋笑著說。他的回答總是很簡單:信息公開。
參觀者順著樓上的長廊,按照垃圾焚燒的工序流程參觀。在每一道工序車間上面,參觀者透過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車間裡的一舉一動,在玻璃旁,還會有一個電子顯示屏顯示車間內的基本數據。
在東京灣填埋場附近,排列著包括新江東在內的六個垃圾焚燒廠,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節省運輸成本,另外的原因則在於東京灣是相對人口稀少的地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市民們都不願意焚燒廠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東每年的運轉費用是800億日元(約64億人民幣),其中的450億日元來源於政府稅金,而另外的350億日元則是針對企事業單位收取的垃圾處理費用。
「我們的生存狀況挺好,」本橋說,「任何有興趣的市民,都可以來監督我們的財務狀況。」市民們亦很少擔心焚燒廠弄虛作假,因為廠方的定期報告比市民監督更為嚴格。
不久前,東京都的21家焚燒廠中的4家排煙檢測器,測出氣化水銀濃度超標,儘管這個濃度並不會給環境帶來多麼惡劣的影響,但焚燒廠還是主動停止了運轉,並第一時間向所在地區的居民通報。「通報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面是焚燒廠有信息公開的義務,同時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業單位要遵守垃圾分類。」本橋說,「之所以水銀超標,是因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隻狡猾的狐狸」
「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鬥爭,最後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了。」
事實上,焚燒廠並不是天生就願意敞開懷抱,這是日本市民幾十年鬥爭來的結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焚燒廠在日本,也曾遭遇過強烈的反對,但不是因為二惡英,當時的科學家尚未發現,那時的民意主要出於一種狹隘的心理:焚燒廠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邊。
東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燒廠是另一個中共政府官員們的熱衷參觀地,因為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區內的焚燒廠,或許可以幫助回答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遭遇民眾反對該怎麼辦?
還有一年就結束任期的後藤市長,希望在他離任前解決選址問題,然而他親自挑選的一處地方,卻被市民代表們在市民會議上強烈反對。
無計可施的後藤市長向做垃圾處理諮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騎著自行車將武藏野市走了個遍,發現「想找到一片遠離居民區的合適空地根本沒有可能」,所以,「我建議市長還不如把這個燙手的山芋直接丟給市民,直接讓市民來參與選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樂道的經驗就是,從一開始便確定了遊戲規則。為了保證市民參與有章可循,首先確立了選址預備會規則,內容包括:由專家和市民代表組成的環境委員會推薦人員參加選址預備會,每個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如果一年內選不出地址,則意味著市民沒有做出選擇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長的選址。市民們表示同意。
「一開始就確立了遊戲規則,而且是公開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無論這個地址選在哪,最終都必須在一年內有個結果。」八太昭道說,「換句話說,市長不用擔心焚燒廠的地址沒有著落了。」
經過選址預備會的投票篩選,四個地方被列入候選,其中包括市長最初的選址方案。
隨後,選址進入到第二階段,由專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這四個候選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組成了「建設特別市民委員會」,再做定奪,這是31年前的1979年。
後藤市長最初選定的那個地區的代表,為了防止被選上,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代表們做了一個焚燒廠和社區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燒廠建成以後,當地的小學會怎樣、小區會怎樣,還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走遍了日本的焚燒廠,去搜集問題,他們用實際行動樹立了市民參與的榜樣。最終的結果果然不是市長的最初方案,而被選中的地區的代表們非常懊惱,曾一度提出過退場,但因為有約在先,他們最終選擇了尊重規則。
後藤市長的難題果然在一年內解決了,新的垃圾焚燒廠也在1984年順利完工。
三十多年後,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讓市民參與,其實並沒有消除反對者的聲音,而是把反對者的聲音納入到了一個合法的程序中,「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鬥爭,最後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了,而我就是那隻狡猾的狐狸。」
在新江東焚燒廠,透過玻璃,可以看到焚燒廠各個工序幾乎所有的運轉信息。
自掃門前雪,解放「東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
如果說武藏野市的經驗解決了民意反對的難題,那麼,地方政府間如何明確垃圾處理責任則是另一個重要話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東京都的垃圾處理都是由都政府來全權負責,隨著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漸覺力不從心。改變源自一場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後,東京的垃圾大多被運往靠近東京灣的江東區填埋處理,隨著填埋衍生的污染和衛生問題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場越來越難堪重負,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提出「在城市夾縫中建造垃圾焚燒爐」的主張。
當時的東京都政府要求下轄各個區都需要建設自己的焚燒設施,「各家自掃門前雪」,儘管將垃圾推進焚燒爐在當時是日本社會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識,但這一主張還是遭遇了阻力,引發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垃圾戰爭」。
其中,最強烈的反對聲來自高級住宅密集的杉並區,他們認為處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責任,跟杉並區無關。
憤怒的江東區居民則堅決反對杉並區的垃圾運進本區的填埋場,喊出了「杉並區的垃圾滾出去」的口號。堅持要在杉並區建焚燒廠的都政府,最終被杉並區居民告上了法庭。訴訟最終以和解而告終,居民最終同意在區內建設焚燒廠。
這場官司促使東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轄各區在垃圾處理上的職責問題。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說,「這(杉並區事件)是一個轉折。」
1996年,東京都政府正式通過法規,明確垃圾處理原則上是各市町村的責任。
而東京都23個區的區長們則成立了一個自治單位,即所謂的區長聯席會議,下設一個專門的垃圾處理機構,即東京二十三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東京都政府將分管的垃圾焚燒廠全部移交給了對方。
十幾年來,東京23區的垃圾處理已在一個責任明確的體系中穩定運轉,各司其責:23個區各自負責自己的垃圾收集、搬運與資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 21座垃圾焚燒廠,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則送到相應的處理中心。最終的焚燒灰渣等被運送到填埋場,而填埋場則是由東京都政府負責,「東京都政府終於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動
「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並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燒國度,也從不缺堅定的反建派,近幾年尤甚。年過七旬的廣瀨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會議(NPO組織)會長,便是一名旗幟鮮明的垃圾焚燒反對者。
在廣瀨看來,占到垃圾總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裡直接用廚房垃圾處理機來處理,最終變成肥料。
廣瀨對垃圾焚燒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並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現在的處理辦法就是把收集裝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險源始終存在。或許有一天地震了,也將是危險。」
隨著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燒廠的使用壽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燒廠均面臨重建的問題,而類似於廣瀨先生這樣的新興反建派並非少數。「不誇張地說,現在又是一個新的反建潮。」廣瀨說。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德島縣上勝町。這裡僅有2200人口,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了40%,高達34種垃圾分類的要求近乎變態,每個家庭均配發了廚房垃圾處理機,在居民們的努力下,帶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經實現了資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燒廠無疑顯得多餘。
但是,名古屋大學的岡山朋子博士研究發現,各家堆肥化處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難行,「像東京這種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無處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葉縣這樣可以應用肥料的地方,從法律上來看又是不允許的,因為法律規定,垃圾處理必須在自治體內解決。」
岡山朋子一度建議,不要對落後的焚燒廠進行升級改造,而是將其變成集中堆肥化處理的工廠,但這並不比建焚燒廠更容易獲得支持。她曾對名古屋和韓國做過民意支持的比較研究,結果令她很意外,對肥料轉化廠的支持度,韓國超過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對於焚燒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會認為堆肥有味道,而中國人和韓國人則擔心焚燒會產生危害健康的二惡英問題。」她總結說。
一燒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
岡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來取經的中國人,「千萬別學日本!」
「日本焚燒垃圾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的政策,都是為垃圾焚燒服務的。」而垃圾的出路更應該在源頭減量和循環利用。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垃圾處理正呈現著一個看似矛盾的圖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燒技術的日益精進,對垃圾焚燒的依賴感與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絕垃圾焚燒的呼聲從未間斷。
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環境省對於任何致力於3R(reduce,reuse,recycle)運動的嘗試都是支持的,但具體哪個地方應該實行怎樣的垃圾處理方式,應該由當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討決定。在他看來,選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主導方式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
而廣瀨先生擔心的是:現在的垃圾焚燒技術越來越發達,什麼都能燒了,會讓政府和市民們覺得,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他的擔心終於變成了事實。
塑料最早被劃分為不可燃垃圾,是因為1973年東京都在焚燒塑料的焚燒廠的廢水中檢測出重金屬超標。而如今,焚燒技術的進步似乎為將塑料推進焚燒爐提供了安全保證,而節約填埋空間、延長填埋場壽命更是理據十足。廣瀨先生則堅信另外的邏輯,焚燒爐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許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進入一個焚燒爐改造期。而焚燒爐企業表現出的強大的遊說和公關能力,令廣瀨先生心有餘悸,「我擔心改建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會加大日本對於焚燒爐的依賴。」
環境省的官員對上述擔憂的反應則明顯樂觀:「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類意識已經很高了。焚燒是建立在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顯然,這與岡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結論相左,在她看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處理的政策,無不是以垃圾焚燒為中心的,而最終也會受制於垃圾焚燒。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
中國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專題)「失去的十年」,今年8月,終於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國的經濟總量首次超越日本(專題),位列世界第二。在綠色浪潮來襲的今天和未來,我們究竟超越了日本(專題)什麼,又落後了日本什麼
日本社會環保意識得以固化並傳承,這得益於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業污染的教訓,得益於不斷完善的法律,得益於日本人習慣於遵守規則的國民性格,這使得整個社會如同工業流水線一般程序化運作。
日本遺憾,中國警醒,但數字上的高下,並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實。
南方周末記者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會,遍訪各界,還原真實的中日差異。「超日之思」專題將以上下兩輯的篇幅,超越數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環保、低碳等綠色領域的成敗利弊,以資後來居上者中國借鑑。
日本水俁病確認五十周年之際,母親帶著孩子悼念當年逝者。
東戶山小學的環保烹飪課
在四十餘雙眼睛的注視下,65歲的村井安成老師要在學生們面前變「魔術」----他要把烹飪台上的苦瓜變成一個個「甜甜圈」。
苦瓜是這些四年級小學生們春天種下的,如今到了收穫的季節。苦瓜生長時,7名小學生還利用垂下的藤條,製作「綠色窗簾」,在教學樓外面遮擋陽光,降低室溫。環保烹飪課前,這些小學生站在講台上,舉著室內外溫差記錄表,講述他們的成功實驗。
這是位於東京新宿區東戶山小學綜合學習時間的一項內容,幫助學生親近大自然。綜合學習時間是日本中小學環境教育的重要載體,每周兩小時,讓小學生自行選擇喜歡的調查內容。
「有30%多的學生選擇環保。」位於東京的環境保護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說。
與中國環境教育注重科學知識不同的是,日本的環境教育更傾向於「體驗」。這種環境教育有很強的實踐性。為此,有的學校在校園裡開闢一塊田地,學生們種植水稻;有的則帶領學生到垃圾處理廠參觀廢品回收發電的過程。「這樣,小孩子長大之後就不會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說。
東戶山小學校長國分重隆在記者面前攤開一份詳細的課程安排計劃,每個科目都有環保內容。「最難融入的是數學。」他說。即便如此,老師也設法讓學生在校園裡各自找一棵樹,自己計算樹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與記者談話間,他便接到一個環保組織的電話,向他推薦在工業課、農業課里融入環境教育的活動。
現在,文部省(相當於中國教育部)每年都會制定環境教育大綱,各個地區的教育機構進一步細化,到了國分重隆手裡就是詳細列舉每個科目、年級和學期的具體活動表。
「日本人對環保的要求已經根深蒂固了。」國分重隆指著手裡的文部省的「環境教育指導資料(小學校編)」感嘆道。
那一場日本教育大辯論
當了40年教師的村井安成如今在東京都新宿區立環境學習信息中心工作。這所民間組織類似於環境教育的仲介機構,負責登錄環保組織信息,然後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區各個學校推薦。
村井安成的辦公室色彩斑斕,擺置著許多小學生作品,有環保小屋的模型、昆蟲標本,還有一個太陽能收集器。一塊展板上貼滿學生日記,其中一張記著:「今天在電車上,我看到有人穿長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裝。這在夏天是很不合適的,浪費空調。」
這所信息中心隸屬於新宿區政府的環保部門,通過招投標合作,每年獲得政府一千多萬日元的活動經費。在全日本,這類非盈利組織有數千所。
環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這源於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場大辯論:日本教育缺乏什麼?爭論的最終答案是,日本學生記憶很拿手,但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從各個科目中削減了上課時間,增加了綜合學習時間。這恰恰給起步的環境教育提供了載體。
1980年代中後期,日本正經歷著著名的經濟泡沫時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場盛行投機熱潮。「所有人都覺得做什麼都能成功,房貸利息6%都覺得能還,現在2%都不敢買房子。」38歲的東京婦女早川美妙子說。
如今司空見慣的企業環保廣告,當時幾乎沒有。一名東京市民唯一記得的是一家地鐵公司做的環保廣告,它將塑料瓶變成纖維,製成員工制服。
經濟崩盤之後,日本開始反思。這意味著國民意識的轉變,教師、學者開始專注於環境教育。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環境教育論壇成立。這個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性論壇前身是清里論壇。1987年,在距離東京市區約2個小時車程的小鎮清里召開了第一屆環境教育論壇,這成為全國各地教師、學者交流的平台。
一位日本母女用2000個廢鐵罐做成燭台,呼籲身邊人保護環境
日本環保啟蒙運動
9月15日,學習院大學教授走訪哲郎從書架上抽出兩本教科書,其中一本是幾年前的小學課本,上面沒有現在熱門的低碳、地球環保知識,而是講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業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發於1960年代,這是日本環境污染時代的標誌。
1970年代,公害病的醫學認定工作持續多年,受害居民和企業激烈對抗。雖然四大公害只發生在日本偏遠地區,但抗議活動和隨後曠日持久的訴訟震撼了整個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時代正好是水俁病訴訟激烈的時候。當時他的課本並沒有相關環保內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會癢。」
10年之後,當法律認定企業責任之時,村井安成從學生變成教師,課本上也開始出現了公害教育。
在這期間,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國民性使得自然保護教育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特別在都市圈快速發展期間,普通市民更加渴望親近自然。一種「自然學校」的民間組織、企業開始為這種需求提供服務。
如今,「自然學校」被賦予了環保理念,有解說者專門進行環保宣傳。「七八年前,自然學校有兩千多所,現在有四千多所了。這意味著家庭與自然接觸的意願在增加。」走訪哲郎說。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對於日本人的環保意識,染野憲治更願意相信是環保法律確立所致。這名東京財團政策研究員原來在日本環境省(相當於中國環保部)就職,參與水俁病賠償工作。他拿出一張帶有坐標系的講解稿,縱坐標是時間,橫坐標代表從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變。時間越靠近現在,帶有鼓勵、促進性質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從1967年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項環保法律經歷了政府、民間力量和企業之間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類環保法令和產業標準都比較完備,連保鮮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屬鋸條,都有企業更換為更加有利於垃圾分類的代替品。最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類,種類區分在各地不盡相同,但每個地方至少能看到5個並列擺放的垃圾桶。這已具體到了每一個飲料瓶上。製造商要標明可回收標誌,瓶蓋、瓶身、包裝紙分為3類垃圾分別回收。為方便消費者撕下包裝紙,生產商還特別製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開始有規範,企業也開始遵守,人們才慢慢了解環保。」村井安成說。
環保正成為企業促進消費的招數。屋頂綠化成為潮流,就有商家開始廣告推薦大象糞便是絕好的肥料。有人在看電視時會走開或者不知不覺打瞌睡,就有生產商開發了可以感應觀眾是否在場,或者是否睜眼的電視機,就算閉眼睡覺了,電視機都會自動關閉。
「企業是給了我們很好的正面影響。」家住東京高尚住宅區的園山京子說,「比如買冰箱、空調,就會注意不含氟氯烷。」
「環保意識現在是一種fashion(潮流)。」愛知大學教授大澤正治說,大概5年前,他在歐洲看到環保袋時,就感覺這將會風行日本。如今,這果真已是年輕人喜歡的一種「潮品」。
矛盾的環保社會
早川美妙子家裡有10個環保袋,幾乎每買一宗商品都會送一個,這成了浪費的環保品。「商店裡也賣環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變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細觀察日本人的環保意識,會令人心生矛盾。無論誰踏足這裡,都會讚嘆它乾淨的街道、精細的垃圾分類。不過,當入夜時,看到滿街密如叢林的霓虹燈整夜通明,商店裡精美包裝的商品,又會糾結於這個消費社會的奢侈浪費。
許多垃圾桶放在飲料自動販賣機旁邊,與數十種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裝容器回收法」,認為塑料瓶的回收技術已成熟,允許企業生產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回收。」廣瀨稔也說,「這是站在企業發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廣瀨稔也住在橫濱市,家裡垃圾分為8類,牛奶紙盒必須剪開、洗淨、攤平,才能送去回收點。這個過程要用水電,他與一些家庭婦女一樣迷惑,這到底是環保還是浪費?
馬桶是另一個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馬桶水箱的進水口是水龍頭,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環用於沖洗馬桶。它同時有舒適的額外設置,方便之後有噴水口沖洗肛門,馬桶圈會常年通電發熱,保證如廁人士裸露的屁股不著涼。這顯然有些不環保,於是,有商家生產了感應發熱的馬桶,避免無人時的「浪費」。
許多餐廳提供免洗筷、餐巾紙。如果發給顧客4張餐巾紙,只用了1張,但是最後清理時,嚴謹的日本餐廳會扔掉所有餐巾紙。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環保,這並不是為了減少消費。」染野憲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說道。
走訪哲郎有時會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學三年級測試上,有30%的大學生不會把英語的「生物多樣化」、「全球變暖」翻譯成日文,在小學學習過的蜻蜓、蒼蠅幼蟲,也有很多人不認識。「日本的環保意識整體是很高的,但兩極分化很嚴重。現在有一些『宅族』,只關心自己的事情,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
「像我們這個年紀,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較年輕人,他們接受了系統的環境教育,應該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廣闊的視野。」村井安成說。
垃圾焚燒大國日本,正成為中國各地政府面對垃圾圍城難題時,競相取經的對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對策的權威學者卻高呼,「千萬別學日本!」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應該學習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開,尊重民意,權責界定,應該摒棄的是,一燒了之的依賴路徑。
日本鄉間街頭的垃圾收集點,垃圾被嚴格分類,以利於焚燒或回收利用。 (南方周末記者 何海寧/圖)
日本是個名副其實的焚燒國度,至今仍擁有超過1400座垃圾焚燒爐,作為世界上最早應用垃圾焚燒技術的國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進焚燒爐,這一數據在世界遙遙領先。
然而,專門研究廢棄物處理的名古屋大學岡山朋子博士卻對來訪的中國人提出了忠告:千萬別學日本!
在她看來,中國和韓國民間源於對二惡英恐慌而發生的反垃圾焚燒浪潮,在日本並未出現過,因為當二惡英問題被發現時,日本的垃圾焚燒廠早已遍布全國,「日本的焚燒歷史太久了,發展經歷也太特殊了。」
透過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麼辦。」
本橋勝照是東京新江東垃圾焚燒廠(下文簡稱新江東)管理課事務系的系長(類似於中國的科長或小組長),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參觀。
在日本,到焚燒廠參觀是每個小學生的必修課,而作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燒廠,新東江總是參觀的首選。這座位於東京灣沿岸的建築,單從外觀上看,很難相信竟是一座日處理垃圾1800噸的焚燒廠。隔壁的訓練場上,東京都警察機動隊正在集訓,廠區周圍既沒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見路面被污損的痕跡。
焚燒廠的一樓大廳,是一個專門用於介紹廠區概況的報告廳,這個報告廳耗資近億日元(約800萬元人民幣)之巨,每個座位前都設置了投票器,小學生來訪時可以通過大屏幕進行智力問答,優勝者還會有獎品。為了吸引孩子們的興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採用了卡通造型。
本橋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記著參觀預約,其中不乏中國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預約中已有三個中國的團體,分別是中日友好協會、專家學者考察團和安徽省一正籌建垃圾焚燒廠的地方政府。「他們(中國的地方官員)提的第一個問題無一例外都是:遇到民眾反對怎麼辦。」本橋笑著說。他的回答總是很簡單:信息公開。
參觀者順著樓上的長廊,按照垃圾焚燒的工序流程參觀。在每一道工序車間上面,參觀者透過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車間裡的一舉一動,在玻璃旁,還會有一個電子顯示屏顯示車間內的基本數據。
在東京灣填埋場附近,排列著包括新江東在內的六個垃圾焚燒廠,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節省運輸成本,另外的原因則在於東京灣是相對人口稀少的地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市民們都不願意焚燒廠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東每年的運轉費用是800億日元(約64億人民幣),其中的450億日元來源於政府稅金,而另外的350億日元則是針對企事業單位收取的垃圾處理費用。
「我們的生存狀況挺好,」本橋說,「任何有興趣的市民,都可以來監督我們的財務狀況。」市民們亦很少擔心焚燒廠弄虛作假,因為廠方的定期報告比市民監督更為嚴格。
不久前,東京都的21家焚燒廠中的4家排煙檢測器,測出氣化水銀濃度超標,儘管這個濃度並不會給環境帶來多麼惡劣的影響,但焚燒廠還是主動停止了運轉,並第一時間向所在地區的居民通報。「通報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面是焚燒廠有信息公開的義務,同時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業單位要遵守垃圾分類。」本橋說,「之所以水銀超標,是因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隻狡猾的狐狸」
「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鬥爭,最後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了。」
事實上,焚燒廠並不是天生就願意敞開懷抱,這是日本市民幾十年鬥爭來的結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焚燒廠在日本,也曾遭遇過強烈的反對,但不是因為二惡英,當時的科學家尚未發現,那時的民意主要出於一種狹隘的心理:焚燒廠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邊。
東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燒廠是另一個中共政府官員們的熱衷參觀地,因為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區內的焚燒廠,或許可以幫助回答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遭遇民眾反對該怎麼辦?
還有一年就結束任期的後藤市長,希望在他離任前解決選址問題,然而他親自挑選的一處地方,卻被市民代表們在市民會議上強烈反對。
無計可施的後藤市長向做垃圾處理諮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騎著自行車將武藏野市走了個遍,發現「想找到一片遠離居民區的合適空地根本沒有可能」,所以,「我建議市長還不如把這個燙手的山芋直接丟給市民,直接讓市民來參與選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樂道的經驗就是,從一開始便確定了遊戲規則。為了保證市民參與有章可循,首先確立了選址預備會規則,內容包括:由專家和市民代表組成的環境委員會推薦人員參加選址預備會,每個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如果一年內選不出地址,則意味著市民沒有做出選擇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長的選址。市民們表示同意。
「一開始就確立了遊戲規則,而且是公開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無論這個地址選在哪,最終都必須在一年內有個結果。」八太昭道說,「換句話說,市長不用擔心焚燒廠的地址沒有著落了。」
經過選址預備會的投票篩選,四個地方被列入候選,其中包括市長最初的選址方案。
隨後,選址進入到第二階段,由專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這四個候選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組成了「建設特別市民委員會」,再做定奪,這是31年前的1979年。
後藤市長最初選定的那個地區的代表,為了防止被選上,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代表們做了一個焚燒廠和社區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燒廠建成以後,當地的小學會怎樣、小區會怎樣,還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走遍了日本的焚燒廠,去搜集問題,他們用實際行動樹立了市民參與的榜樣。最終的結果果然不是市長的最初方案,而被選中的地區的代表們非常懊惱,曾一度提出過退場,但因為有約在先,他們最終選擇了尊重規則。
後藤市長的難題果然在一年內解決了,新的垃圾焚燒廠也在1984年順利完工。
三十多年後,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讓市民參與,其實並沒有消除反對者的聲音,而是把反對者的聲音納入到了一個合法的程序中,「本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鬥爭,最後轉化為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了,而我就是那隻狡猾的狐狸。」
在新江東焚燒廠,透過玻璃,可以看到焚燒廠各個工序幾乎所有的運轉信息。
自掃門前雪,解放「東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
如果說武藏野市的經驗解決了民意反對的難題,那麼,地方政府間如何明確垃圾處理責任則是另一個重要話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東京都的垃圾處理都是由都政府來全權負責,隨著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漸覺力不從心。改變源自一場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後,東京的垃圾大多被運往靠近東京灣的江東區填埋處理,隨著填埋衍生的污染和衛生問題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場越來越難堪重負,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提出「在城市夾縫中建造垃圾焚燒爐」的主張。
當時的東京都政府要求下轄各個區都需要建設自己的焚燒設施,「各家自掃門前雪」,儘管將垃圾推進焚燒爐在當時是日本社會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識,但這一主張還是遭遇了阻力,引發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垃圾戰爭」。
其中,最強烈的反對聲來自高級住宅密集的杉並區,他們認為處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責任,跟杉並區無關。
憤怒的江東區居民則堅決反對杉並區的垃圾運進本區的填埋場,喊出了「杉並區的垃圾滾出去」的口號。堅持要在杉並區建焚燒廠的都政府,最終被杉並區居民告上了法庭。訴訟最終以和解而告終,居民最終同意在區內建設焚燒廠。
這場官司促使東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轄各區在垃圾處理上的職責問題。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讓都政府扛著。」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說,「這(杉並區事件)是一個轉折。」
1996年,東京都政府正式通過法規,明確垃圾處理原則上是各市町村的責任。
而東京都23個區的區長們則成立了一個自治單位,即所謂的區長聯席會議,下設一個專門的垃圾處理機構,即東京二十三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東京都政府將分管的垃圾焚燒廠全部移交給了對方。
十幾年來,東京23區的垃圾處理已在一個責任明確的體系中穩定運轉,各司其責:23個區各自負責自己的垃圾收集、搬運與資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 21座垃圾焚燒廠,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則送到相應的處理中心。最終的焚燒灰渣等被運送到填埋場,而填埋場則是由東京都政府負責,「東京都政府終於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動
「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並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燒國度,也從不缺堅定的反建派,近幾年尤甚。年過七旬的廣瀨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會議(NPO組織)會長,便是一名旗幟鮮明的垃圾焚燒反對者。
在廣瀨看來,占到垃圾總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裡直接用廚房垃圾處理機來處理,最終變成肥料。
廣瀨對垃圾焚燒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焚燒廠產生的二惡英並沒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現在的處理辦法就是把收集裝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險源始終存在。或許有一天地震了,也將是危險。」
隨著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燒廠的使用壽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燒廠均面臨重建的問題,而類似於廣瀨先生這樣的新興反建派並非少數。「不誇張地說,現在又是一個新的反建潮。」廣瀨說。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德島縣上勝町。這裡僅有2200人口,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了40%,高達34種垃圾分類的要求近乎變態,每個家庭均配發了廚房垃圾處理機,在居民們的努力下,帶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經實現了資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燒廠無疑顯得多餘。
但是,名古屋大學的岡山朋子博士研究發現,各家堆肥化處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難行,「像東京這種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無處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葉縣這樣可以應用肥料的地方,從法律上來看又是不允許的,因為法律規定,垃圾處理必須在自治體內解決。」
岡山朋子一度建議,不要對落後的焚燒廠進行升級改造,而是將其變成集中堆肥化處理的工廠,但這並不比建焚燒廠更容易獲得支持。她曾對名古屋和韓國做過民意支持的比較研究,結果令她很意外,對肥料轉化廠的支持度,韓國超過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對於焚燒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會認為堆肥有味道,而中國人和韓國人則擔心焚燒會產生危害健康的二惡英問題。」她總結說。
一燒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
岡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來取經的中國人,「千萬別學日本!」
「日本焚燒垃圾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的政策,都是為垃圾焚燒服務的。」而垃圾的出路更應該在源頭減量和循環利用。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垃圾處理正呈現著一個看似矛盾的圖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燒技術的日益精進,對垃圾焚燒的依賴感與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絕垃圾焚燒的呼聲從未間斷。
日本環境省廢棄物管理部官員筒井誠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環境省對於任何致力於3R(reduce,reuse,recycle)運動的嘗試都是支持的,但具體哪個地方應該實行怎樣的垃圾處理方式,應該由當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討決定。在他看來,選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主導方式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
而廣瀨先生擔心的是:現在的垃圾焚燒技術越來越發達,什麼都能燒了,會讓政府和市民們覺得,把垃圾推進焚燒爐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沒有人會有動力做更費時費力的垃圾分類了。他的擔心終於變成了事實。
塑料最早被劃分為不可燃垃圾,是因為1973年東京都在焚燒塑料的焚燒廠的廢水中檢測出重金屬超標。而如今,焚燒技術的進步似乎為將塑料推進焚燒爐提供了安全保證,而節約填埋空間、延長填埋場壽命更是理據十足。廣瀨先生則堅信另外的邏輯,焚燒爐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許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進入一個焚燒爐改造期。而焚燒爐企業表現出的強大的遊說和公關能力,令廣瀨先生心有餘悸,「我擔心改建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會加大日本對於焚燒爐的依賴。」
環境省的官員對上述擔憂的反應則明顯樂觀:「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類意識已經很高了。焚燒是建立在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顯然,這與岡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結論相左,在她看來,日本的垃圾分類和處理的政策,無不是以垃圾焚燒為中心的,而最終也會受制於垃圾焚燒。
照搬了焚燒的日本,也就可能斷送了垃圾問題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