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觀濤,1947年生於浙江義烏,197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劉青峰,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編輯、前主編。畢業於北京大學,先後在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工作;1980年代活躍於學術文化界,任《走向未來叢書》常務編委,著作《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以靳凡為筆名發表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1989年之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學術伉儷,他們擁有共同志趣,學術研究方面長期合作,出版了諸多著作,尤其在系統論和觀念史領域建樹頗深。
到台灣政治大學任教
我和青峰到台灣是命運的安排。我們建立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在學術界很有名,台灣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中文系教授鄭文惠專門帶一個小組來參觀學習。在得知我和青峰將於2008年退休後,他們希望我們能到政大任教,將有關研究引進台灣學術界。我們總覺得對思考中國前途、反思歷史並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來說,海峽兩岸暨香港的生活經驗將極有助益。在一定程度上,大陸(內地)、台灣和香港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呈現出的複雜性的縮影。香港作為英國占領地在100多年中吸收了西方政治社會的經驗。台灣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傳統,同時又完成了現代轉型。三地歷史經驗可以互相補充。實際上,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接受了政大的邀請。
2008年9月1日,我正式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到政大任講座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在我退休前幾年,最令人操心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我任主任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預算。2009年3月,我們從香港搬家到台灣。讓我至今難忘的是,我們家的狗"皮皮"從台大獸醫院隔離處回到政大宿舍化南新村之後,高興得樓上樓下亂跑。雖然我以前多次來過台灣,但真正對台灣有感覺是到政大工作以後。
我對台灣最大的感觸有兩點。一是台灣學生很優秀。在香港中文大學我是研究講座教授,故而沒有學生。台灣學生不僅有很紮實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還對用資料庫進行思想史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我來說,組織研究團隊,帶領學生開拓數位人文研究只有在台灣才能做到。與台灣碩士生、博士生共同研究的日子,也成為我和青峰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記憶之一。一般每周二晚上,我們會一起討論如何將關鍵詞分析運用到中國思想史研究中,聽完學生的匯報已是晚上10點。我和青峰離開憩賢樓辦公室,穿過依然熱鬧非凡的街巷回到新光路的家,皮皮在等著我們。
二是台灣人很迷惘。面對大陸經濟的發展,有些人開始喪失自信心。20世紀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80年代台灣開放黨禁,完成民主轉型;進入21世紀以後,台灣經濟發展停滯,政治體制上的特點因島內意見紛爭而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短期現象,但在學術日益專業化、人的視野日益狹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觀趨勢反而不容易。
我在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曾來台北故宮博物院看藏畫,那是我們新光路的家最熱鬧的時候。我和青峰為兩岸的學生準備晚飯,皮皮則興奮得不知道應該去親近誰才好。我家院子裡本來就有一棵桂花樹,有一次我和青峰買了一盆白蘭花回來,青峰提議將它種到院子裡。想不到不到一年,白蘭花樹蔭已高過屋頂,並四季開花。
我和青峰認為在漂泊歲月中的思考需要進行總結,並打開更寬廣的思想空間,而不應在香港的海邊或台北的鬧市過退休生活。青年時代,我們通過對超穩定系統的研究,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在香港期間,我們不斷深化中國視角,並比較中西社會的現代觀念。與此同時,我們感覺到西方學術這潭水很深,不太敢講全人類普遍的歷史。就我的本心而言,最終的目標是人類文明史的研究,即探討不同文明的演化以及現代社會的起源。
2008年我完成《歷史的巨鏡——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一書。該書初步提出了一個研究綱領,將中國文化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放到軸心文明演化中加以理解。2009年搬到台北之後,我沒有覺得其有進一步展開的必要,因為我和青峰已在專業範圍內從事規範性研究太久,與其去建立大歷史觀,不如多做一點求實的研究。當我們游弋在人文世界中時,耳邊有時會迴響起青年時代看過的電影《鴿子號》插曲的歌詞:"駕著船兒去遠航,趁現在還有風景可看,趁世界還是自由之鄉。"這時,我並沒有感受到從哲學上探索開放社會的迫切性。
大歷史觀的痛苦
自2011年起我不在政大教課了,但仍做著課題研究。之後,我日益感到自己應該從專業和細節研究中擺脫出來,再次關注思想和宏觀歷史。於是我和青峰又開始漂泊了,在台北、杭州、北京和香港之間穿梭。我們總覺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們去做,但又說不清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正在老去。在和台灣朋友的交往中,我們深感他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特別是1949年來台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他們在這裡留下的腳印,以及他們和台灣水乳交融的感情,令我們十分感動。但是,我們又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不可能像他們那樣。
我們總是處於不能自拔的悖論之中。一方面,我們認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不是大陸(內地)、台灣和香港三個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是中國人,以探索中國文化前途為生命的意義。我們是無根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趕路"來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很少有像我們這樣的,在老年來臨之時仍在做毫無限定的、自己也說不清的探索。我們不知道哪裡是故鄉,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將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即便如此,我和青峰還是決定搬回大陸居住,一方面青峰實在不能適應台北過於潮濕的氣候,另一方面是我們的父母都已90多歲了,每當接到杭州老家的電話,我都心驚肉跳,擔心老人出現意外。此外,我還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在杜軍的邀請下,我和青峰住進了北京西郊的西山書院。2011—2013年,青峰的母親和我的父母分別過世,能陪伴他們走完生命最後的歷程,使我們不留遺憾。
回大陸定居後,有一件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在朋友的支持下,我們開始給企業家和非學術界的思想愛好者做系列學術講座。在和他們的交往中,我們第一次覺得自己並不是無根的。他們和我們一樣,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傳人,還是中國文明走向現代之路的探索者。日益精細化的分工,既是今日大學學術研究最大的優勢,也是其最致命的弱點。當專業的深入成為學者的主要追求時,專家往往看不上知識的整合,特別是將高度整合的人文歷史向外行講述。然而,正是在上述系列講座中,我們發現了應該進一步研究的新方向。因為在給非學術界的朋友授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針對今日世界和中國的問題,把自己以往的研究貫穿起來,提供一種新的視野。這既是一種立足於觀念史—系統論的大歷史觀,也是對現代社會起源和未來走向的鳥瞰。在持續幾年的講座中,我和青峰完成了中國思想史的整合,完成了《中國思想史十講》的草稿。此外,我還完成了《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的寫作。我從青年時代就在尋找的大歷史終於顯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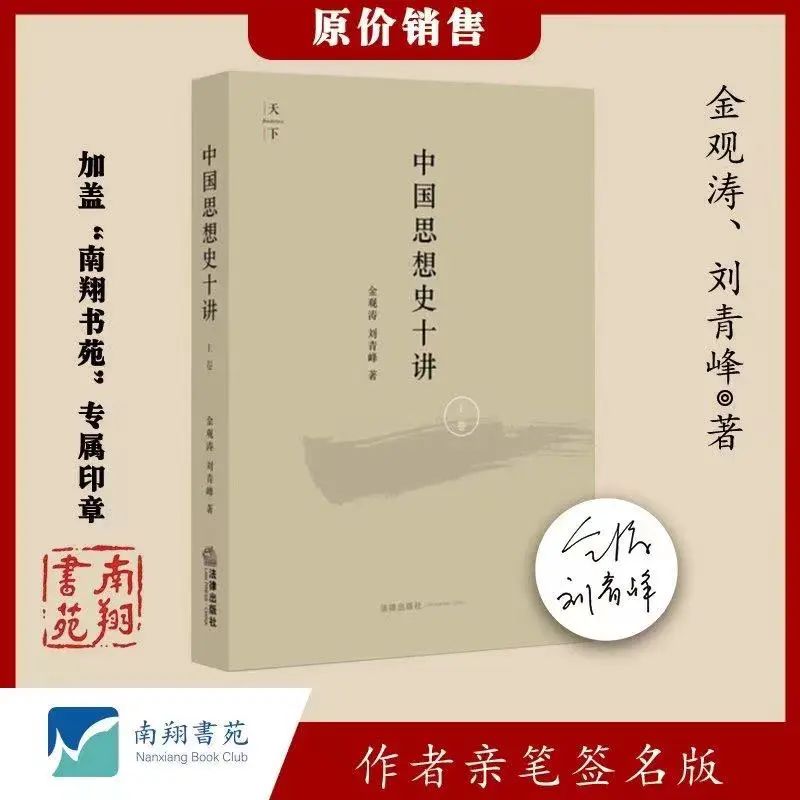
完成上述工作之後,我理應感到高興,實際上卻陷入一種深深的憂慮之中。我向來把大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發現,即研究者在得到大歷史觀後,能夠看到之前看不清的東西。我早就認識到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的新階段,但對現代社會往何處去的看法是朦朧的。我通過寫作《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一書發現:軸心文明起源的本質是將不同類型的終極價值追求(終極關懷)注入社會,形成不同的超越視野,包括希伯來救贖宗教、印度解脫宗教、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認知理性和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傳統文明。其中,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認知理性因最終證明無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義,與希伯來救贖宗教結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其在現代性起源過程中又進一步演變出現代科學。總之,這些超越視野使得個體能夠從社會中跳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即實現超越突破。正因如此,文明在演化中不會滅絕,人類才有如此輝煌的現代文明。但是,我發現終極關懷在現代社會是不穩定的,它日益遭受現代科學的衝擊,以致最後有可能解體。換言之,終極關懷正在日益喪失其真實性。
大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可以使人們透過紛亂的表象看到文明的結構。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終極關懷慢慢退出社會,這件事人人皆知,但唯有透過大歷史觀才能理解其後果有多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人類文明將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狀態。無論科技多麼高超,經濟多麼繁榮,沒有超越視野的文明終將難逃滅絕的命運。如果我通過大歷史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對的,則意味著現代社會是不穩定的。這種憂慮終於轉化為大歷史觀的痛苦。
我深知實然不能推出應然。迄今為止,應然世界都建立在終極關懷之上,因此現代社會不能沒有終極關懷。在現代社會,終極關懷和現代科學之間存在著日益嚴重的衝突,其後果是終極關懷退出社會以及價值基礎的土崩瓦解。終極關懷和科學的衝突必須消解,因為人類不可能再去尋找新的終極關懷了。更重要的是,現代價值不能以終極關懷作為基礎。換言之,要建立穩定的現代社會,終極關懷必須純化,[4]即化解它們和現代科學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此同時,終極關懷還必須和現代價值分離。這一切並不是所謂"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所能實現的。如果不能實現上述變化,20世紀現代社會經歷的浩劫會以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捲土重來。
大歷史研究帶來痛苦的根源在於,明明知道大倒退將會發生,卻不能阻止它。歷史學家常說,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是那些我們不大記得的教訓。事實何止於此,歷史真正的教訓是人總是會忘記歷史的教訓。這必將導致過去的苦難再一次重演。對此,我們難道真的無能為力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在各種場合用艾薩克·阿西莫夫《基地》的故事來隱喻這種大歷史觀,我真不知道一個歷史學家還能做什麼。作為一個思想者,我最終選擇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無論未來有多麼晦暗不明,只要遠方存在著光,就應該向光明走去。思想者要做的是將這種探索進行到底,而不是等待。其實,正如歷史不是講故事,歷史學家要做的也不是為未來建立文明復興的基地,而是去發現歷史真實,以改變當代人在歷史面前的盲目性。然而,對此我應該去做什麼?我又能做什麼呢?最終,我選擇回到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這一世紀難題的哲學探索之上。事實上,如果出現現代社會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終極關懷)的真實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學異化為科學烏托邦。
(本文摘自金觀濤《消失的真實》一書,標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