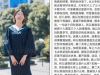烏雲密布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1957年10月7日晨,楊剛被人發現死於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人民日報》社宿舍內。她是服過量安眠藥而死,時年52歲。
此時,楊剛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此前,她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辦公室唯一的副部級秘書,是周處理國際事務和對外宣傳的得力助手之一。
楊剛為什麼自殺?
一,因病說。
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持這種說法。
1955年,她不幸遭遇一場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醫治後,仍有後遺症,經常頭痛,無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請病假,到廣東從化、杭州療養,但療效不佳。
費正清分析說:「她發現她的大腦遭受的損壞如此嚴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殺了。」
但是,據她在報社的同事講,她自殺前,出席會議、撰稿、處理稿件等,都算正常。這說明病情干擾並不大。
二,丟本說。
1950年10月,作為周恩來的秘書,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電,裡面有一些黨的機密。為此,她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說,筆電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撿到筆電的人已把它交給周,周已看過裡面的內容。
筆電內,不僅有黨的機密,還有楊剛與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主任費正清親密交往的內容,有她和費正清的聯繫方式。
周恩來將上述情況告訴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要他找楊剛談話,將她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管國際宣傳。
雖是平級調動,一切待遇不變,楊剛還是很難過。她知道,周恩來和黨中央不信任她了。
反右運動一來,她擔心中共藉此整她,一時想不開,自殺了。
這件事發生在七年前,雖然對她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也可能是其自殺的原因之一,但不應該是主因。
三,理想破滅說。
中國作家傅國涌持這種說法。
回顧楊剛的人生旅程,這個說法或許更可靠一些。
為什麼?
因為楊剛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拼命奮鬥,都是基於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為此,她背棄了她的家庭。
楊剛,原名楊季徽,祖籍湖北沔陽,1905年,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個官宦之家。
她的父親楊會康,歷任武昌守備、江西道台、鄂省政務廳長、湖廣漕運使、湖北省代省長,還是一個古籍字畫瓷器收藏家。母親則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在家塾誦習古籍;中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南昌葆靈女中;大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她就是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的。
北伐戰爭期間,中共鼓動農民燒了她的家,毀了她家的藏書,分了她家的田產,還監禁了她的父親。
為此,她跟信仰不同的丈夫分道揚鑣。
大學畢業不久,她嫁給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鄭侃,婚後生育一女。但日後,她與丈夫因信仰不同而常爭執。
有一天,他們又吵起來了。
她說:「我未能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但我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時代賦予我的使命,不允許我做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更不允許我做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說:「當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裡也總想著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請問:這樣的革命給我帶來什麼好處?」
一番爭吵後,她與丈夫各奔東西。
為此,她捨棄了自己的婚姻。
與丈夫分開後,她一直單身。有一年,在香港,她採訪中華抗敵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許地山之後,許地山夫人想給她當紅娘。
她說:「我只能先感謝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對愛情是深有體會的。愛是雙向的,只有互相真誠的愛,才是人類最聖潔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強湊合在一起,就會使夫妻關係變成庸俗的情慾夥伴。我現在寧願孤獨地生活,也不願與不稱心的男人勉強湊合。」
一直至去世,她都沒有再婚。
為此,她與唯一的女兒長期分離。
女兒鄭光迪三歲時,被她寄養友人、美國女教授包貴思家。之後,她把女兒送到延安。女兒上中學時,她在美國;女兒上大學時,她在上海;女兒去蘇聯留學時,她在北京;她自殺時,女兒仍在蘇聯。
為此,她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國內到國外,一直辛苦奔波。
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後,她和謝冰瑩等作家共同發起成立中共附屬組織——北方「左翼作家聯盟」。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結識了替中共做宣傳的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這年秋,她回到北平,協助一名美國記者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個美國記者就是後來寫出為中共唱讚歌的《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
1937年,她在《大公報》當記者,後隨報社南遷香港,接替蕭乾主編《大公報》副刊,讓這個小小的副刊「環上甲冑,披上戰袍」,成為「一隻號筒」,「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
1943年,她輾轉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其才華得到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賞識。周指示她以編輯、記者身份,與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美國記者聯繫。在此期間,她結識了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主任費正清。
1944~1948年,她成為《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根據中共的指示,她寫了大量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問題的通訊。
她還在美國報界、文藝界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學者之間奔走呼號,反對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支持中華民國,爭取美國對中共的同情。
期間,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進修文藝。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國。在香港,她利用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的便利,全力做《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經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宗旨的《大公報》,轉向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
她從香港北上,到達西柏坡後,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接見。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報》改造成中共的《進步日報》,並擔任副總編、黨委書記。
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報》的軍代表,把這份報紙也改造成中共傳聲筒。
1949年10月1日,她以新聞界代表的身份出席開國大典,寫了通訊《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她滿懷信心地寫道:
「我們幾千年來的希望,我們幾千年來的要求,要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五者具備的國家的要求——在過去常常使人稱為是白天大夢,或者是唱高調,現在這個幾千年的大夢一定會實現了。」
1950年,她奉調進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書。不久,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她沒日沒夜,全心全意為周服務,沒有任何怨言。
但是,1950年10月她因筆電丟失被調到《人民日報》後,一直到1957年,她親歷了毛髮動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運動。
特別是1957年毛髮動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報人、作家、藝術家,包括她的朋友,領導,同事,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全國上下,人人自危。
這場運動,使她曾經火熱的心,變得冰涼;那千年的大夢,變成一枕黃粱。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有三大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
到1957年,彭子岡、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
她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岡的會上發言,揭批她當年在《大公報》的同事,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黨員彭子岡。
到1957年,她的燕京同學、多年的摯友蕭乾,也被打成右派。
抗戰前,她請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從此,《大公報》成為發表和轉載中共根據地文藝作品最多的三家報刊之一。
1949年,蕭乾已接到英國劍橋大學的聘書。在是否回國的問題上正猶豫不決時,她力勸蕭乾回國,為「新中國」效力。
現如今,蕭乾僅僅因為響應黨的號召講了幾句真話,竟被打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壞人之列。
她自殺的前一天,作為《人民日報》「反右領導小組」的第三把手,不得不寫一篇批判蕭乾的文章。
《人民日報》副總編林淡秋,將她的文章交給編輯葉遙校對。過了深夜23點,快校完時,她敲門而入,對葉遙煩躁地說:「沒意思,沒意思,不要發表了。」
她自殺前兩天,她被安排到文聯禮堂參加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會。
她挨著丁玲坐著。當時,丁玲拿著手絹,不停地擦眼淚。她則表情諳然,呆若木雞。
當時任中國作協黨總支書記的黎辛後來回憶說:「我和(中組部長)安子文談到楊剛自殺時,安子文曾經問過我:『這天開會有誰知道?』我說,我們五人小組知道。安子文又問:『還有誰知道?』我說:『中宣部部長和副部長知道。』我又說:『部長陸定一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他不會幹這個事。』安子文忽然大聲說:『那就是周揚,肯定是周揚通知楊剛的,他可能想擴大戰果。』」
周揚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毛在文藝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運動中,過去反對過他的,對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統統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寫道,七整八整,文藝界就剩下他(指周揚)一個「正確」的了!
周揚點名要楊剛參加批鬥丁玲等人的會,讓楊剛不寒而慄。
黎子文寫道:「那種場面,使楊剛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樣被批鬥,所以自殺了。」
1957年6月9日,標誌反右運動開始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第二天,楊剛以「金銀花」的筆名,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這是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她寫道:
「弟兄們,我想起那些年我們一起做的夢,不論人家怎樣想,幾萬萬人的夢想,會是很大的吧;那時候,美國人和地主官僚資本的鞭子抽得我們滿地滾呵,我們的苦惱有天那麼大,我的夢也有天那麼大;天上飛著大紅旗子,天幃和煙囪交頸擁抱,繞著我們的紅旗呼呼地,呼呼地,噴出我們強烈的詩篇——鋼鐵的火焰和煙雲;我們全站起來了,抬出了紫艷艷的晨曦,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洪流把人們載送到永遠,永遠。雖然我們吵架,爭工分,爭豬食,反對官僚主義……可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弟兄們,我們一起做過夢,又一起把夢變成了生活。難道這一切都錯了嗎?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
「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這壓抑已久、從心底迸發出的驚天一問,或許正代表了她拋棄個人的一切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理想破滅。
結語
作為一個把一切都獻給黨的忠誠女兒,楊剛曾經誠心誠意地相信:中共是「一個為自由和尊嚴(幾千年來他們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和尊嚴)而進行鬥爭的偉大民族的化身」。
但是,從中共建政後強迫知識分子自我羞辱的「思想改造運動」,到1957年「引蛇出洞」,然後一網打盡的反右派運動,她苦苦追尋的自由在哪裡?尊嚴又在哪裡?
理想原是鏡中花,一生奮鬥全白搭。
楊剛絕望了,只好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