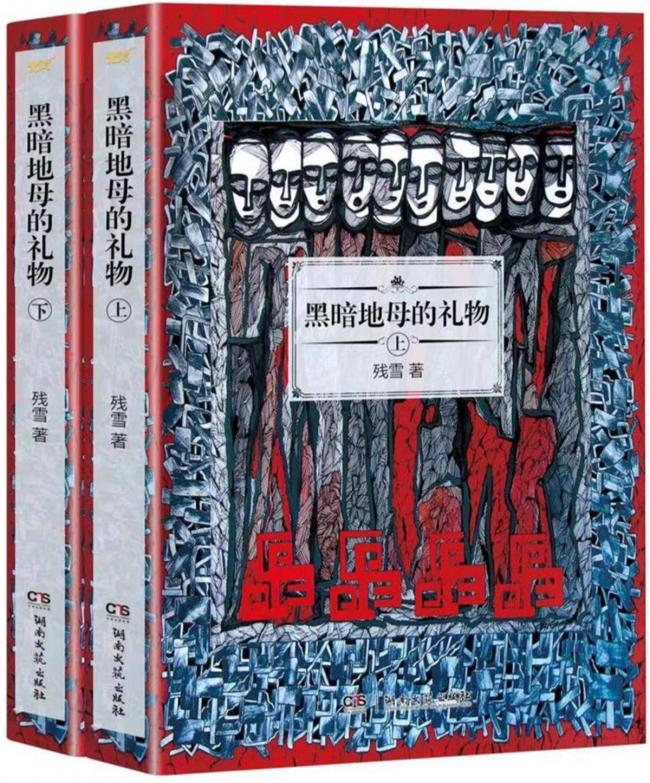1
中國的純文學還活著嗎?
大概在21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的文壇上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時至今日,這個問題和答案似乎都已然漸行漸遠了。
2012年似乎是個分水嶺,那一年,還不算很年邁的莫言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算是給八十年代開拓「先鋒之路」的「50後們」交了一份答卷。
縱使結局很完美,但就這樣結束了嗎?
我的內心中不禁閃過了一個女作家的身影,在那些曾經在先鋒之路上走過的人裡面,她曾經曾有機會續寫莫言的傳奇,更難得的是,她一直在那條路上走著,未曾停下。
她的名字叫殘雪,對於很多人而言,這個名字顯得遙遠而陌生。
1953年,殘雪出生於長沙,原名鄧小華。
她的父親畢業於著名的「湖南一師」,後來參加了革命,「在戰爭年代裡頭立過大功」,建國後一路當到了《湖南日報》主編,和很多後來的「先鋒派」作家不太一樣的是,殘雪是非常標準的革命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這種家庭背景,奠定了殘雪與眾不同的文學視野。

-殘雪一家在報社-
建國後出生的這批作家,被五十年代以及之後的二十餘年裡的當代中國反覆打磨,上演了無數部真人版的《人世間》,而這無疑也塑造了他們的文學和性格,他們註定是開拓的一代。
不過即使是一代人,也各有各的風景。
小時候的殘雪,看到的並不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世界,而是悲愴和陰暗。
在她年僅四歲的時候,她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看過前面幾期文章的應該很明白,那會兒但凡和「右」占上邊,那你家裡基本上就慘透了。
不出意外,殘雪被迫和父母分離,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被被打散下放到農村勞動(其中就包括殘雪的哥哥,著名哲學家鄧曉芒),而殘雪則因為年幼,自小跟著外婆一起生活。

即使我們今天去讀殘雪的小說,也能比較直觀地去感受到她作品中那種介乎於夢幻和神秘之間的色彩,而殘雪的這種寫法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她外婆從小的教育。
雖說建國之後不能成精,但湘西特有的神秘文化還是在老一輩人身上有所體現,在殘雪小的時候,經常聽外婆講一些神秘故事和迷信風俗,這些東西在殘雪的思想中生根發芽,最終融入到了作品中。
如同洪子誠評價的那樣:殘雪擅長以現實與夢幻「混淆」,敘述人以精神變異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懼感,來創作了一個怪異的世界。
「在我同她相處的年頭裡,她總是用好笑的、有幾分自嘲的口氣講那些絕望的故事」,殘雪這樣回憶著自己的外婆。
過了1962年,殘雪家比較幸運的摘了「帽子」,一家人得以團聚,殘雪也因此得以在家中享受到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殘雪的哥哥鄧曉芒發後來曾回憶道,那時候一家人八口擠在二十多平的小房子裡,幾個孩子圍在火爐旁,輪流讀著《魯迅全集》的第一卷,而父親則坐在一旁的書桌上,認真地批註著馬列哲學。
當然這種好景對於殘雪的家庭而言並沒有太長久,十年動亂一來,殘雪的父親又被下放到了牛棚里。

殘雪那時候已經是少女初長成了,就搬到了湖南師範的宿舍里照顧父親,開始了那段被她稱之為「小黑屋」的歲月,在後來的創作生涯中,殘雪寫下了那篇《歸途》,其中就出現了「小黑屋」這個景象。
在殘雪從幼年到少女再到青年成家的這段時光里,她所見到的,只有無盡的恐慌、動盪、黑暗和不安,這將化作她的回憶,也將成為她的素材。
2
時間來到改革開放初,這個時間無論是對中國還是殘雪本人而言,都是一段不可複製的機遇。
在這之前,中國國內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極少,只有少量的俄文作品,而當70年代末,國門打開之後,大量的文學作品開始通過翻譯,湧進了中國,那些曾經沉浸在奧斯特洛夫斯基作品裡的青年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卡夫卡和博爾赫斯。

而殘雪又是其中特殊的那個。
她在閱讀翻譯的過程中還堅持嘗試著去讀外文原著,這也讓她的文筆多了幾分外文的「原汁原味」。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對莫言意義深遠一樣,卡爾維諾等人同樣也讓殘雪的文學之路得以開啟。
「80年代至90年代我們大開眼界,向西方學到了很多好東西,並運用到創作中,使文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殘雪這樣回憶著。
1985年前後,已是人到中年成婚立業的殘雪來到了父親的病榻之前,拿出了一部手稿請父親看,這部手稿,就是她的處女作《黃泥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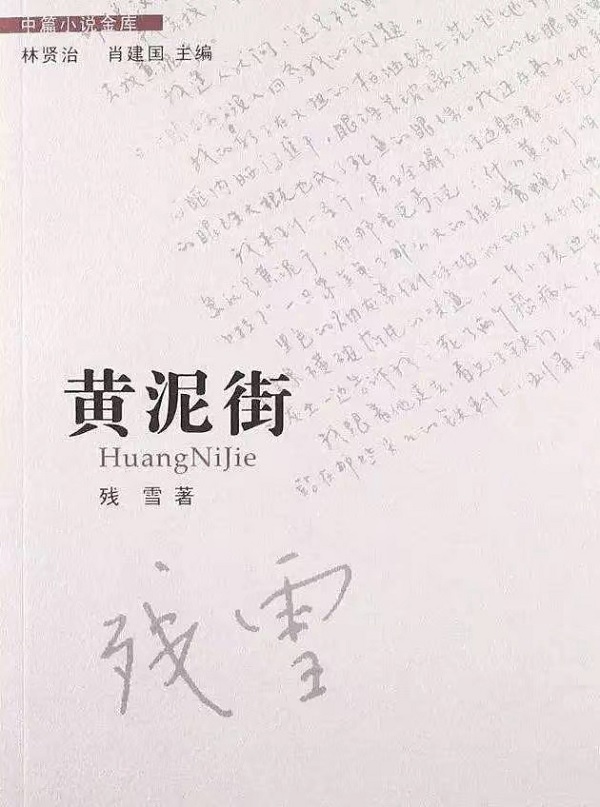
這部小說實際上是殘雪作品的一個縮影,一方面「黃泥街」取材於十年動亂時期殘雪的個人感受,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殘雪外婆從小給她講過的故事,在外婆的故事裡,永州確確實實有這樣一條街。
但事後殘雪問了許多人,都不曾找到這麼一條街,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似乎早早地就與殘雪結下了緣分。
《黃泥街》的第二個讀者。大概是殘雪的哥哥鄧曉芒,鄧曉芒為這部小說吃了一驚,小說中大量的象徵手法非常地老練,絕不像是一個新人作家的手筆。
帶著家人鼓勵,殘雪拿著手稿跑到了北京,但過程卻不像想像中那麼順利。
《人民文學》的編輯對這部風格奇特的小說分成了兩派意見,總編李曉峰覺得還不錯,但也有編輯對此嗤之以鼻,最關鍵的是,這部小說實在是有些敏感,因此最終《人民文學》沒敢接。

回到湖南,殘雪沒有氣餒,而是繼續創作,同時也結識了一大批作家。
不久之後,殘雪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污水上的肥皂泡》在長沙的《新推薦》上一炮而紅,其中那句「我的母親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令人印象深刻。
隨後,她的作品登上了《收穫》,正式走上了作家之路。
當然,真正奠定了殘雪文壇地位的,還是那篇著名的《山上的小屋》。
從個人角度來講,我認為我們很難用通俗文學的邏輯思維去試著理解這本小說。
生病的母親,被整理過的抽屜,山葡萄的葉子以及父親的白髮,有太多讓我們難以捉摸的意象。在殘雪的筆下,構架了一個充滿陰暗的小屋,和一個互相猜疑的家庭。
這本小說的意義在於,給予了先鋒文學一種不同的探索性,在之後的歲月里,這種探索性被殘雪一直堅持著,國際上也認為,殘雪是「中國的卡夫卡」。
3
長此以往,殘雪似乎都以一種「狷者」的形象對外界展示,而且從未改變過。
在自己的文學風格上,她毫不諱言的說:
「所以文學作為文學自身要站立起來,就必須向西方學習」。
這當然引起了一堆人的驚呼甚至反感。
這也讓殘雪的作品頗有幾分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意思,雖然殘雪的書在國內以小眾的純文學為標籤,但確實是翻譯到國外最多的中國作家之一。
而在對同其他作家的點評上,殘雪更是毫不客氣。
她將炮筒對準中國作家圈,直言不諱地挖苦那些在文壇混,和批評家一起欺騙讀者的作家們。
「許多作家寫過兩三部東西之後就空掉了,江郎才盡,轉行、用劣質品來矇騙讀者的比比皆是。「
說到王蒙,她覺得這位老前輩「這位老作家在新世紀裡的表演實在令人失望」。
說到後面一點的格非(格非在八十年代末寫了「江南三部曲」),她則乾淨利落地指出「我只看到一個過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點歷史感悟在勉為其難地拼湊所謂的『中國故事』」。
而即使是對同為女性作家的王安憶,殘雪的評價也堪稱刻薄:「她近年的作品水準下降得不像話,大概做官做上了癮吧」。
這樣尖銳的言論當然不被討喜。
2007年《殘雪文學觀》發表以後,殘雪在文學界的形象似乎越發地固化起來,「不近人情」「孤僻」「小眾」甚至「故作姿態」等等,成為了她身上的標籤。
但是,誰又能說這樣的堅持在文學上是毫無意義的呢?
當「50後」的先鋒們日漸老去,皺紋爬上他們的臉和筆尖,我們應該包容一個還在戰鬥的人,儘管她顯得與眾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2019年的收穫,對於殘雪而言,也許是對其這種堅持的一種褒獎。

這一年,殘雪同時獲得了法國布克文學獎提名和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且賠率高於年年陪跑的村上大叔。
對於這一切,殘雪還是表示地很淡定,她認為,這意味著諾貝爾文學獎開始更多地關注「高層次的純文學」,而她則還在等待著自己的讀者成長起來。
「廣泛的影響還不夠」,殘雪如是評價自己作品。
話題似乎又回到了我們開頭討論的那個問題:中國的純文學還活著嗎?
殘雪似乎已經用她近四十年的寫作生涯給出了一個答案:
是的,還活著,而且在她的預期中,會比現在有一個更美好的前景。
延伸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將揭曉,中國作家殘雪躍居「賠率榜」第一名
202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結果將於北京時間2023年10月5日公布。每年諾獎公布前,英國專門刊登全球博彩的網站Nicer Odds也會受到關注,它代表了一部分國外讀者對作家的支持度。當前排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賠率榜第一名的是中國作家殘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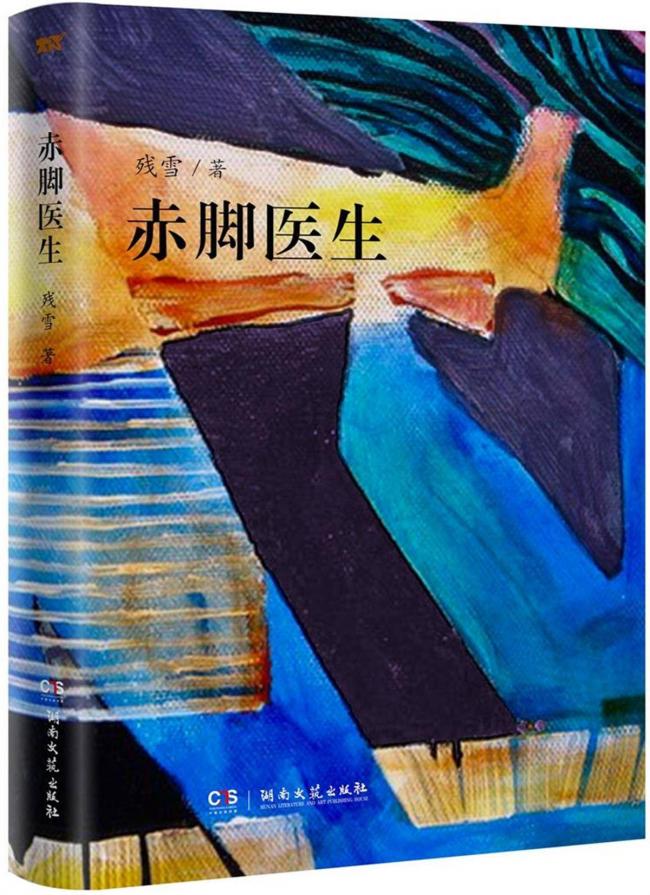
殘雪近幾年是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的常客,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眾多殘雪的作品。記者從湖南文藝出版社了解到,今年殘雪的呼聲如此之高,與殘雪的長篇小說《新世紀愛情故事》瑞典文版在瑞典面世可能也有關。《新世紀愛情故事》譯者是瑞典著名翻譯家陳安娜,她的譯作多達40多種,諾貝爾獎得主莫言主要作品的瑞典譯本便是由她完成。《新世紀愛情故事》在瑞典出版後,即掀起一波殘雪熱,瑞典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該書近日入圍瑞典最佳翻譯文學獎短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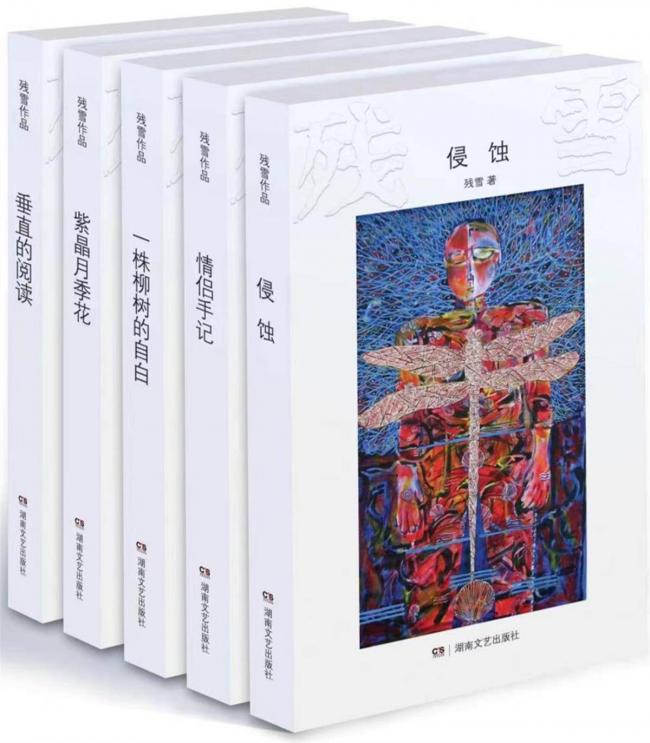

殘雪稱自己的敘事風格為「靈魂文學」,她在作品中呈現出的活躍的想像力和深邃的精神世界,一直是評論家關注的焦點。自從2019年殘雪入榜諾爾文文學獎賠率榜,「殘雪是誰」成為當年網絡推文的爆款。此後幾年,大家對殘雪的名字也越來越熟知,她的作品大量出版,眾多普通讀者讀到了她的作品,殘雪也從小眾走向了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