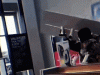很多涉事不深的人往往將白左視為偉大的道德典範,但事實上,這種認知是極為錯誤的。
白左的源頭:個體的自私和對責任的厭惡
儘管當今世界的白左思潮源流甚多,但他們思想最重要的成型節點則在於兩位有趣的思想家:一位是法國大革命最主要的啟蒙者雅克·盧梭(1712-1778),世界史上最早的左派政治團體雅各賓派,即是標榜盧梭思想的維護者,並推行了現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權措施;另一位則是在戰後五六十年代的哲學家保羅·薩特(1905-1980),現代白左思想就是在他所熱衷的「五月風暴」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走向成熟,並逐漸從人厭鬼憎的「頹廢品」占據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薩特本人也被他的媒體崇拜者們稱為「世界良心」。
不過,在一個具備健全常識和道德觀的人看來,盧梭和薩特這樣的「人類良心」,如果扯開被其追隨者不斷修飾的耀眼桌布,實際上不過是兩個不擇不扣的人渣。
法國思想家盧梭不僅是一個肆意玩弄女人的風流浪子,更是一個連續丟棄五個親身骨肉的「好父親」。從某種程度上看,後世左翼文學家筆下的「法蘭西良心」,其作為更像是某些為了還債而賣掉自己孩子的賭棍。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法蘭西的良心會用自己的如神之筆將其「扔孩子」的作為,描繪成「保護情人名譽」和「爭取人性解放」的「義舉」,而心智相對古樸的賭棍則只能將父子親情化作賭桌上的新籌碼。
平心而論,丟棄一個自己的孩子的父親,已屬相當罕見,而盧梭卻一連丟棄了五個,這實在可以稱得上最徹底的「自私涼薄」之人,而這樣的人能夠被白左文學家稱為「法蘭西的良心」,實際上使得筆者很長時間內對白左人士和法蘭西心懷恐懼。不過,對於被盧梭拋棄骨肉的作為,沒有比歷史學家保羅·詹森(Paul Johnson)在《知識分子》一書中描述得更恰如其分了:「他們(盧梭孩子)都沒有名字。估計他們也都沒有活多長……盧梭告訴他的情人:拋棄孩子是唯一『捍衛她榮譽』的辦法。然而事實上,最後唯一被保護的是這位名作家自己生活的舒適和自由,以及他自承對於父親責任的不屑。」
薩特雖然沒有盧梭那樣驚世駭俗的棄子「壯舉」,但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動家西蒙娜在標新立異方面則毫不遜色。這位被很多左翼媒體視為「人類標杆」的道德模範,在最基本的家庭倫理上糟糕得一塌糊塗,其程度哪怕是最開放的社區也難以忍受。
如果非要實事求是地看問題,那麼左翼報人筆下的「人類標杆」很可能只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流氓。早在戰前20世紀的30年代,身為教師的薩特和西蒙娜夫婦開始嘗試扮演真正的禽獸:在這裡,「人類的標杆」喜歡誘騙不同的處女學生上床,隨後迅速對她們失去興趣,而偉大的女性伴侶則熱衷於勾引自己的男學生,並將做愛的細節告知她的愛人。與此同時,薩特也是一位迷幻劑和安非他命用品的愛好者,曾經一度因嗜食迷幻劑而精神崩潰。
當然,與偉大的盧梭一樣,傑出的左翼思潮領袖薩特同樣將自己的性癮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繪成一個宏偉勇猛的壯舉,將厚顏無恥闡述為對「存在與虛無」的自由探索。

如果按照傳統道德來看的話,薩特和西蒙娜的生活實際上不過是兩個吸毒淫魔的苟合。1943年,一名憤怒的母親向法院提出控訴,控告西蒙娜和薩特腐化未成年人,作為「皮條客」使薩特誘姦了自己的女兒,然而此案後來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
那麼,是什麼驅使白左的前驅們如盧梭和薩特等,義無反顧地反抗傳統道德的價值觀呢?
白左思潮的鼻祖盧梭,在自己的《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一章里,將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動機進行了最徹底的刨析,他聲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對自己五個孩子的拋棄,本質上就是對約束他放縱之枷鎖的拋棄,而這種枷鎖就是盧梭身為父親的責任——即盧梭認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無處不在的枷鎖」也就是「父親的責任」、「家庭的責任」和「社會的責任」等傳統道德義務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這種對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厭惡,同樣出現在薩特和她伴侶西蒙娜的人生觀中。西蒙娜在她的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第二卷中這樣描述她和薩特的理念,「(我們都認為)婚姻將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責任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們)來說……自由僅僅存在於自由的頭腦與心靈中。」
從盧梭和薩特兩位白左先驅思想的內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礎在於個人的絕對自私和對家庭社會責任的絕對厭棄。盧梭冷酷無情地丟棄自己的兒女,絲毫不考慮他們的死活;薩特肆意地玩弄誘騙自己的女學生,卻豪不在乎她們的命運。兩位「人類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後,是其人性的絕對自私和絕對涼薄。
事實上,1964年開始的美國「反越戰」運動和1968年3月爆發的法國巴黎五月風暴,這兩場標誌著現代白左意識形態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運動,恰恰體現了白左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在。美國的反戰運動,是美國年輕人因逃避兵役而引發的政治運動;五月風暴爆發的直接原因,則是法國大學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進入」的禁令。這兩場運動,本身反抗的就是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對個人的約束,即西方新一代年輕人,相比其父輩更加自私。他們美妙包裝下的唯一訴求,就是掙脫道德、義務和責任對他們的約束。

法國五月風暴和美國反越戰運動中,最出名的口號,"要做愛不要作戰",實際上恰恰反映了對社會責任的拋棄和對個人慾望的追求——而現今歐洲和美國的左翼政治家,很多受到了「五月風暴」和美國反戰運動的薰陶。
「政治正確」:確保不道德者的「道德」
無論是盧梭還是薩特,如果按照傳統道德來看的話,都是不擇不扣的流氓惡棍;不管是五月風暴中的浪蕩學生(這場運動隨即遭到法國相對保守的大多數民眾堅決反對),還是反越戰運動中逃避兵役的怯懦青年(據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言,大多數美國人一直支持美國參加越南戰爭),若以傳統道德而論的話,相比其父輩,實際上都是嚴重缺乏家庭倫理和社會責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運的是,這些傳統道德的背棄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飾非」的本事。
盧梭以巧妙的哲學構思,將他丟棄五個孩子的舉動順理成章地描述為掙脫人性枷鎖的勇猛創舉,並反過來指責那些試圖以家庭道德和「父親責任」約束他的社會輿論,不過是腐朽骯髒的牢籠;薩特則以重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通過宣揚「存在主義」的信條,把他厚顏無恥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對「真正自由」理念的踐行;而那些試圖逃避兵役的美國嬉皮士青年和浪蕩懶散的巴黎大學生,則把他們自私的動機,巧妙地解釋成對和平的嚮往和對自由的渴望。
另外,為了標榜自己比傳統道德的守護者更有道德,白左的先驅們——扔掉五個骨肉的盧梭、誘姦學生的薩特和逃避兵役的嬉皮士及希望男女生混住的巴黎大學生,提出了一些聽起來更有層次、本質上卻違背常理的新道德準則。
盧梭扔掉五個骨肉之後,把自己標榜為「人權」的捍衛者,表示自己時時刻刻都將公民的權利放第一位;薩特不斷誘姦不同的女學生,然後聲稱自己將會為全世界的良知而奮鬥,為了體現自己的絕對寬容和公正,他甚至拋棄了自己的祖國,表示將支持阿爾及利亞伊斯蘭聖戰士對法軍的攻擊;美國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視為反抗霸權的勇士,同時也把自身描述為幫助黑人反抗種族壓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權」運動的推動者;巴黎的五月風暴青年的技巧則與之類似。
實際上,多元文化、平權運動和反權威等上世紀60年代開始風行的白左道德詞彙,本質上是對自私者逃避傳統道德責任行為的一種掩蓋。
白左美德的本質:不付出的假道德
美德的本質在於責任,而責任則是一種需要長期付出的枯燥瑣碎之義務。
傳統價值觀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體責任基礎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紮根於長年累月善待雙親、盡人子之責任的行為之上;「好父親」的美德,只可能源於一個父親多年來盡到了養育子女的責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樣如此,都是建立於具體的責任之上的。
但白左的道德則不同,如果這種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話。
一方面,與傳統道德相比,白左道德的最大特點,就是對社會責任的丟棄和對個人名聲的追求。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盧梭、薩特、掀起反戰運動的美國越戰逃兵和五月風暴的浪蕩兒們,其思想內涵所代表的乃是對自身所必須肩負的家庭、社會責任之反抗,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會對其的哺育,卻不想受對應義務契約的拘束,同時還想得到更高尚的名聲,於是就提出了一種不需要個體付出責任、卻可以得到更好名聲的新道德。
在2015年的中東難民危機中,不同道德觀秉持者的不同意見和相應遭遇,實際上就體現了白左道德相比於傳統道德的無成本優勢:主張無限接受穆斯林難民的白左人士,本身並不承擔相應的安全、經濟和社會之長期責任,卻能夠順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這種施他人之慨的背後是對國家、社區和家庭毫無責任感;而對家庭、社區和國家懷有強烈責任心的傳統價值觀秉持者,卻不得不擔憂隨之而來的威脅,而且還被抨擊為「納粹」或者「法西斯」的惡名。
事實上,相比於貧困的本國民眾,白左人士之所以更熱衷於關注中東難民,並非源於他們的高尚,而是因為關心前者只是一種傳統價值觀中需要長期履行的枯燥義務——即便長久的付出也很難被視為高尚,而對遠方毫無瓜葛的中東難民進行關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裝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種通過極低成本賺取名聲的道德捷徑。因此,某些違背常理的現象變得順理成章:越是遠方的無關之人(物),越能夠得到白左人士的關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難受到白左人士的關注。

著名的白左人士安吉麗娜對她需要長期盡責的親身父親極為冷漠,卻熱衷於即興扮演難民大愛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與傳統道德偏重於默默無聞的長期付出相比,白左道德更偏重一時興起的順手施為和精心策劃的修飾擺拍。
在傳統價值觀看來,沒有長期具體瑣碎的付出和對家庭社會責任的承擔,個體幾乎不可能成為傳統價值觀下的道德模範,所謂君子之德,「訥於言,而敏於行」,即使如此。
但是,白左的道德則完全不同。無論從各個方面來看,盧梭的真實人生都與道德無關,但是這位偉大的修辭作家能夠通過感人至深的愛情小說《新愛洛伊斯》把自己刻畫為忠貞不渝之人;平心而論,薩特的責任感是極為短暫的,他可以在走下一個情人的香床之後,馬上給另一個女人寫情書,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則能夠將這種動物一般的性行為描述為充滿時尚意味的「存在主義愛情觀」,甚至以此將自己和西蒙娜的淫亂修飾成令人欽佩的愛情典範;與之類似,逃避越戰兵役的美國青年們則將自己的怯懦構建成對和平的嚮往,並大肆包裝;法國五月風暴的青年們同樣如此。

事實上,白左人士或許缺乏真正的責任感和勇氣,但卻從來不缺乏對鏡頭語言和修辭手法的把控能力(逃避兵役的美國青年在恢復秩序的美國軍隊面前)
白左道德:文明癌症的表象
傳統道德則要求踐行者承擔對家庭、社區的責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付出。也只有在各個成員基於傳統道德進行付出的基礎上,家庭才能美滿,社區才會發展,文明才有可能進步。這也是傳統道德雖然枯燥無聊卻經久不衰的關鍵。
不過,白左道德所起的作用則截然相反。作為一種低成本的道德,白左道德為那些不想做出長年累月的付出,卻貪戀名聲的聰明人提供了絕佳的登榮之梯。這種道德本質上是一種對社會道德資源進行透支的騙術,即投機取巧者通過鼓吹至高的道德口號,讓所在社區中的其他人承擔由此引發的負擔,然後自己從中賺取最好的道德名聲。
與懶惰之人鼓吹不勞而獲的極端福利政治一樣,白左道德本質上是一種自私之人宣揚不勞得譽的欺詐。如果極端福利政治是對勤懇踏實之人的剝削,那麼白左道德則是對老實敦厚之人的矇騙。因此,一個施行了福利政治的國家,消耗的是他人對國家的貢獻,勤勞的人將越來越少;一個踐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區,透支的是他人對社區的感情,虛偽的人會越來越多。
今天的西歐社會,普通民眾之所以不敢站出來反對難民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丟自己的臉,這本質上說明其對親人、家庭、社區和國家缺乏責任心。
因此,無論是極端的福利社會,還是白左道德,都是一個文明走向衰微時,才會出現的產物,即社會個體變得:只在乎自己的財富和名聲,而不在乎家庭、社區的前途;只考慮自己的所得,卻不願意做相應的付出。在這種氛圍下,文明的財富和力量就會逐漸枯竭,並終歸寂滅。
魏晉之禍
五胡亂華前夕,中原士人逐漸喪失了兩漢期間的使命感,其領袖人物大多對社會責任和傳統道德不屑一顧,「越名教而任自然」,通過肆意妄行而相互標榜。
名臣何晏喜歡吸毒;竹林七賢阮籍的母親死前拒絕見母,反而強求別人與自己下完棋;七賢之一的劉伶,熱衷於縱酒。然而通過巧妙的修辭和標榜,這些人反而獲得了傳統道德堅守者難以向背的名聲,吸毒的何晏被視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計程車林領袖;阮籍則被譽為「禮豈為我設邪」的非俗之人;劉伶成為了「縱意所如」的豪士。
實際上,魏晉風流之後的荒誕作為,本質上不過是自我放縱。而「非湯武而薄周禮」的大義、「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僅僅是精於標榜者對自己放縱作為的美妙標榜。

魏晉人士喜歡相互標榜,王戎讚美王衍(著名清談家,西晉的亡國宰輔),「(當世)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王敦則稱頌自己的堂兄:「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晉書·王衍傳》
1917年的俄國「一號命令」
二月革命期間,為了贏得道德至高點,戰勝立憲自由黨,在左翼領袖克倫斯基的支持下,俄國蘇維埃會議執行主席索科洛夫頒布了「一號命令」,命令允許,「俄國士兵可以拒絕軍官的指揮」,「士兵的武器由士兵委員會掌管,軍官無權過問」。
在這一命令的推動下,很快俄國軍隊就陷入了癱瘓。軍人從剛開始的胸口幫著紅繩,到後來的敞開軍裝,再到後來變成劫掠的土匪,俄國秩序與她的軍隊一起陷入了癱瘓,最終形成了臨時政府崩潰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天敵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惡行,但沒有一種比破壞道德的惡行危害更大,白左對社會的摧殘作用即是如此。
強姦、殺人、搶劫、詐騙僅僅只是違背了社會道德,但白左則是摧毀了社會道德本身。通過對自私的巧妙修辭和誇張,白左人士往往能夠把自己不付出任何代價的廉價表演,包裝為至高道德的體現;通過對家庭、社區價值觀的肆意攻擊,白左士人常常將這些最基本道德倫理塗抹成對個性的壓迫和牢籠。由此滿足那些投機取巧並自私愛名的聰明人,以及一心向善卻單純膚淺的蠢材,最終摧毀調一個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基礎。
一個真正理解文明價值的人,必然能夠清楚洞曉犯有此類惡行之人對社會的巨大危害。
公元前496年,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任魯國大司寇,上任七日後就將魯國「聞人」少正卯誅殺於東觀之下,暴屍三日,學生不解孔子的作為,孔子解釋道,此人(少正卯)有以惡言善(五惡)、破壞世風的「小人之桀雄」,故而非殺不可;東晉名將桓溫則將五胡亂華中原淪陷的悲劇歸咎於西晉末年士林風氣的敗壞,稱「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王衍,西晉士林領袖,擅長清談和自我標榜)
事實上,一個文明的進步和繁榮,不僅僅有賴於她物質力量的強大,更有賴於正常的道德倫理。一個鼓勵好吃懶做的社會,是不可能進步的;一個嚮往虛幻美好的文明,是不可能維繫的。就像魏晉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標榜一樣,出於自私的白左道德本質上是文明的愛滋病,她將摧毀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並使得微末小疾發展成不治之症。
所以,批判白左,不僅僅是對白左的抨擊,更是對文明本身的拯救。畢竟,白左的勝利就是文明的失敗,白左的失敗就是文明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