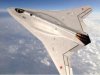839年,法國作家阿斯托爾夫·德·屈斯蒂納探訪俄國。他最初對這個國家興趣盎然,但最後發現,「在俄國,專制只是在御座上,但暴政卻遍及整個國家。」於是,他寫了《俄國來信》一書吐糟「野蠻俄國」,使得俄國政府十分惱火,將此書封禁。
19世紀上半葉,自由旅行還是一件稀罕事,人們對異國的了解多半來自書本和道聽途說,還有各種想像。也正因此,那些親身探訪顯得格外珍貴。
屈斯蒂納曾說:
「對於我來說,旅行從來不是時尚,而是與生俱來的愛好,而且我從年少時便開始滿足自己這種愛好。我們大家都模模糊糊地受著一種欲望的折磨,想要了解這個在我們看來如同牢獄的世界,因為我們自己並沒有把它選作居所。要是沒有把我的牢獄努力地探索一番,我覺得我不會平靜地離開這個逼仄的世界。我越是探究它,它在我的眼裡就越是美麗遼闊。『為知而看』,這是旅行家的座右銘,也是我的座右銘。這話不是學來的,它天然就在我的心中。」
將世界視為牢獄,顯然與窒息的童年有關。阿斯托爾夫·德·屈斯蒂納出生於1790年,正是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的父親被處死於斷頭台上,他與母親僥倖在恐怖殺戮中倖存。他於1857年去世,正是第二帝國時期。
屈斯蒂納最著名的兩部作品都是遊記,分別為《斐迪南七世統治下的西班牙》和《俄國來信》,在《俄國來信》中,他以大革命時代敏銳的法國人視角,對沙皇俄國專制制度的根源和特點進行了分析。
屈斯蒂納的總結非常精彩,與其說是描述俄國當時的現實,不如說是這片土地的宿命。他寫道:
「總之,所有能讓組織良好的社會具有價值和魅力的東西,所有能讓政治制度具有意義和目標的東西,在這裡都消失了並混淆在一種單一的心理中,那就是恐懼。在俄國,恐懼代替了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恐懼讓思想麻木了。」
他繼而分析道,這種心理在單獨處於主宰地位時,只能造成文明的表象,因為恐懼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的推動力量。
「它不是秩序,而是掩蓋混亂的外衣。缺少自由的地方必定也缺少熱情和真理。俄國是一具沒有生氣的軀體,一個只靠頭顱活著的巨人;至於它的四肢,已經全都失去了力量並在萎縮。這就造成一種深層的焦慮,一種難以言表的不安。」
作為經歷過法國大革命跌宕的人,屈斯蒂納當然會將這種不安與法國聯繫在一起,認為它「就像法國的新革命者的不安一樣,不是源於思慮的模糊、傷害、物質繁榮的饜足或者不同力量的結盟所引起的嫉妒心理,它表現的是真正的苦難,反映的是根本性的弊病。」
儘管當時的法國人也不算幸福,但屈斯蒂納坦言:
「我們自己也不幸福,但我們覺得幸福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可在俄國人當中,它卻可望而不可即。」
對於俄國的遠景,屈斯蒂納也進行了預判,認為它是一大鍋沸水,蓋得嚴嚴實實,卻放在燒得越來越旺的爐火上。他還不無譏諷地提出建議,認為俄國統治者「在製造出受到民眾愛戴的表象之前,他該先製造出人民來。」
屈斯蒂納的俄國之行始於1839年,此舉受到巴爾扎克的鼓勵。不過當時更主要的刺激來自於托克維爾,後者在1835年出版《論美國的民主》並獲得巨大讚譽。托克維爾在書中不情願地承認美國模式在當時的先進,同為貴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納則表示懷疑,想通過俄國與美國之間的比較來否定這一觀點。
1839年的俄國,正是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此時的俄國在國際地位上已經達到歷史頂峰,對外強大、內部穩定的假象足以忽悠不少人,最初的屈斯蒂納便是一個例子。在歐洲,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的保守派都對俄國沙皇大肆吹捧,認為他達到了「復古的極致」,維護了君主的權威和內部穩定。保守派也習慣以它為例子,反對美國的代議制。
那年7月10日,屈斯蒂納抵達聖彼得堡,8月3日到達莫斯科,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國總共呆了不到三個月,他不會說俄語,而且旅行中一直被政府官員「保護」並監視。但他仍然寫出了一份長篇旅行記錄,以三十六封信來呈現自己的俄國之行,也因此被稱為「俄國的托克維爾」。有趣的是,屈斯蒂納最初是打算在俄國尋找反對美國式代議制的證據,結果卻被沙俄的專制腐敗所震驚,結果反而成了最激烈的沙俄體制批評者。
1843年,《俄國來信》在巴黎出版,隨即被搶購一空,此後不斷再版,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赫爾岑曾稱《俄國來信》是迄今最為了解俄國的著作,20世紀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則稱其為對俄國的最佳描述。
許多細節都暴露了沙皇專制下的俄國是何等腐朽,但最可怕的不是腐朽本身,而是民眾對這種腐朽熟視無睹,認為統治者的特權、自己所受的壓迫都是理所當然。比如屈斯蒂納在書中寫道:
「在彼得堡和諾夫哥羅德之間,我注意到連續幾個路段都有與主路平行的輔路,雖然離得較遠。輔路上橋樑什麼的都有,安全和通行沒有問題,只是遠沒有大路那麼漂亮和平坦。我問驛站老闆這是怎麼回事,他通過我的憲兵回答我,小路是在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員去莫斯科時給運貨馬車、牲口和旅行者走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如果大路對公眾開放,灰塵和障礙物給尊貴的旅行者造成的不便和妨礙。我搞不清楚店老闆是不是在拿我開心,但他說話的樣子一本正經,似乎認為在一個君主就是一切的國家,君主獨占道路理所當然。」
當時在位的尼古拉一世,極力扼殺自由思想,以絞刑架和流放對付所有異議者,書報檢查制度十分嚴苛,秘密警察遍布每個角落,人們無法表達思想,「交談就是密謀,思考就是造反,況且思想不僅僅是一項罪行,它是一種不幸」,政府則靠謊言活著。
這當然跟俄國的歷史有關,它從未真正與文明接軌,只有野蠻擴張。統治者色厲內荏,內心懼怕所有自由與開放的東西。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大手筆」,在屈斯蒂納眼中也是可笑的。他寫道:
「我步入涅瓦河兩岸的彼得堡歷史上的心臟地帶,被海軍部大廈和總參謀部的莊嚴宏偉所震懾——這些建築讓我想起彼得大帝最初的意圖是建設一座堡壘來保護港口。但是,在一條每年封凍八個月的河流兩岸設立海軍基地和貿易基地,這是荒謬的,或者說是令人絕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羅的海貿易路線的入口,便將他的新都設立在俄國薄弱的西北邊境。」
一開始抱以期待的屈斯蒂納最終發現,沙俄是一個非常畸形的國家,人們崇拜強權,盲目排外,民眾對自己糟糕的生活狀態並不在意,卻很在意沙皇對外的窮兵黷武是否能夠獲勝,他們可以對任何官吏下跪,毫不在意尊嚴,但同時又有著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認為其他歐洲國家都是等待沙皇「雖遠必誅」的敵人。「在這裡,暴君和奴隸之間、狂人和野獸之間沒有什麼區別。」
有一段對俄國民眾的總結非常貼切,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在一個因為恐怖而變得鐵石心腸的民族當中,寬厚仁慈被稱為軟弱。嚴酷無情讓他們卑躬屈膝,寬恕則使他們抬起頭顱。他們可以被征服,但沒人知道怎樣讓他們信服。他們沒有驕傲的資格,卻依然膽大妄為。溫和的,他們反抗;殘暴的,他們服從;因為他們把殘暴當作力量。」
對於屈斯蒂納來說,最初對俄國的「濾鏡」在短時間內便被擊得粉碎。不過這並非壞事,因為這反過來加強了他對自由的認知。沙皇的專制,還有對個人自由、尊嚴與權利的踐踏,都讓他明白一點:相比野蠻,文明即使有再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也仍然可貴。
在歷史上,曾經被表象蒙蔽的知識分子很多,他們會誤認為某些政體或組織是人類文明的答案,於是飛蛾撲火一般湊過去,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屈斯蒂納這樣看清並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