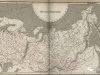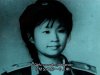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這二者是不同步的,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宏大敘事中被拋在一邊。
從涅恰耶夫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那麼「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因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的」。於是,政治上的輕率與摒棄道德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為放棄自我完善的道德淪喪找到一個最冠冕堂皇的藉口。怪不得還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就稱涅恰耶夫「原來是個普遍的流氓」。
廣場式的譁眾取寵的激進比賽,很容易造成更純樸、更敢作敢為的印象,對於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來說,總是願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災難和外部的強力聯繫起來,對於現狀總是存在著一種絕對完整的觀點,這種心理習慣於推卸掉個人責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眾運動中快速翻身,於是「印象主義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離開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熱的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政治激進派,而這些人恰恰不是從民族國家的長遠發展著想。
俄國為暴力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斷層是無法想像的,革命打碎了舊世界,同時也毀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積累,新世界只能在蠻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築。
▌君子總是鬥不過小人
俄國革命的實踐表明,凡是那些關心道德操守,認為任何政治鬥爭行為都應該具有道德底線的人,都被認為是「書呆子氣」,這也是區分政治激進派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重要標誌。不講道德的人與講道德的人競爭,永遠是前者勝出,這是一個規律。
早在1917年時孟什維克李伯爾就說過,不是群眾追隨政治激進派,而是政治激進派追隨群眾,他們沒有任何硬性的綱領、沒有底線的原則,對群眾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們往往對工人說,他們的要求是辦不到的,而政治激進派卻對他們百依百順,我認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綱領有原則的人,而那些沒有綱領、贊同人和群眾口號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其實,誰都知道「革命」這種宣傳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顛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後,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權威和規則,而且是更嚴酷的更鐵腕的統治,否則道德淪喪的惡果很快便會降臨在「以惡達到善」的弘揚者身上,因為如果任其泛濫,每一位宣揚者都會成為它的犧牲品。
個人的道德素養、自我完善、操守品德與社會運動不能脫離,很難設想一個缺乏高貴心靈、在日常瑣事中沒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為了崇高信仰不惜犧牲個人,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倒要懷疑目的真實性了。
而且在「以惡達到善」的實施過程中,惡行任其大泛濫不被譴責,不擇手段成為相互追捧法則,即使達到了目的,「向善」的社會的道德規範已被破壞殆盡,這種「理想社會」即便實現了又會是一種什麼景象呢?
俄國革命導致原來知識分子最為稱道的道德觀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國積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壩頃刻間坍塌。由於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們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鄙視,「民眾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最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眾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隨後再也不能提供任何東西了」。
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看起來轉化為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後,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卻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有益的東西。
存在的只有兩種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復歸後又一次輪迴到專制制度,在民粹派「為民謀幸福」的假象背後,不過是少數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種手段,人民根本不是社會的主人。
但更可怕的是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被徹底顛覆。「惡」成為一種制勝法寶,心慈手軟者都會成為最早的出局者,這種「善良淘汰機制」甚至比它所顛覆掉的舊體制更糟糕、更可怕。
道德虛無主義者在走上這條不歸路之後,就只能把世界分為紅黑兩個陣營,非此即彼鬥爭便成為一種常態,只能以嚴酷的鎮壓體系、恐怖手段維繫凝聚力,以強化集中制、等級制、兵營制的高壓職能來對待異端,在這樣的社會中,真誠、相愛、善良、仁慈、溫情都將被掃進「資產階級的垃圾堆里」,在這種道德時尚的主宰下,人性惡的一面會大大釋放,大家都在比誰比誰更流氓,在這種社會風氣中只會距離理想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