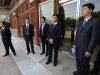十年砍柴
我們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條僅僅遮住下體的褲衩外,都光腳、赤膊。太陽把瘦瘦的我曬成非洲黑孩子,腳板踩在發燙的青石板路上,時間長了都失去了感覺。黃昏,太陽落山許久,牛們還不願意歸欄,死乞白臉地賴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後好些時候,牛才冒出頭,鼻孔忽忽地往外噴水。人和牲口都很煩躁,只有晚飯後,我脫光衣服,躺倒門前淺淺的溝渠里,才覺得有一絲涼快和安寧。西邊天地庵水庫垻上的大馬力抽水機沒日沒夜地抽水,經過溝渠灌溉著一丘丘渴極了的禾苗。流動的水,是潔淨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塊石頭,頭露在外面,水從脖子開始,順著肚皮趟過,輕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雞雞處在十分自由放鬆的狀態,在流水的撫摸下,悄悄地起了變化。仰看滿天的星斗,它們眨著眼睛看著我,耳邊只有流水的聲音以及蛙鳴,四野安靜得很。偶爾有一聲奇怪的呼喚,疑心在喚我,想起爺爺給我講過的許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喚他的名字,如果一答應,魂兒馬上就沒了。於是無論怎樣也不答應,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靜有一天被山外傳來的恐慌打破了,聽說北方很遠的地方鬧地震,死了很多人。我們那裡的人只經歷旱災、水災、山洪等等,沒有誰見識過地震。於是這地震越傳越可怕,好像就在你面前有一個魔鬼張開血盆大口。有老人說這是地底下的龍不安分了,龍一動身子山就倒下了,地開裂巨大的縫,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這條龍吃了。我總覺得水庫四周山裡的大岩洞中間,藏著這樣的龍,它要是生氣了,就會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裡?連爸爸媽媽和大隊書記都沒去過那裡,只有我二伯的三兒子運哥知道確切的位置,他剛剛復員回家不久。他在石家莊當兵,我從來沒聽說的地方。復員時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圍觀,他穿一身沒有帽徽領章的草綠色軍裝,從一個黃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發兩顆。回家後媽媽聽說我和弟弟比別的孩子並沒有得到優待,有些生氣地說他當兵你爸爸給找了公社武裝部長,不然哪去得成?也是兩顆糖,真不知道好醜。後來有隊上的人問他用的是什麼槍,他憨實地說,部隊幾年,除了新兵連三個月摸過槍外,就一直在當炊事員,餵豬、做飯。去那麼遠的地方餵三年豬?有人說划不來,也有人說見見世面總是好事。不過對運哥來說最大的收穫是,許多人家辦喜事,找他去幫廚。
地震越來越說越玄乎,有人說天老爺要來收人了,也有人說乾脆把豬宰了,好好地吃幾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隊幹部終於站出來了,開大會告訴社員們,地震並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離我們很遠。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學會預防。於是社員之間相互傳授了許多地震的土知識:比如井水突然變渾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填油加醋,弄得荒誕不經。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這是平時開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隊長的手裡。原來當隊長的華阿叔,他家的母雞半夜打鳴,他覺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喚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衛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聽到哨聲,姐姐自己爬起來了,我和弟弟被媽媽喚醒。我記得媽媽還沉穩地為兄弟倆穿上厚厚的衣服,後來她說聽人講地震後天會變得很冷,所以讓我倆多穿衣服有備無患。
一家人從屋裡出來,往東邊的茅屋山走,聽說地勢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後龍口裡噴出來的水淹不著。全村的人都往哪裡聚集,大人喊小孩鬧,亂成一團。我提著我家的煤油燈,走在前面。覺得後面真有個野獸來追我似的,跑得飛快,將媽媽、姐姐和弟弟拋在後面。當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時,我還不知疲倦地往山頂上沖,似乎只有山頂才安全。媽媽在後面大聲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讓我止住腳步。
當然是一場虛驚,天麻麻亮的時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隊長的冒失,說白白地浪費了燈油,耽誤了困眼閉(我家鄉睡覺的說法),強烈要求隊長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剛過,又傳來了一則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死了。
那是一個的黃昏,天氣還很熱,西邊是紅紅的火燒雲。我們這些小孩還穿著小褂子、短褲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學讀書的全叔叔回來了,穿一件紅色的跨籃背心,挑一擔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挑水,經過村口時,和村口臭椿樹下納涼的酉爺爺說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亂講,這樣的話能隨便講的!你想吃牢飯了?」酉爺爺一陣驚慌,說道。
「不是亂講,鄉里廣播裡廣播了,我們老師也講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嗎?他去了,誰來管我們?」酉爺爺提出疑問。
「全老滿,你肯定是亂講,毛主席怎麼能死的?他老人家是萬歲,是長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們聽說這話,也不敢相信。回去問媽媽。媽媽說:大概是真的,這樣的話沒人敢亂講,除非他不想要吃飯的傢伙了。
大隊的大廣播裡面終於證實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紅最紅的太陽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裡,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鑾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爺爺一樣的毛爹爹,就是掛在堂屋正中間的那張像,下巴有一顆痣,村裡的老人說,毛主席就是這顆痣生得好,是菩薩相。我們小孩最先認識的字就是生產隊隊部牆上用石灰寫的幾個大字:「毛主席萬歲」,我們會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太陽升」。我們村里一個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語錄的報紙剪鞋樣,被發現後,大隊幹部說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腳底下。她被抓住遊行,鬥了個半死。
接下來,公社和大隊都開始辦喪事。大隊的靈棚扎在小學校的操坪里,有大人從山上折下來的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會上有幾個貧農代表聲淚俱下地講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個老太太哭著哭著就暈過去了。
再接下來大隊開始部署基幹民兵荷槍實彈站崗放哨,對地主、富農等四類分子嚴加看管。走親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確實需要外出的,必須憑大隊部開具的路條。由於我爺爺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這裡設卡盤問過路人。有一個挑擔子的中年人被擋住,沒有路條,不讓他過,他講自己的成分是貧農,是哪個公社哪個大隊的社員,叫什麼名字,去哪裡幹什麼。沒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個後生跑到他所說的大隊核實無誤後,才開具已盤查的證明放行。
生產隊保管員的二兒子,一個字寫得不錯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門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畫一個長方形的黑框,框框裡用墨寫幾個宋體字:「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許多家門口這些字還在,也算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了。
在那個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紗的供應好像不受限制。根據家裡的人口,除「四類分子」和沒有上學的小孩外,其他人每人一個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沒有上學,所以不發給黑箍箍,心裡很不高興,覺得自己受到了歧視,纏著媽媽要黑紗。媽媽沒辦法,只好從家裡拿出黑布,給我們兩人做了兩個黑袖章,我根本意識不到什麼悲痛,只是覺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學孩子一樣的待遇,便覺得虛榮心得到了滿足,而且那些日子有鬧熱可看。
上學的哥哥和姐姐回來後說,毛主席逝世後,他們最不習慣的是,每節課上課前,老師都要他們站立、低頭,默哀三分鐘,天天如此,厭煩了。媽媽告誡他們,此話只能在家裡講。
又是一個深夜,已是深秋,天氣比夏夜涼多了。我們又被隊長吹哨子吵醒,告訴有重要事情。媽媽起來點亮煤油燈,我也睡不著,非得跟著她出門看熱鬧。
這次不是鬧地震這樣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訊。隊長帶領幾個人在我家屋後面,挨著生產隊烤菸房空地上,敲鑼打鼓,說是剛跟著大部幹部,連夜從公社接來了寶像,讓社員同志們請到家裡,馬上貼到牆上。
每家都是兩張寶像,回家後在油燈下。一張寶像我認識,胖胖的頭像,梳著賓士頭,嘴下面有一顆痣,這是剛剛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張寶像,同樣天庭飽滿,同樣雙目炯炯,只是理了一個平頭。看起來和毛主席長得差不多。
媽媽告訴我:這個人是華主席。
我問華主席是誰?
媽媽說毛主席死了,華主席來接腳的。
我打破砂鍋問到底,什麼叫「接腳」?
媽媽有些惱怒地說:原來毛主席當家,現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讓華主席當家,接著毛主席來管我們。
原來如此,但我還是似懂非懂。從來沒見過毛主席和華主席,他們怎麼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媽那樣能每天早晨拿著攪拌豬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來去放牛。
寶像回家不過夜,媽媽把堂屋正面原來貼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掃帚掃乾淨,熬一小鍋稻米糊糊,恭恭敬敬把兩張寶像貼上去。從此每天經過堂屋,就看到兩個人眼睛盯著我,似乎在問我,今天做沒做壞事?
過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學回家,高興地說,這幾天又不用上課了,去學校演戲,遊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學校就停課參加政治宣傳活動。
聽上初中的哥哥說,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
四人幫是四個人,三個男的一個女的,簡稱王張江姚。什麼叫粉碎?哥哥說用鐵錘敲一個土坷垃,一敲就碎。什麼叫「一舉」?哥哥說就是舉起拳頭。華主席一個人伸出拳頭,就把四個人打得粉碎,好厲害喲?那段時間,華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麼領導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熱鬧看,我當然不會放過。在家我還埋怨那一年媽媽為什麼不送我上學?本來秋季開學時我纏著她要去報名,後來小學裡的老師說,五歲,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還在小學校。小學校離我家兩里地,姐姐哥哥們帶弟弟妹妹上小學校,是當時很正常的場景。小學校剛修建後,哥哥在這裡讀了五年級,那時還沒有課桌,一塊木板用磚頭架起來,每人從家裡搬來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幫時,學校已經有了統一製作的桌椅。我家山區多樹木,大隊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沒什麼難的。老實說,直到我前些年做記者去西部某些省區採訪時,看到一些鄉村學校還不如我記憶中家鄉的小學校。
學生們在操場上先是開會,然後呼口號,什麼「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類。開完會就遊行,遊行打著紅旗,繞七個生產隊的居民點轉一圈,一路上小學生呼口號,背毛主席語錄,什麼「排除萬難,不怕犧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部帶了頭,群眾有勁頭」之類。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高年級學生,舉著標語和畫像,那畫像是學校老師畫的王、張、江、姚的頭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禿頭,有的像老巫婆。
我記得很清楚一幕,遊行隊伍到了一個村莊,一個老頭指著江青的漫畫像說:真是怪事,長得這樣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棄,娶了做婆娘。給我我都不要。
遊行慶祝完了以後,學校開始排戲。每個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幫,那些不聽話的調皮搗蛋鬼,被老師說成是四人幫一類的人物,演戲時站到講台前面,面對全體同學,分別飾演王、張、江、姚,弓著背,下面的學生裝革命群眾,控訴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幫的戲演完後,學校老師排演《園丁之歌》,說的是一個後進生不聽話,貪玩,後來在老師的教導下發奮學習的故事。這個戲有情節,難度比較大,非小學生能信任的,學校的幾位民辦教師親自塗抹油彩上場。大隊書記的兒子,我叫斌叔叔的,剛代課半年,長著一張娃娃臉,他飾演那個不聽話的刺頭學生,拆了算盤珠子,做玩具火車的輪子,我的親嬸娘,嫁給我在縣城工作的叔叔好幾年了,也是民辦教師,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師。
那兩年,孩子們跳橡皮筋的歌謠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開門,一舉打倒王洪文;……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一舉打倒姚文元。」我當時疑惑非常,為什麼撿到一分錢,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這些歌謠究竟是何人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