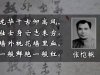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創造了畝產干谷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豐產記錄。這塊早稻長得密密厚厚,孩子們站在上面就像在沙發上似的。新華社記者 于澄建攝
對於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幕幕戲劇,村裡的老人們爭論頗多。
2009年12月上旬,正午的龔家埠村。
2009年,龔家埠普通農家的廚房。
2009年,龔家埠普通農家的廚房。
饊碗鹵—三萬六:尋訪「天下第一田
龔家埠村就在路邊上。從武漢到麻城兩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原本以為要找到當年的那個小村子會費很大週摺,甚至可能要翻山越嶺,但實際上很順利。一到麻城就看到了往白果鎮的路牌,沿著路牌指示的方向走不多遠,還沒到鎮上,就看到了「龔家埠村」的牌子。這裡就是原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早稻田畝產 36956斤的「神話」就誕生在這裡。
頭一天我們打聽行車路線的時候,一位對當地比較了解的同行曾對我們說,龔家埠村應該不會離大路很遠。他的理由是,51年前就這麼出名的村莊,絕對應該位於交通便利的地段,誰會在偏遠地區樹立一個典型呢?那不是給前來視察的領導找麻煩嗎?
現在看來,人家分析得有道理——龔家埠村鼎盛時期,周恩來總理都來過呢!
把車停在路邊。路邊是一戶挨著一戶的村民的房子,風格樣式都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一個院子,房子的大門衝著院子開著,人坐在院子裡,聊天或者做活兒。我們問路的這家,正在踩縫紉機,是一個中年婦女,看樣子五十多歲。
翻出那張當年新華社記者于澄建拍攝的「天下第一田」的照片,四個孩子站在豐收的稻子上,天真爛漫的笑著——大嫂一看,脫口而出:「饊碗鹵」!
「饊碗鹵」是「三萬六」的方言表達,我們當時還覺得這位大嫂很善於「歸納」,否則我們得費好多口舌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現在人家一個「饊碗鹵」就把當年「天下第一田」造假畝產三萬六千斤一事概括出來了。後來,我們到了村子裡,才發現,幾乎每一個碰到的人,在看到照片的時候,都會說「饊碗鹵」。「饊碗鹵」在當地已經屬於「地標性」名詞。
大嫂說她知道「饊碗鹵」,但不知道照片中的這四個小孩。她建議我們去找龔安伯的老婆問問,龔安伯做過公社領導,已經過世,他老婆還健在,應該對當時的情況比較了解。
龔安伯的老婆住在村子裡。車開到村頭,遇到一位老漢,他看一眼照片,也是一句「饊碗鹵」。他說他那時候歲數小,知道這件事情,但不知道照片中的孩子是誰,他聽說我們要去找龔安伯的老婆,立刻自告奮勇帶我們去找她家。正是中午,老太太家鐵將軍把門。老漢帶著我們滿村找——幸虧村子很小,村子裡的人也都認識,路上隨便問了幾句,就問了出來。老漢告訴我們,龔安伯家在村子裡很有名,見過毛主席的。
龔安伯的老婆60多歲,精神矍鑠,比普通農村婦女要顯得見過世面。她看了一眼照片,就先問我們來做什麼?我們說就是想知道當年照片中的四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她說她不知道,這個事情不是他們家搞的。那個時候,他們家不在村里,在武岡。她一再強調,她老頭是不會搞這種弄虛作假的事情。
我們問她,村上有沒有能幫助我們找到這四個孩子的老人?她帶著我們去找了一戶,去的時候人家正在吃飯,只看了一眼照片就搖頭,說:「不曉得」。
怎麼可能?當時那麼驚天動地的一張照片,而且這張照片就在這個村子裡拍的,而且因為這張照片,整個村子成為典型,絡繹不絕、川流不息的領導、專家來此取經參觀,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怎麼可能現在整個村子裡,竟然沒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四個孩子是誰?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村裡的人對照片所拍攝的地點也出現了爭議。
龔安伯的老婆一口咬定,照片拍攝於「陸」棵樹——她把我們帶到51年前的「事發現場」,指著前面一處一棵樹都沒有的光禿禿的開闊地說就是這裡。當年村口有六棵樹,其中一棵就是照片中的這棵。邊上其他村民也紛紛跟著說「是」。
人越圍越多,每個人都伸頭看照片,都說「饊碗鹵」,但都不知道照片中的四個孩子——如果是村子裡的孩子,怎麼會看不出來?照片中兩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就算女孩子遠嫁了,但男孩子總歸還是留在村子裡的吧?
後來,一個60歲左右的老漢說,照片中的男孩子好像是他哥哥龔正堂。我們立刻歡喜地跟著他去——穿過村子,村子裡的池塘很髒,有一婦女拎著一桶衣服,正在池塘邊上找下腳的地方,她大概只能用這麼髒的水吧?否則,但凡有選擇,誰會在這池塘里用一池臭水洗衣服?
龔正堂對「饊碗鹵」印象很深。那時候他是中心小學四年級學生,「衛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車子50多輛,震撼了全世界。來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飯,讓我抱一個大南瓜,還抱不動。周總理戴著白帽子,像廣東人(裝束)。蘇聯專家跟我說話,我不懂,邊上的人告訴我他是說『你好,叫你握手』。蘇聯專家的手很大,長滿了毛,我一隻手上去握,只握住兩根手指頭,兩隻手只攥了四根手指頭。心裡怕得要死。」龔正堂說的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到村子裡拍紀錄片的事,他還記得當時把小孩搞到田裡,但是,當問到他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時,他說:「我沒得拍這個照片的印象。」
那時候,整天村子都很熱鬧,他還是個孩子,用他自己的話說「糊裡糊塗」的,可能被拍了,也可能被拍的不是他——他反覆看那張照片,最終搖頭,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周圍有人說很像他小時候,我們問他有沒有小時候的照片,他說沒有。
根據他的回憶,「天下第一田」是一個叫王乾成的社主任搞的,搞好以後,樹立了典型,很多蘇聯專家都來參觀,他們當時認為中國人不懂數學,不會算術,一畝地產不了三萬六,一定是算錯了。但是村子裡的人沒有人去懷疑這個事情,大家只是很高興能有這麼多人這麼多領導來村子裡,周總理都來過,還拍電影。關於當年的「天下第一田」,龔正堂還記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後發生的「飢餓」。「1959年就餓了,草籽樹皮都吃。那樹皮吃進去,三天拉不出來,快要死了。去向周圍村子裡借,人家講:『你們那裡『饊碗鹵』,還到我們這來找水找東西,根本不跟我們講話。一直到1962年,還有人埋怨。現在沒有人提這個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記這個事情。」
龔正堂儘管無法確認自己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但他可以確認一點,就是照片並不是拍攝於所謂的「六棵樹」。他說「天下第一田」在村子後面的壪子裡。他撂下碗筷,帶我們穿過村子,去找他印象里的「天下第一田」。經過一戶人家,門牌號「龔家鋪村龔家埠壪9號」,他說這裡當年是祠堂,他就是在這裡見到的周恩來總理。不過,現在祠堂沒有了,拆掉了。
終於到了當年的「天下第一田」——地全荒了,幾頭牛在地里散步,龔老漢說:村子裡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兒子在廣東,女兒出嫁了。所以地就沒有人種了。
1958年10月4日,刊載於《人民日報》上的木刻畫「迎接大豐收」。作者:黃永玉
這塊曾經熱鬧一時的稻田,如今已很少有人問津。
這塊曾經熱鬧一時的稻田,如今已很少有人問津。
望著眼前這塊長滿了雜草的稻田,很難想像它就是1958年8月間名聲大噪的畝產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51年過去,當年站在水稻上,與龔正堂同齡的孩子們也已從少年變成白頭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很自豪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很自豪,但後來就覺得這有問題。」2009年12月3日,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鎮龔家埠村(原麻城縣建國一社),端著飯碗的龔正堂在自家磚土結構的房屋前回憶起往事。
「那的確容易讓人自豪!雖然社員中也有想不通的,但後來就被幹部們說服了。」龔正堂回憶到。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圖文報導,轟動一時。
根據歷史資料,三萬六千的衛星一放,建國一社先後接待了各地的參觀訪問者10多萬人次,其中還有朝鮮政府代表團,蘇聯、東德、波蘭、越南等國家的專家學者。
周恩來總理也來了,龔正堂在祠堂的大門口見到了周總理。電影製片廠也來了,龔正堂當時專門負責給拍紀錄片的劇組送開水、送飯。
當年的報導詳細地描述了天下第一田的練成術:「據了解,這塊田整地共達十次,深耕達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後施用的肥料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擔、陳磚粒四百擔、硫酸銨一百零五斤......在驗收時,人們曾選一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結果推算,平均每畝約有七百六十八萬穗。把雞蛋隨便地放在上面滾動,雞蛋始終不會掉到田裡去。可見這塊田的稻子密集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一年後有人餓死
「自豪」沒有維持多久,建國一社人開始嘗到了「畝產三萬六千斤」的苦頭。
來自省內外、國內外的參觀者蜂擁而至。當時,麻城縣委指示:對參觀者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許怠慢客人。於是沿途十餘里,路邊都是招待吃飯的指示牌。一時間路上人不斷,灶里火不停。社員們不得不放下手中農活,敲鑼打鼓前去迎接參觀的客人。
河北垸的糧食吃完了,社裡大車小車趕忙送;雞鴨豬羊殺完了,縣裡怕怠慢全國各地參觀客人,要求四鄉八社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選好的往河北垸送。據說,周邊的小孩、老人都往這裡趕,想趁機打一場「牙祭」。
熱鬧總是像朝露一樣容易消逝。不到一年時間,三年饑荒來臨。建國一社先是按謊報的產量超賣了大量的糧食,接著是吃公社食堂,再接著是天災人禍餓肚皮。建國一社的社員們真正是吃了「畝產三萬六千斤」的虧,到公社糧管所秤口糧,營業員冷嘲熱諷:「哦,你們是建國一社的,畝產三萬六千斤糧食,還稱什麼口糧喲?」
到周圍借糧,遇到的儘是白眼:「就是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搞個畝產三萬六千斤,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超了,要借糧?沒門!」
「周圍的人一點也沒有同情之意。」建國一社的人出去稍遠的地方辦事,一天不能來回,連借宿、吃飯的地方都找不到,人家不接待。
人們開始吃糠、吃樹皮,有一次龔正堂連續三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脹得像個大鼓。後來他跟著村裡的大人去修水利,可以有點飯吃,但同去的20多個人中還是餓死了8個。「在家裡的,餓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喲。」龔正堂說。
一句話,地不是橡皮做的
51年過去了,當年的麻溪河鄉建國一社變成了今日的白果鎮龔家埠村。儘管人均不到八分地,好多地還是都荒了,「沒有人種,都出去打工了。」龔正堂有兩女一兒,兩個女兒外嫁,兒子在廣東打工,在當地買了房子,「不回來了」。
據老人統計,村里超過三分之一的地都荒了,包括離房子不到50米遠的地。長著雜草的撂荒地間雜在剛剛收割完的、還留著稻茬的地里,有些是孤零零的一塊,有些則成片,頗有點氣勢了。從草的長度判斷,有的地荒了不只1年。
老人指著從稻根中露出的黑色土地說:「我們的地很好種的。」
白果鎮農辦主任周汝元介紹,對於撂荒的土地面積,全鎮沒有統計。據他估計,「可能有1000畝左右」,目前全鎮耕地面積8.1萬畝。他分析說,出現千畝荒地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農產品耕種輪換的問題,部分田地是農民留出來為來年準備的;二是因為外出打工造成部分土地撂荒。
「畝產三萬六千斤還會再來嗎?」記者問。
老人笑了笑,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一句話,地不是橡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