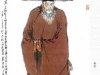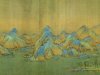歷史上各個統治王朝更替時大都刀光舞動劍影四射,血流成河,屍堆如山。只有趙匡胤在開創北宋王朝時黃袍加身搞了個「和平演變」,從人家孤兒寡母手中順手牽羊兵不血刃得了一個江山。公元960年陳橋兵變,宋承周祚,開啟了大宋三百年江山基業。
得到容易守起來就困難。為此,北宋王朝一建立,宋太祖趙匡胤就在皇宮一處密室立了一塊神秘之碑,讓他身後的繼位者恪守碑文的約束。這塊碑上的碑文左右了宋王朝的政治方向。
陸游《避暑漫抄》記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雖腹心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變,兵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陸游的這段話表述了這樣一段故事:宋太祖趙匡胤開創宋朝之後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通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一個秘密夾室,這個碑叫誓碑,用銷金絲麻蓋著,門鎖閉的十分嚴。每當四時八節的祭祀和新皇帝登基時,都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拿鑰匙將夾室的門打開,新皇帝進去焚香、跪拜、默誦碑文。群臣和侍從都不知道碑文的內容,歷代皇帝都嚴守這個秘密,就是他們最信得過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等到北宋末年,靖康戰亂爆發,金軍攻破開封城掠走朝廷諸多器物,所有的門都被打開了,人們才看到了這通神秘之碑。碑身高七八尺,寬四尺余,上面刻有誓詞三行:第一條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處以死刑。第二條則是優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對其進行殺戮。第三條只是強調前兩條之必須遵守,否則會遭到老天報應。等到建炎年間,曹勛從金國回到南宋,捎回來太上皇的囑託,祖宗的誓碑在太廟,恐怕當今皇上不知道。
另據《宋史·曹勛傳》載,靖康末(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勛隨徽宗被金人虜往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裡,宋徽宗囑託曹勛日後若有可能回南方,要向宋高宗轉達關於誓碑的事情。曹勛後來得以見到高宗,他對高宗上奏說:「太上皇(宋徽宗)讓臣回來後轉告陛下:皇太祖(宋太祖)有誓約,藏在太廟,立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背這個誓約將是不祥之兆。歷代皇帝都是按照這一誓約執行的,已經經歷七代相襲,從來沒有改變。每次想起來靖康年中,誅罰的太重了。現在的禍端,雖然不是因此造成的,但一定要明白,因而要謹慎戒備。」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有這樣的話:「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宋論》中在說這件事時卻有另一種說法:「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這段記載與陸游所說不同在是第三點上。
兩段記載誓碑第一條,都先說了宋太祖趙匡胤對自己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天下,取而代之總有些理虧的愧疚之情。何況柴榮對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於是趙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訓。奪了人家天下,而能優厚其子孫,也算他寬緩不苛,感恩回報。
王銍《默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為這件事提供了佐證: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回師進入汴京皇宮時,六宮迎拜,趙匡胤看見有兩個兒童,就問是誰的兒子。回答說是周世宗子二子,紀王和蘄王。當時,范質、趙普、潘美都在一旁,趙匡胤問他們怎麼處理。趙普等回答說:「應該除去,以免後患。」惟潘美在後以手摳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曰:「你認為不可嗎?」潘美回答說:「臣豈敢以為不可。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 趙匡胤點頭讚許,說:「我接人之位,再要殺人之子,我不忍心。」太祖當即將世宗子其一判給潘美為養子,後不再過問。
誓碑其二是講大宋天子就是讓臣子說得再沒面子,也不能殺了人家。這也使得有宋一代的文人得以成為真正的文人。趙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感知武將掌管兵權對其主子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因而他對武人深懷戒心。他認為武人往往是戰亂的禍首,要想天下太平安定,就不能讓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權力。這是宋王朝高調重文輕武的根本因素。
趙匡胤在一次設宴招待群臣時,原後周臣子翰林學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故主,當眾大哭起來。群臣大驚,都為他捏一把汗。太祖卻毫不怪罪,命人將他攙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當眾大哭,思念周世宗,應當嚴懲。太祖說:「他喝醉了。在世宗時,我和他同朝為臣,熟悉他的脾氣。他一個書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讓他去吧。」這件事也反映出趙匡胤的襟懷大度。
整個北宋基本上不殺士大夫、言官,營造出一種很適合文人生活的氛圍。與歷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那些文人士大夫再怎麼讓皇帝過不去,也不擔心性命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宋初的文化發展很快,在文壇上出現了一些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這樣的文壇領軍人物。其中的蘇軾由於深陷「烏台詩案」,在一片要他老命的呼聲中,蘇軾雖坐牢而保住了自己的「老頭皮」,正是得益於這一政策。
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在漢朝,大臣一人有罪,則會遭到滿門抄斬。本朝祖宗恩澤極厚,還沒有過殺戮大臣,最多就是將其貶謫流放嶺南罷了。」
對於「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讚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據《范仲淹年譜》。
誓碑第三,按陸遊記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而王夫之說法是「不加農田之賦。」我是傾向王夫之這一說法的。如果按陸游的說法去理解,太祖立的誓約第三條無任何意義。
宋太祖開國後以法治國,實行澄清吏治,減輕徭役,興修水利,勸獎農桑,移風易俗等一系列英明決策,不僅儘快醫治了二百多年的戰爭創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那裡,可就沒有趙匡胤氣度了。他的《皇明祖訓》中充滿血腥的味道:「今吾朝罷丞相,設五部六府,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大明律》更是殺氣騰騰:「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書言大臣德政者,皆斬。」
兩相比較,還是趙匡胤的「誓約」溫和的多文明的多。正是在趙匡胤影響下,北宋王朝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頂峰;北宋王朝可以說是君主專制史上的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太祖誓碑」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誓言。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