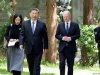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張光撰稿

2013年的中國以官方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國夢而始,以半個中國陷入霧霾的苦境而終。任何明白人都知道,中國的霧霾大爆發是過去三十年,特別是近十年經濟發展模式累積的結果,而中國式地方分權恰恰在這個發展模式中居於核心地位,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必須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分權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貢獻,但也需要集中談談中國式分權給中國造成的問題,包括席捲半個中國的霧霾難題。
中國式分權主要表現為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行政分權主要是各級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的社會經濟事務的管理和發展,尤其在規制的設定和執行上,享有高度的
自主權。例如,在過去的十年裡進行的幾輪房地產調控,都是中央給大政方針,地方政府制定用於本地的具體規則。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的規制也或多或少以類似的方式形成和執行。
財政分權則主要是中央財政所做的幾乎完全限於國防外交並維持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如海關和國稅)運轉,而國內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幾乎完全由地方財政承擔。這一點,清晰地表現在財政數據上(圖1)。
2012年,在全國預算內財政支出中,中央占14.9%,地方占85.1%。而且,如果把預算外支出、社保基金支出、國有土地財政支出等加進來考慮,中國地方財政支出比重當接近90%。放眼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達到這般財政支出分權的水平。美國學者蘭德里在他的《中國的分權型威權體制》(2008)一書中,把中國的地方財政支出比重與世界其他50餘國做了比較。僅次於中國列第二位的是聯邦制國家美國,其地方(包括州和州以下政府)支出比重不到50%。按財政支出口徑計量,中國是世界上最分權的國家,沒有之一。

圖1:中國預算內財政規模及其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布,1978-2013
中國行政集權與財政地方分權古而有之
中國為什麼能在地方分權特別是財政支出(事權)分配上成為世界的例外?
原因之一是中國歷來如此。在漫長的帝制社會中,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至少就其文官系統而言,規模非常之小,不過區區數千人而已。國內的一應公共和管
制事務,從稅收到教化(如科舉考試),從驛站到河工,基本均由地方政府承擔。甚至在軍事財政也是如此。在朝代強盛之際,通常由地方政府在朝廷的統一調配遞解下,供養所轄地區的軍隊;而在朝代衰落之時,則出現軍閥控制地方行政,各自供養的局面。
如此分權,中國何以能夠保持大一統數千年不倒?其奧妙之一在於秦朝形成並綿延不絕的皇權官僚體制。在正常情況下,所有縣級以上文官和武將都由中央政府甚至皇帝任命,帝制中國的官僚政治集權為它的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礎。
從這個觀點看,民國近40年的歷史,大半是在地方軍政一體的境遇下渡過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在北洋軍閥時期,還是南京政府時期,都沒有達到帝制中國中央政府(朝廷)強政治集權的狀態。
新中國同舊中國相比,則有沿襲有損益,但在變動中保持一點
不變。這一點就是官僚政治集權。皇權雖然不再,但馬列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為政治集權,不但提供了更強的意識形態辯護,而且形成了更具操作性的手段。自建國至今,中共在各級黨政領導由上級、最終為中央任命產生這一點上,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動搖。
然而,在行政和財政分權上,改革前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建國後的前30年中央計劃經濟,地方政府在行政和財政事務上,幾乎沒有任何自主性。其主要表現之一是國家財政資金大量用於經濟建設,特別是基本建設(通常占財政總支出的40%),國家經濟建設主要由財政融資,而財政建設資金絕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及其部委執行。因此,國家財政支出的半數以上由中央政府完成。這一財政支出中央集權模式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依然清晰可見(圖1)。
眾所周知,這一經濟管理模式使地方和民間發展經濟的動力消滅殆盡。再加上改革前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和鬥爭,導致中國經濟在毛澤東的晚年到了瀕臨崩潰的地步。
改革開放後財政大包幹:中央地方均尋求機會主義
所以,改革伊始,中共中央一方面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另一方面則在堅守甚至強化官僚任命政治體制的同時,進行了大膽的行
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自秦以來至1980年代,中國的財稅的大部分基本上一直由地方政府徵收,但地方不過是中央政府的稅收之手,並無任何自主裁量之權。
1980年代的財政大包幹制,給予地方政府以控制支配按契約規定的財政收入「剩餘」,即劃歸上級政府後的所有剩餘收入的權力。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
各地政府特別是那些經濟增長迅速的地方政府,很快就學會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與中央政府博弈的方法:一方面,它們只完成為財政合約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財政收入,以求得將上解中央收入最小化。另一方面,它們想方設法變預算內收入為預算外收入,因為後者無需與中央分成。
這樣做的結果是,財政收支規模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逐步下降,即便是把預算外收支規模加進來,國家財政規模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仍然顯著下降(圖
1)。這一發展,客觀上起到了藏富於民、國退民進的作用,曾為鄧小平所讚嘆的異軍獨起的鄉鎮企業,就是在這樣一種地方分權的財政制度下形成的。
然而,財政大包幹的邏輯是不可持續的。上述地方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最小化、化預算內收入為預算外收入的手法,雖然沒有違背財政包幹契約,但畢竟是鑽
空子的機會主義做法。事實上,少數地方政府如北京市為了留住收入竟然在1990年前後向中央政府隱瞞了幾十億元的財政收入。而財政窘迫的中央政府,在
1990年前後,不得不重演百年前晚清政府派員向富裕的廣東省借款的苦戲。這些借款,從一開始,就沒有還的可能和打算。
結果,財政包幹制的邏輯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雙雙走上了機會主義的博弈道路。
分稅制改革讓中央和地方在擴大財政收入問題上一致
1994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徹底改變了中央與地方在財政分權關係的邏輯。
改革把最大稅種增值稅定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並由新成立的國稅系統來徵收,並按央75%地25%外加稅收返還的既定規則統一划給地方政府。這一改革使地方政府沒有機會在分成收入上搞收入最小化。更重要的是,財政
包幹制下地方政府在分成財政收入上執行最小化戰略的動機不復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擴大財政收入的問題上利益完全一致。
各地政府不但努力協作在本地的國稅部門徵收國稅,以期增加自己的分成收入。(因此,各地國稅局的部門預算中,大約20%來自於所在地方政府的激勵性補貼)。而且,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更是不遺餘力地徵收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專享收入,從預算內到預算外,從稅收收入到收費收入,從社保基金收入到土地出讓收
入。原因無他,根據分稅制的規則,地方政府對劃給它們的分成收入和自有收入的使用,在不違背中央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主裁量權。
發展地方經濟,成為擴大地方財政收入的最好的手段。這一點和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GDP主義在鄧小平南巡後被強化至極的形勢相配合,驅動中國財政規模不斷擴張(圖1)。
分稅制驅動下的GDP主義最終導致環境惡化
在
1980年代,除了廣東珠三角的例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離鄉不離土的鄉鎮企業(尤其在蘇南)和私人企業(浙江)以及地方國營企業。按企業所有歸屬分配財源的財稅包幹體制,促使地方政府非常看重企業的地方所有性質。土生土長的企業,通常會對家鄉的水土保持應有的敬畏感,再加上它們多建於輕工業和耐用消
費品產業,國人的消費尚未進入住房、汽車等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建造並使用的階段,因此,1980年代的初期工業化並未對中國的環境造成重大的破壞。
而自1990年代中葉以來,在分稅制條件下,地方政府對於企業的觀點,發生了「不重所有、而重所在」的變化。招商引資儼然成為眾多地方政府的頭等大
事。外來的企業,包括民營的,外資的,甚至國有的央企,大多缺乏本地企業對鄉土的那般敬畏。中國經濟自1990年代以來的「世界工廠化」、重化工化和房地產化的背後,往往都有不斷流動的產業和金融資本和固守一地的地方政府的合作和共謀,而並非偶然地,中國地方政府的黨政主官多為非本地人出任,而且變動頻率
極高。這些力量的結合,在使中國獲得20餘年兩位數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其付出了產能過剩、環境惡化的沉重代價。
改革帶來的地方分權提供社保也是一種例外
1990年代,作為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國進行了「抓大放小」、「減員增效」的全國性的國有企業改革。結果,除了行政和事業部門外,單位不再成為中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的提供者。中國開始建立政府主導的社會化保障網絡。從那時到現在,這個社會化保障網絡一直處於各地政府分而治之的分權實施狀態。
以最大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為例,除了四個中央直轄市的例外,其餘各地的統籌水平基本上仍然停留於縣市層次。這一發展,大大加劇的中國財政支出分權的水平。
中國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險收支的地方分權化,在全世界的範圍上看亦屬例外。已開發國家不論採取聯邦制或單一制,均由中央政府主導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障。實行社會保障計劃的開發中國家,也多由中央政府主導。
從理論上看,中央統籌社會保障,使保險基金庫在一國範圍內
最大化,風險分散最大化,並有助於社會公平。進而言之,在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財政的地方化根本無法成立。這是因為,如果某地提供比其他地方更好的社會福利項目,必然使它成為福利磁石,吸引大量人群來該地享受福利;與此同時,在財政分權的條件下,該地的福利開支只能來自本地的財
政收入,為此它的財政徵收水平不得不超過其他地方,而這必然使資本和勞動力以腳投票,遠離而去。於是,在資本和勞動力充分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服務的地方分權化必然導致各地政府的「逐底競爭」,儘量降低稅收水平,儘量少提供社會保障。這是造成在許多國家那裡社會保障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的事實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之所以能夠以地方分權的方式提供社會保障服務,根本原因在於戶籍制度。依靠這個制度,地方政府能夠在吸引資本和勞動力流入的同時,把非本地甚至非城市戶籍人口排除於本地的社會福利網之外。結果,中國的社會保障福利能夠在地區之間、階層之間非常不平等的分配下延續至今。
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和轉移支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平等狀況,但離社會公正和效率的起碼要求還差得很遠。社會保障物品和服務分配的不平等又給予地方政府以強烈的誘因去維持並保護早已不合時宜的戶籍制度。
總之,中國今天的眾多公共政策問題,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社會保障提供的低水平和不公平分配,都與中國式的地方分權息息相關。
這些問題的治理需要改革和完善中國式分權。首先,中央政府應當承擔更多的事權,尤其是與社會保障相關的事權。基本養老保險由於只涉及到資金的收取和支付,由
中央政府來操作即全國統籌,從技術上來講完全可行。其次,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政績的考核標準,再也不能唯GDP是論。社會政策和環境保護應當成為優先考核標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切實落實基層民主參與。2007年,廈門市民的政治參與,加之當地和福建省黨政領導的開明,使PX項目不在廈門實施,才有今天廈門乃至整個福建良好的環境和清新的空氣。事實證明,廈門和福建的經濟發展,並沒有PX項目未在廈門設籍而受損。廈門和福建做得到的,中國也應該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