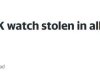在用來吸引客人的粉色螢光燈光下,一名女性性工作者列舉了在中國從事這份工作的職業危害:粗暴的客人、感染愛滋病的恐懼,以及如同利刃一樣插在她心上的鄰居們尖銳的眼神。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這個名叫李正果(音譯)的女子在等待下一名客人時說,「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焦慮,有時,在出賣了自己的身體後,我感覺我的心都死了。」
但她最擔心的還是警察上門。上一次被帶到一個當地警局之後,沒有經過審理,沒有律師為她代理,李正果就被送到了附近河北省的一個收容中心。她在那裡待了六個月,每天製作裝飾用的紙花,或者背誦禁止賣淫的法律條文。在她離開邯鄲收容教育所的時候,又一件令她氣憤的事發生了:她需要向監獄交納每月大約300多元的生活費。
李正果說,「下一次如果警察要帶我走,我就割腕。」現年39歲的李正果有兩個兒子,是一個單親媽媽。

中共政府去年11月宣布,將廢止勞教制度,這是法律改革倡導者的一次勝利。勞教制度允許警方在未經法庭審理的情況下把輕微罪犯和對政府瀆職行為表達了過分激烈不滿的人送到勞教所,時間最長可達四年。
不過,與勞教類似的兩個法外懲罰機制仍然存在:一個針對毒販,另一個針對性工作者及其顧客。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中國問題研究員科琳娜-芭芭拉·弗朗西斯(Corinna-Barbara Francis)說,「濫用職權和刑訊逼供仍然繼續,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在進行。」
「收容和教育」,這一針對性工作者的含義不清的懲罰制度,與勞教制度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這些女性會在公安部營運的收容教育中心關押至多兩年,她們通常會被要求在車間裡干苦工,一周工作七天,沒有報酬,生產玩具、免洗筷和狗尿片。被收容的婦女說,其中有些產品的包裝是用於出口的。倡導組織亞洲促進會(Asia Catalyst)上個月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嫖娼者也會被關進這樣的看守所,但人數要少得多。
中國有200個收容教育所,一些曾經進過收容教育所的婦女們描述了裡面昂貴的收費和獄警對她們實施的暴力。
就像勞教制度一樣,警方不經審理就對性工作者處以收容教育的懲罰,後者幾乎沒有申訴的機會。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高級研究員林偉(Nicholas Bequelin)說,「這種制度隨心所欲、濫用職權,從公共衛生角度看是災難性的。」該組織去年發布了一份報告,內容有關女性性工作者在中國蓬勃發展的性產業中面臨的種種危險。「這是中國法律體系的另一個腐朽分支,應該被廢除。」
亞洲促進會的報告稱,收容教育所是以改造女性為名的龐大斂財機構。這些看守所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1年建立的,由地方公安機關管理,它們對如何處罰被收容者擁有最終決定權。曾經的被收容者說,警察有時會以釋放在押人員為條件索取賄賂。
中共政府未公布有關收容教育制度的數據,但是專家估計,每年有1.8萬至2.8萬名女性被送進看守所。亞洲促進會的報告說,被收容者需要自己承擔食物、體檢、寢具以及香皂和衛生棉等生活必需品的費用,大多數婦女在六個月的收容期間會花費人民幣大約2400元。
一名婦女告訴亞洲促進會,「交不起錢的人每天只能吃饅頭。」
在一些看守所,探視親屬的人也需要交納200元的費用。
研究過這一制度的人士說,地方的警局可以從這些免費勞動力身上獲取豐厚的收入。
中共政府對賣淫活動的態度一直在變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將妓女的改造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共產黨認為妓女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受害者。在執政的頭幾年,毛澤東有效地禁絕了這個產業。不過,上世紀80年代初的市場改革導致了色情服務業的死灰復燃,一份聯合國報告估計,最近幾年在色情行業工作的女性達600萬人。
如今,中國的城市到處可以見到這種「髮廊」:髮廊裡面是很多用帘子遮擋的黑屋子,看不到理髮剪;在高檔的歌廳,年輕的女服務員也扮演著應召女郎的角色。許多賣淫女說,收受了賄賂的警察通常會對她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在定期的「嚴打」運動中,這種明顯的寬容就會消失,大批賣淫女會受到圍捕,這種活動通常發生在重要的政治會議之前。遼寧省的一名警察告訴亞洲促進會,地方的公安機關需要完成指標,所以會開展突擊的掃黑行動,為監獄的工廠補充勞動力。
法律界人士說,警方有時為逼供使用暴力,強迫女性性工作者拍裸照,作為她們違法的證據。亞洲促進會倡導官員沈婷婷說,「警方對待性工作者的方式踐踏了她們的尊嚴。這個制度給女性打上了恥辱的烙印,並且傳遞出一個信息,即性工作者是骯髒的,需要被改造。」
據女性性工作者描述,看守所的勞動尚可忍受,但是極其單調乏味。一名來自中國東南部的江西省的41歲女性說,她在這樣的監獄待過,製作毛絨動物玩具,有時要做到晚上11點。她只肯說自己工作時的名字是小蘭。她說,「縫的太多了,手都疼了。」
在被問到這個制度中的教育成分——主要是花大量時間背誦監獄的行為準則,她笑了起來。「我們管獄警叫老師,他們管我們叫學生,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學到,」她說。
小蘭被關了六個月之後被釋放,繼續從事以前的工作。她說,「其他的姑娘也是這麼做的。」
在電話採訪中,設有大型收容教育所的幾個省份的公安官員拒絕談論這一話題,他們說,自己沒有得到對媒體講話的授權。
尋求廢除這一制度的人們承認這很難實現。公眾幾乎不支持減輕對賣淫嫖娼的懲罰,影響力強大的國內安全機構也不太可能願意放棄這種權力,以及現有制度帶來的利益。
在看守所的屈辱經歷並沒有讓這些女性下決心轉行。她們作為性工作者每月能賺得超過6000元人民幣,是中國無特殊技能勞動者平均收入的三倍。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李正果說,她沒有文化,如果做一份平常的工作永遠不會賺這麼多錢。她說,「我是一個沒有技能、沒受過教育的農村婦女。」
曾經是個養豬戶的李正果笑聲輕飄飄的,她目前在北京商業中心一個狹小的街面房子裡工作。她接待客人的地方與她和兒子的臥室只隔了一面薄牆。
來找她的都是常客,大多數是已婚男人和孤獨的民工,但即使是常客,有時也會賴帳。有些客人冒充警察,要求她們免費服務,有些客人偷偷把安全套頭部剪開,還有喝醉了的客人,如果李正果拒絕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會怒不可遏,暴力相加。
她說,「我會報警,但是警察總是站在客人的一邊。」
說完,她便站起身,去接待等在門外的一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