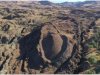〔原編者按:這是27年前的1993年李科威同學的一篇小文,若不是有切膚之痛,相信他不會寫下這些蒼涼文字。他是個觀念超前、很有想法的人,也很有奮鬥的激情和毅力,曾很想一展宏圖,卻在現實中常有掣肘之煩,最終決定遷徙美國。寫作此文時,他以為從此真的永遠漂泊天邊了。然而,他的根終究在中國,十餘年後,事實上他又重返祖國創業,創研電腦診病新領域,成效喜人。他本可以在國內考古行當更好地施展才華,卻因這一出走,因為改行,中國考古學界永遠失去了一位富有傳奇性的好手。讀讀此文,或許多少可以看出他當年為何要遠行……〕
我將要移居美國了,熟人、朋友紛紛向我道賀,說是天大好事。可我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實際上,在近十年中,我放棄了好幾次機會,這次要走,只是我敗走麥城的選擇。
早上,鄰居小孩問我:「你還會回來嗎?」我無言以對。
此前我一直希望能與工作單位保持某種關係,也想不久能回來。當小孩問我時,我已經面對著毫無浪漫色彩的現實:離職、退房、銷戶口、捲鋪蓋走人!
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不再有我的容身之所。
忙亂之餘,我開始閉門思過。要說我不成功吧,我也幹過一些事:完成了國家文物局《考古情報檢索系統》等項目的研製;在人工智慧應用於考古的領域,曾有過獨占鰲頭的地位;在考古理論領域裡,我發表的《中國考古學變革的基本結構》《考古類型學的進化觀與文化動力學的問題》等文章,可以說是在考古學界先聲奪人。
而要說我成功吧,我也有許多失敗:國家文物局《中國考古主題詞表》項目實在無法繼續;我企圖推進計算機應用於考古事業的計劃和推進考古學理論發展的計劃,難以大面積實現。我可以不辭勞苦、不爭職稱、不計錢財,然而我無力改變社會現狀。
也許我的失敗就在於太認真,又太自以為是。
早有畏友如是告誡:「有心雄泰華,無意巧玲瓏,自認為仗義為國,更加之功高震主,數惡難赦,安有不敗之理?」
人生需要忍受,這對我並不是難題。而現在,我遇到的不是用忍受可以解決的問題。政策或執行政策的人,毫不留情地在移民與自己生活的祖國之間砍下一刀。我想大約是這麼一種邏輯:從前你是「公家」的人,用的是「公家」的物,做「公家」的事,享受「公家」的待遇;現在是你要離開「公家」,你赤條條來、赤條條去吧,休想占「公家」的便宜。住房和辦公物品是公家的,必須退掉:屬於自己的兩大項:變買全部家當,值人民幣3000元,離職費3936元,此兩項之和,按照政策能給我的價格比率,即以8.35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再以1美元兌換5.72外匯券,不夠買一張去舊金山的飛機票。
想想這就是我在「公家」的單位工作26年後,屬於我個人那一部分所得,僅此而已,心中不免有無邊的悲涼。
說是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可我現在竟有些茫然,我的「根」在哪裡?爺爺、奶奶死了,外公、外婆死了,他們曾經擁有的財產早巳灰飛煙滅;父親死了,母親出國了,在這兒何處尋覓親人的依憑?何況可資為「根」的東西正隨風飄散:工作沒有了,戶口沒有了,房子沒有了,我委身於公家的一切將連「根」拔除。
記得父親死時正值三十年前那個可怕的「三年」的苦日子,母親無力負擔我兄妹四人,把哥哥和我送進了湖北沙市的孤兒院。每當天空放晴,我被罰頂著尿床尿濕的被褥,站到膏石板的台階上去曝曬。可以後我有機會去沙市,還是要去尋找當年孤兒院的舊址,想再去站一站那青石台階,摸一摸那尿濕的被褥,這是不是一種「根」?
後來,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從湖北沙市遷到了湖南長沙,那時我們全部的家具,只有最小的妹妹擁有的一張小木方凳,可是至今我們全家都還惦著那張早巳無影無蹤的小板凳,這是不是也算是對「根」的留戀?
我現在的家很清貧,沒有一丁點兒奢侈品,土氣破舊的家具總令我有不舍之情。我不抽菸、不喝酒、不要小孩,工資維持著最恬淡的生活;這使得我有可能拿出一點點錢,去潤滑我領導的課題組以高效運作;我家中的所有簡陋的家當,也是從牙縫裡一點一點省出來的。
那天我找所長說:「能不能借給我一間小房子堆堆我的家什,我也算這個所的開朝元老,我還想回來。」所長的態度,是這樣子:「不行,一間房子一個月可租二百多塊!美國有的是好東西,你那些破爛早該扔了。」
我的東西是不好,可是那畢竟是我的,那上面有我的心血、有我的歷史,此外,還有我的書、我的數十萬字的手稿。我想:即便我暫時不一定回國,但總有一天我會來找尋堆著我破爛東西的小屋,拂開灰塵,獨自一人借著窗口飄進來的一縷夕陽,翻翻我自鳴得意的那些手稿,發一回身曾許國、命未逢時的牢騷。可是,幻想還沒開始,就已經破滅,「掃地出門」的感覺油然而生,強化了我沒有了我的鄉土的意念,我甚至懷疑我會失去了自己的祖國。
我的父親於1960年死在武昌那個他為之努力奮鬥的醫學院裡,那年頭,「右派」的骨灰是無人關心的,於是骨灰成塵,再也無人知曉其下落。三十多年來,我們兄妹沒有掛祭、沒有掃墓,因為沒有他的骨灰、沒有他的墳墓,慢慢的,就好像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人一樣。
前兩個月母親來信說:去給你們的父親刻個碑、修個墓,哪怕是座空墓。如果是為了靈魂保佑的話,三十年多來他不曾保佑過我們,難道現在需要他來保佑?我知道,這是母親和我們兒女心底一件說不出來的心事。
父親死後,為了養活我們,母親變賣了所有東西,只留下賣不出去的兩件西裝背心。知青下鄉時,母親在背心的夾層里舖上棉花給我和哥哥當棉衣,我一直穿得很愛惜。這次我們拆去棉花,把背心作為父親的遺物,埋在了屬於他卻並沒有他骨灰的墳墓里。世界上又多了一座空墓,空墓能表示什麼呢?也就是一絲絲牽掛罷!同時也就帶上了一點點對母親國的懷念吧?
可是,畢竟我不可能用一生的時光去陪伴父親的墳墓,我生活在我的家、工作在我的單位、奮鬥在我的事業里。無論愛還是恨、無論血還是淚,經過四十年的融煉,我的生命已和這塊土地緊緊聯在一起。一個農民,他的祖國可能就是他耕耘收穫的土地;一個市民,他的國家或許就是他遮風避雨的住所;一個學者,他的祖國是什麼呢?
美國的商人就是聰明,居然在中國發起了「擁有一片美國」的活動,利用感情賺取金錢。我沒有金錢,只能用汗水澆灌情感,我只想擁有「一片中國」,可是,以我26年的年資、刻苦踏實的工作精神,是不足以支付每月二百元的房租以擁有那「一片」的國的。然而,只要以移民的腳步走出這個國度,我就將失去生於斯、長於斯的一切,就像一棵砍掉根、擄去葉的樹。
我不甘心如此結局,竟向所長乞求:能不能借一點錢給我,不管多少,能讓我擁有一片債務。當我確信一切都是惘然時,我感到一片空虛,一種令人窒息的虛無感在瀰漫。我,就要離開我的國了,我想擁有一份對母親國的牽掛,我無法為自己也修一座空墓,那麼難道就不能擁有一份債務?
又是一天開始了。家,已被搬得空空蕩蕩;床,鋪在地上:只有幾個準備帶去美國的箱子昂首挺立。在這一片土地上我即將逝去,無言、無怨、無悔。天空靜得出奇,烏雲裹挾著悶熱,嚴嚴實實地罩在喧囂的大地上。
就在早幾天,國家文物局來人檢查工作。當他們聽說我準備出國和我沒有完成《中國考古主題詞表》的原因時,感嘆嗟吁了一番,猶懇切說:「其他都不談了,關於『詞表』,走之前如果你能『哭』出來,就為我們『哭』出來吧。」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多少年來我兢兢業業工作不就是為了一點點信任?時間雖然只有10天了,且放下繁瑣的私事吧,再做一回銜木的精衛、帶血的啼鵑,去為「詞表」「哭」最後一聲,同時也為我的祖國、也為我自己,哭……
1993年6月寫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