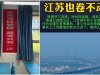上頓渡不大。如果二環道上的北京城牆還在的話,把上頓渡放在裡面,差不多能圈下。從全國範圍看,這是個再平凡不過的小鎮;但在江西,這是個誕生神話的地方——關於教育的神話,說得再準確點,是臨川中學的高考神話。
上頓渡最有名的是鎮上的兩所學校,臨川一中和臨川二中。前者在2021年《全國百強中學》榜單中排名43名,江西省排名第一。幾乎每年,都會有數十名畢業生從這裡考入清北。近二十年來,這兩所學校吸引著來自江西乃至全國範圍內的學生。教育拉動了上頓渡鎮乃至臨川區的經濟發展,甚至連小鎮上的潮汐晝夜,包括大多數店鋪的開關張時間,皆以學校的鈴聲為示。
鎮上最多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學生,一種是學生的母親。陪讀,是後者到此落腳最重要的目的。照顧孩子之外,多數媽媽還會去超市、房屋仲介和手工作坊謀一份生計。但千萬要緊的是,不能耽誤自己的「本職工作」。陪讀媽媽幾乎能滲透上頓渡的所有角落。上頓渡年紀輕一點的女性「80%都是陪讀媽媽」——有人甚至會這樣說。

臨川一中
但現在,媽媽們在離開。只消在鎮上逛一圈就能發現,房東們的空房間多了起來,有些商鋪也貼上了關店轉租的告示,地產商新建的樓盤不少陷入滯銷。
隨著幾所中學的搬遷,上頓渡作為一個「陪讀小鎮」的輝煌正在消散。
但「陪讀」不會消失。就在臨川一中實驗學校的新址,與上頓渡的衰落同時發生的,是一個「新上頓渡」的建立。「狀元樓」、輔導班、小作坊、棋牌攤,正在這片名為「白嶺新村」的農民自建樓里生長。7點、12點、17點半、22點,是學生上下學的時間,這些數字因為學校的鈴聲在白嶺新村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陪讀媽媽隨著孩子遷徙至此,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呼吸。
神話
上頓渡據載已經存在千年。相傳,此地始建時原名「頓溪」,為溪岸頓居之意。千年以來,宜黃河從這裡穿流而過,讓這裡成為一個建有商驛、會館的古渡。
古渡早已不在。今天,這裡的活水是學生。與之頓居於此的,還有陪讀的母親。後者有一個特殊的名字——臨川孟母。
新時代的孟母來自撫州乃至江西其他地市,甚至全國各地,她們像水一樣流進頓溪,讓孩子匯入高考大軍。其目標是臨川的兩所中學,臨川一中和臨川二中。
趙引娣在上頓渡生活了73年。在她的記憶中,一中和二中幾乎是上頓渡存在最久遠的建築,連縣政府都比它們建得晚。她住在臨川二中西門對面一條巷子裡,拐出去,就是上頓渡老街。趙引娣說,上頓渡原本只有這一條大路,貫穿南北,一中在北頭,二中在南頭。

趙引娣家所在的小巷
「才子之鄉」是個當代神話。在包括趙引娣在內的不少上了年紀的上頓渡人看來,一中和二中經歷了一場「爆紅」,在那之後,上頓渡才漸漸與「才子」捆綁在一起。
這兩所中學首次登上新聞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彼時,「超常教育」的概念炒得火熱——1978年,中國科技大學設立少年班,招收少年大學生。1977年,以13歲年齡進入少年班的寧鉑正是來自江西。有統計顯示,1982年至1986年,撫州地區先後為中國科技大學等九所高等院校少年班輸送了66名學生,其中34名來自臨川。一時間,小鎮因「神童」喧囂起來。在趙引娣的記憶里,這些少年大學生們考入的大學叫「少年科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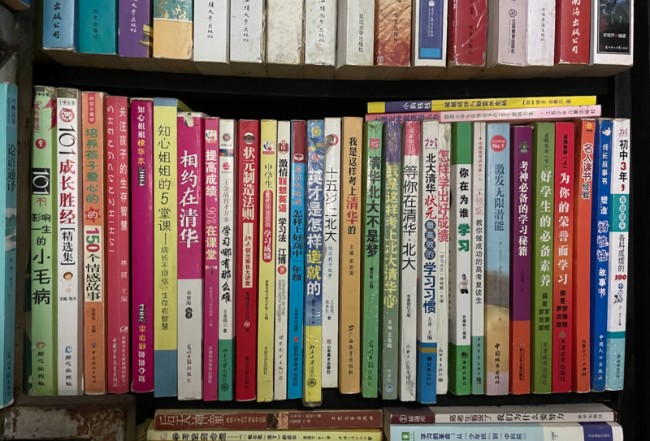
鎮上的一家書店裡,擺著不少勵志類圖書
另一個關鍵的節點是2002年。
新世紀初,臨川區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撫州市臨川區時任區委書記堯希平2002年接受採訪時坦言,當年的財政缺口約有8000萬,2001年則為7000萬。在此背景下,區政府對臨川一中、二中「財政『斷奶』」。兩所中學就這樣被推入市場。
2002年,臨川教育集團成立;2015年,集團內的撫州一中、臨川一中和臨川二中又以「名校帶私校」為由,分別建立了民辦的實驗學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這種雙軌制賦予了教育集團在現行教育制度下更高的自由度與自主權,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外地學生,而這些外來者們也成就了今天的上頓渡。在2007年的報導中,時任臨川二中行政辦主任熊海水回憶,從2002年開始,兩所中學開始大規模湧進「外籍」學生。
2009年,臨川一中新校區建成。隨著新校舍拔地而起的是東西南北進十座住宅小區的落成,它們的名字也多有「文氣」——學府世家、書香門第、狀元府邸;甚至還有處樓盤取名「諾貝爾」。那是臨川樓市最火爆的幾年。一位曾給外地生們做過幾年保姆的本地人告訴全現在,學校南門的文鼎苑樓盤,開盤後沒出一周便全部售罄。

臨川一中新校區附近的一處小區,取名「書香才苑」。
趙引娣住的是一幢三層民房,一牆之隔,就是2018年建成的高層樓盤。新開盤的房子,一平方米價格近萬。緊挨王安石公園的「麗水豪城」項目的房產仲介告訴全現在,目前該樓盤成屋價格為5680元每平,只剩兩套在售,其餘皆已售罄。她說,開發商的總經理來自河北藁城,正是瞄準了上頓渡因學校帶動的市場,才在此投資。
趙引娣家原有的耕地被征去蓋了新樓盤。她就用補償款另建了一幢小樓,一層堂屋,二層自住,三層是兩對二中的陪讀母子,在上頓渡街頭,經常能看到地產商的廣告,「讓孩子贏在人生起跑線」。標語和它所構建的高考神話,堆迭在上頓渡,編織著有關未來的夢。
陪讀
對於購房者來說,買房,就是為了上頓渡的戶口;有了戶口,才能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區政府不遠處的地產廣告,寫著「買房就是為了孩子」。
25歲的李娜和母親在上頓渡經營一家手工作坊,生產塑料髮夾。平時,她一邊看店,一邊照顧三個月大的兒子。雖然兒子年紀還小,但她已經在為陪讀臨川一中做著準備。幾年前,她和在撫州市做電梯維修的丈夫買下了鎮上一個新建的樓盤,為的就是給兒子設籍。從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就進入臨川的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有更高的機率升入鎮上的高中。她告訴全現在,臨川區的戶籍政策這些年一直在變,現在買下房子後,需要七年才能正式設籍。之前,這個時限是5年,再之前是三年。有了戶口,孩子才能進入臨川的九年義務教育學校。為了一個確定的未來,他們得提早準備。
「(來)我們這兒的都是陪讀媽媽」,李娜說。她的小作坊位於老街東側一片安置房的三層樓群內,這片區域裡,類似的小廠還有很多家,除夾子之外,還分別會製作手套、頭繩等小物件。空閒時,媽媽們會到作坊里打點兒零工,要是住得遠,還可以把「料」拿回家裡。
在李娜的作坊里,做一件夾子能賺一分,老闆淨賺2厘。「媽媽工」是產業鏈的最低一環,這些產品從她們手中離開後,還會經過三四層中間商,最終到達浙江義烏。李娜透露,像這種義烏小商品,源頭的製造者,都是四線或以下城市的媽媽。一天下來,一人大多能掙二三十塊,這對每月平均三千元上下的開銷來講是杯水車薪。「打發時間」,是這份工對媽媽們來說最大的意義。

「媽媽工」們在李娜的作坊里做活。(左一為唐麗)
店裡三四張小桌,每張桌子旁都坐著三名女工,手工活在掌間上下翻飛。「當陪讀媽媽的感覺?枯燥唄!」唐麗說。她今年39歲,臨川本地人,三個孩子,兩個讀小學,大女兒在臨川一中上高二。唐麗的丈夫一直在廣東做建築工,獨自陪讀的生活,她過了十七年。
下午是小作坊最忙的時候,因為上午孩子去上學後,媽媽們需要準備午飯,午後到晚上這段,是她們可以自由支配的最長也最完整的時間。唐麗身材微胖,髮絲間滲著些汗水,她坐在桌子一側,從塑料堆件中拿出兩粒,再取根小針,夾著鑷子推進孔里,不消幾十秒,一隻髮夾就能做好。這是個做不完的工作,原料總要做完再取,成品堆滿即清,兩堆碎料塊此消彼長。
唐麗的生活就淹沒在這種無休止的重複動作中。除了這份「死累」而又收入低微的活計之外,她每天還要按時洗衣煮飯,照顧好孩子們的後勤。她羨慕丈夫的工作:「在外面打工多好,一門心思賺錢,賺到錢就下班,下班就睡覺。」
李娜從不愁生意。手工業時間靈活,工資計件,是媽媽們的理想工作,媽媽工「畢業」一批又來一批。她有時在抖音上分享一點作坊里的生活,總有人在下面評論:「哪裡拿貨?」
「你到街上去看,見到年輕一點的女性,你上去問,80%都是陪讀媽媽。」在鎮上生活十年,李娜能感覺到,來陪讀的年輕媽媽越來越多,陪讀年限也越來越長。她告訴全現在,在以前,上頓渡的陪讀模式是,小孩中考達到臨川一中二中的錄取線後,家長帶著孩子到鎮上陪讀;大概從六年前開始,越來越多的媽媽會在孩子上初中,甚至小學時就來到臨川。

上頓渡的一家售樓處,不少樓盤都插上了「售罄」的小旗。
「現在的人思維不就是這個樣子的嘛,人都往熱鬧的地方走是不是?」鎮上的一名網約車司機認為,「鄉村教育,鄉村教育能教育出什麼來呢?出了名的才子校園才是更好的咯。」他的老家在臨川區下面的村里,「現在村小都沒人了,一所學校一個學生、三個學生的都有。還有的學生,上了一個學期就不上了,(家裡)給安排到其他學校去。」
村小和縣中的衰落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贏在起跑線,考到大城市,是包括李娜在內越來越多家長的想法。而要想讓孩子成績好,走出小鎮,必須有一個人留下來,這個人通常是媽媽。
「自己不努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作為唐麗們的後備役,李娜已經在為教育發愁了。兒子出生前,她在武漢的一家國學教育機構里做過幼師。自認為見識過「大城市裡的教育」,她不甘像同鄉們一樣將小孩送入村小,而是來臨川設籍。她看中的是這邊優秀的學校資源以及更多的「體制外教育」——上頓渡街面上有不少課外輔導機構,包括舞蹈、口才、樂器等多種門類。
「一切為了孩子」被貫徹在上頓渡每一位陪讀媽媽身上。校園的鈴聲,不僅指揮著學生們的生活,也在為媽媽們的生活立法。

中午,臨川一中的學生們在放學路上。
中午十二點——這是臨川一中午休時間,下課鈴響,約萬名學生會從學校湧出,在一個個路口分流,最終消失在上頓渡鎮的大小樓房裡。在那裡,媽媽們備好了當日的午飯,到家吃完飯,再做些功課,就是孩子們的午睡時間。依照距離學校的遠近,租房價格也各有不同。在臨川一中南門對過的「文鼎苑」小區,一套房屋的一間臥室,最貴能租到一年兩萬;條件差一點的,會租一間車庫,一年四千元。有的家長會為了讓孩子多睡十分鐘,選擇更貴的住房。時間有它的標價。
一點到兩點半,文鼎苑小區的小廣場上,會聚滿母親的身影,這是她們「放風」的時間,也是小區最熱鬧的時候。有人打牌,有人閒聊,還會有媽媽坐在長椅上,掏出一兜白手套的半成品繼續做活。雖然夜晚只能睡五個小時左右,但在中午,她們必須保持清醒。如果因為自己睡過頭沒能叫孩子起床,麻煩就大了。
捆綁

文鼎苑小區的小廣場上,坐滿了在打牌和閒聊的陪讀媽媽。
張秀芬的兒子今年高考,她的老家在距離上頓渡百餘公里的村里。2014年,女兒在小升初考試中考上了臨川一中,她就帶著當時五年級的兒子轉學到了臨川。至此,她已經在上頓渡生活了七年。之前,她在學校附近的超市做過收銀員,兒子上高三後,她開始一心幫兒子備考。
張秀芬自稱是「鄉下人」,和鎮上本地人不一樣,她不會和人搭話,也從不跑到長椅上打牌。午後媽媽們集體「放風」的時候,她穿著條紅色長裙,坐在廣場邊上劃拉手機。張秀芬對陌生人總會帶有防備,「在村里叫人騙怕了」,她這樣解釋。
這七年,她社交很少,就算在家裡,也不敢多說話。臨川一中學習壓力大,她的孩子基本每天寫作業都要寫到凌晨一點多。張秀芬小學文化,兒子的功課插不上嘴,也害怕管多了生出事來。許多陪讀媽媽都對全現在稱,現在的小孩「不敢管」,因為「總有學生想不開」。唐慧每年都能聽到這兩所學校中有孩子跳樓的傳聞。據報導,2013年9月14日,臨川二中一名高三學生因不滿嚴格管理,在辦公室割頸殺害了自己的班主任。
在上頓渡,幾乎每座樓的窗戶都安著防護欄,在一間間籠屋裡,媽媽們要陪著孩子度過數個春秋。缺乏娛樂,缺乏社交,更重要的是,「沒有自我」——這是許多媽媽都會說出的話。而與此同時,她們也會認為「這就是媽媽的義務」。

在上頓渡,基本所有的窗戶都裝著圍欄。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2020屆本科畢業生萬若六年中學生涯都在臨川二中度過。經歷過陪讀的她承認,在陪讀過程中,學生和家長的情緒都相當受到成績影響。在這個名為「陪讀」的空間裡,母子雙方都「被學習支配」著。在畢業論文中,她訪談了13名在上頓渡經歷過陪讀的學生。在她看來,「陪讀家長對成績的過分關注會給學生造成心理壓力,其中成績越好的學生壓力越大,他們將家庭的高期望、父母做出的犧牲內化為自己的心理壓力。」
「有的學生金榜題名,有的學生名落孫山,有的陪讀家庭輕鬆和諧,有的陪讀家庭矛盾重重,我們無法一以概之地解釋這些差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擁有獨立人格和思維能力的人,陪讀需要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在論文中,萬若這樣寫道。
萬若希望陪讀媽媽能對孩子少一點關注,多一點獨立空間。但現實是,大部分媽媽都則接受這種捆綁,將自己的生活全部寄託於孩子的每一張試卷。
2019年,張若蘭關掉了老家贛州的服裝店,因為她的女兒在初中畢業後參加了臨川一中實驗學校的自主招生考試,並且收到通知,獲得了免費入讀的資格——據家長間傳言,這項待遇是考試前六十名的學生的專屬。
張若蘭就這樣來到臨川,在學校對面租下一間房子,開始了自己的陪讀生涯。
在臨川的高中里,班級被分為三等:零班、A班、B班。張若蘭的女兒被分到了「零班」。在全現在接觸到的學生口中,零班是「只能仰望的存在」。和其他班級相比,零班師資強、進度快,作業量和學習壓力也大。一名高二學生稱,零班的同學作業差不多要寫到凌晨兩點,就這樣,第二天早上還要到學校補完剩下的作業。
在一中,成績不僅劃分學生的班級,還會劃分家長的待遇。有當地人告訴全現在,在臨川一中老校區里,應屆高三生中成績好的,家長可以在學校宿舍陪讀。張若蘭說,她女兒班上的老師都是華東師大畢業,年薪能達到二十多萬,「A班B班什麼情況我們可不清楚」,她帶著些驕傲。女兒告訴她,班上還有位從北大計算機專業退學的學生正在復讀。
「到這來就是衝著清北,不衝著清北跑到這幹什麼。」剛到上頓渡那陣,張若蘭心氣高得很。但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就叫她認清了形勢。按照過往的錄取名單,即便是成績好的年份,也要年級前二十才有可能達到清北的錄取線。女兒的排名在八十。
起初,她覺得是女兒偶爾沒發揮好,但一年過去了,排名還是穩定在六七十的位置。女兒成績提不上來,張若蘭「一宿一宿睡不著覺」。表面上,她安慰女兒,「一兩次考不好沒關係」;但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她會默默坐著,斷絕一切社交,還會掛斷老公打來的電話。
她不會到家長們聚集的地方聊天,更不會去麻將攤上打牌——傳言說,有個學生父母都來陪讀,結果到了臨川之後,父親沉迷麻將,母親沉迷廣場舞,孩子甚至要半夜把爸媽從外面叫回來睡覺。娛樂,在張若蘭看來,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張若蘭堅信,今天的學習成績就等於明天的人生命運:「你好好學習,你才能幫助更多的人。你自己也能過上人上人的生活,感覺上你就不會低了一等,然後你接觸的人和社會都不一樣的,人群都不一樣。你說那些沒讀高中的孩子,慢慢的慢慢的,他接觸的人的社會地位全部都不一樣了。」

學校對面的白嶺新村是大多數學生們放學後的去處,村口牌坊上寫著「前程似錦」。
複製
2019年8月,張若蘭經歷了一次搬家。她從上頓渡搬到了撫州站前新區,臨川一中實驗學校的新址就建於此。學校對面,是一片名為「白嶺新村」的農民安置房,隨著學校和家長的到來,這座原本只有老人居住的小村熱鬧起來,輔導班、高考樓、小作坊一一開業。村裡的快遞點貼著的招牌都是「媽媽驛站」。

村裡的「媽媽驛站」
在這個距離上頓渡大約八公里的地方,「陪讀小鎮」似乎正在進行複製粘貼。
上午十點半,周桂霞正在村裡的一家手套廠做工。這和上頓渡的那些小作坊並無二致,同樣是由一座自建樓的一樓改造而成,幾十平方米的毛坯房裡整整齊齊擺了十幾台縫紉機。周桂霞的孩子正在讀初三,學校從上頓渡搬到這裡後,她也就換了地方陪讀,但工種沒換,還是做手套。雖然實驗學校可以選擇住校,但她還是在學校邊上租了房子,「從生下來就自己帶,一直這樣子」。
周桂霞算了算,自己每天打孩子六點半吃完飯上學後就來縫手套,十一點多回去做飯,孩子下午兩點上學後接著做手套。一天下來,她大概能做兩三百個,一個兩毛錢。

周桂霞工作的手套廠,和上頓渡的小作坊並無二致。
徐建龍也把之前開在上頓渡的輔導班「勵志精品補習學校」搬到了這裡。他自稱在臨川做了十幾年課外老師,主要輔導地理和數學。由於媽媽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徐建龍這類老師,正好迎合了家長們作業輔導的需求。他的「補習學校」開設兩種班型,分別是作業輔導和周末補習班,價格依年級不等——高中學生的周末班價格為每學期4000元,作業輔導為每月1200元。
白嶺新村正在變成下一個上頓渡,這也為這裡的原住民們帶來了財源。首先是房租。媽媽們說,學生們剛過來的時候,房租基本維持在每年一萬六千元,後來基本每過兩三個月,房東就會「坐地起價」。現在,最靠近學校大門的房子,已經漲到了兩萬四一年。有一些房子,還沒完全建成,招租信息就已經貼了出去。廣告上,「白嶺」已經被寫成了「白領」。

村里貼著的招租廣告
就連學校里也住著媽媽。全現在在臨川一中實驗學校傳達室里見到了一位在食堂工作的陪讀媽媽,早上6點打卡,晚上7點10分下班,一個月工資兩千出頭。她是撫州當地人,之前在上頓渡陪讀,去年學校搬到這邊,就在新學校食堂里找了份活干。她告訴全現在,在學校里,像她一樣的媽媽還有很多。有家長稱,有的媽媽為了邊照顧孩子邊掙錢,會到學校里做宿管,一天工作12小時,工資三千元。
肖彩慧是「白領新村」的新租客。臨高考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肖彩慧回到了女兒周娜娜身邊,在白嶺新村租下了一間房,不到30天的租期,房東收了2600元。
女兒是「高四」的復讀生,之前在南昌師大附中,因為高考成績比估分低了近三十分,只能上南昌大學。周娜娜覺得「丟臉」,為了能進985,她選擇再考一次。
因為高考成績好,臨川一中直接幫周娜娜辦理了戶口遷移和入學手續,還免除了學費。有家長稱,為了能幫學校出成績,學校會按照分數為一些復讀生提供優待。臨川一中實驗學校的學生告訴全現在,校方會對尖子生提供優惠;而分數較低的學生,則需要按照排名劃分等級,每學年收取6000至18000元的借讀費。這名來自鷹潭的學生還向全現在透露,學校里不乏「大老闆的孩子」,「十個(差生)養一個(尖子生)」,他這樣形容。根據臨川一中官方網站提供的數據,2021年臨川一中收入預算總額為13654.11萬元。
「我的快樂伴隨著一次高考消失了」,周娜娜說,拿到高考成績後,她幾乎立刻就做出了復讀的決定,「我希望我去年考高很多分,因為我這一年實在是太痛苦了」。周娜娜說,在那次高考之前,她並沒有那麼在意成績,高考失利讓她「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價值」,開始認為「成績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吃午飯時,周娜娜也會上一會網課。
在臨川一中,學習壓力來得更加實在。之前在南昌讀書時,周娜娜高三下學期一共就只考了四場大考,但到一中以來,她數了數,他們高四的學生至少經歷了15場考試。
她把這裡的生活形容為「坐牢」:睡的是鐵架床、食堂飯菜不新鮮,老師會強調「在讀書的時間就只能讀書」,「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睡覺」,學生連出去散步都不會得到認可。
「壓抑」,這是周娜娜林一生活最多的感受。她描述,住校期間,每晚12點上床後,閉著眼睛,直到凌晨三點左右才能入眠。終於,臨高考前一個月,在女兒的要求下,肖彩慧來到了臨川。
現實
在女兒復讀之前,肖彩慧在南昌做過六年陪讀媽媽。女兒上中學那段時間,在肖彩慧印象里,是家長和學生們最為焦慮的。

肖彩慧在手機里設了近十個鬧鈴,提醒自己按時完成作為陪讀媽媽每天要做的事。
周娜娜的理想職業換了好幾次,最開始是心理醫生,後來是經紀人,最近復讀的這段日子裡又改成了金融,原因就三個字,「很賺錢」。
南昌師大附中周圍同樣住了很多陪讀家長,肖彩慧自稱是其中比較「佛系」的。在周娜娜的高中班上,學生和家長几乎時時刻刻都在為自己的孩子會不會「掉班」而擔憂。肖彩慧稱,女兒所在的師大附中「零班」的學生中,每一個都相當優秀,自律性極強。一旦因為一次考試排名不佳掉到普通班,學生和家長都會在那段時間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
肖彩慧還記得,女兒高一時,一位同班女生在一次月考後從學校附近租住的27層樓上跳樓自殺。事件發生後,老師專門組織了家長會,據稱致使意外發生的導火線可能是女孩的父親繳掉了女兒的手機,兩人大吵一架。幾年後,那個學生的父親,一名警察,也從自家樓房19層墜樓身亡。
比起有些全職的陪讀媽媽,周娜娜覺得自己的母親「做得不夠好」。比如,有的媽媽會給孩子定好精確到分鐘的每日計劃,「幾點鐘到幾點鐘做什麼事,全都安排好」;還有的媽媽是「消息通」,對於各所高校的師資力量,中學的補課情況,大學的專業報考都了如指掌。
「她70%的精力都用到那些小朋友身上了」,周娜娜說。肖彩慧在南昌經營一所幼兒園,女兒也是從那裡升入的小學。周娜娜還記得,好幾次,母親送她上學,一張嘴,說出的都是「上幼兒園」。
也許是長期和年幼的孩子們待在一起,肖彩慧有些「心大」,把女兒也教得單純。如果在白嶺新村呆得再久點,融入了這裡的「媽媽群」,她就能感受到什麼是現實。

天黑後,陪讀媽媽們在超市門口「打小牌」。
從天色剛剛擦黑開始,這裡的街面就成了媽媽們的天下。給孩子送過晚飯,媽媽算是基本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孩子們十點放學之前,她們終於有了一段喘息的時間。這時,有些媽媽會結伴散步,老一點的支起牌攤打牌;稍年輕些的,則坐在了麻將館前的凳子上,交流自己「陪神獸讀書」的經驗。
和上頓渡臨川一中公立校的陪讀媽媽們大多來自撫州本地相比,由於政策更加寬鬆,實驗學校的媽媽們來自江西各地。對於她們來講,陪讀的成本更大,因此對孩子的期待也更高。
「我就把他(孩子)當投資,不管學什麼,你出來不還是想賺錢?誰不想單位好一點,賺多一點錢,輕鬆一點賺錢?」「你看那個老師講那個課,人家說了,就算你賺一輩子錢,說不定你兒子一年就給你消耗了。你這樣來陪讀,說不定你一輩子賺不到的錢,他一年就給你賺來了。」這是麻將攤前一位媽媽的發言,後半段內容來自於她在抖音看來的視頻。聽了這段話,她更加堅定了陪讀這條道路,「都陪讀,你不陪行嗎?」
這個線下的「媽媽群」成員總共七位,大多是放下了生意來到臨川,有些甚至是把孩子從浙江、上海帶過來的。對於其中一些媽媽來說,陪讀是迫不得已的選擇,「我女兒原本放在縣城中學讀,後來看到不對了,別人都往(臨川)這邊跑,我也趕緊把小孩送到這邊來。」還有媽媽說,自己初中小孩班上還有好幾個從北京送過來的,要在臨川讀了書後再回去考試,「那邊卷子簡單」。
「今年江西高考考生多了3萬人」,一個高三學生的媽媽說。一旁那位「把帶娃看作投資」的媽媽立馬搭話:「現在錄取分數越來越高,怪就怪這些家長,再這麼下去,分叫他們搞得越來越高了。」
還有位媽媽有點苦惱。最近,她的兒子突然問了她個問題:
「人活著,為什麼要這麼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