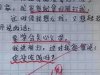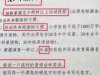能認出照片中有幾個中國有名領導人?陳毅,周恩來,董必武,劉少奇,朱德,宋慶齡…….中間的兩個小姑娘,都是我認識的女孩,這是1962或1963年的照片,那時每逢迎接貴賓如西哈努克親王等,或是國家領導人如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訪問東南亞歸來,她們都會被選去機場獻花,出生根紅苗正,長相甜美可愛,1980年代中我在溫哥華圖書館發現了一份古舊雜誌,就好奇地影印了這幾張黑白老照片,最近偶然在舊物中發現,引起了近半個世紀前的回憶。
那個眼睛很神氣明亮的女孩和我中學同班,住在同一個宿舍里,還常常一起打球和參加比賽。她的父親是大學教師,是解放前就參加革命的大學生,因為文革前發表了幾篇文章,贊同楊獻珍的理論,1966年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自殺身死。我那時都不知道楊獻珍何人,楊有什麼傷天害理的學說致使同意他的人都被逼自殺,留下像花朵一樣可愛的女兒。
這個女孩後來很奇怪,天天靠攏組織,幾乎不食人間煙火,拉著你就是討論大聯合大批判那一套,我們同班同宿舍,認識她時她十三歲,兩年後她父親自殺她就成了狗崽子,不久就眼見她從一個明媚陽光人見人愛的小女孩變得面容枯槁,語言乏味,不食人間煙火,天天都是革命鬥爭跟主席導師走,大家都躲著她,敬而遠之,因為和她說話要小心,她太革命了,除了文革靠攏黨團組織,沒有別的話題。
我們成年後才明白,她當時十五歲是受了家庭變故父親之死的刺激造成的變態,值得同情。後來她恢復了健康,是一個很有同情心很有求知慾的青年。此同學1968年就自動積極報名去了內蒙古插隊,也經受了很多磨難才回到北京,經過刻苦努力成為一名醫生,現在已經退休。
文革前,我們總是每周要小組開會檢討自己,談論家庭歷史,這是我們學校的傳統,別的中學不搞這一套。我發現同學的爸爸一輩百分之九十都是革命幹部,父母親戚都是共產黨員,好像都上過大學,有的還聞名遐邇,我屬於百分之十的白丁群眾家庭。但數到爺爺那一輩,全班幾乎都沒有什麼無產階級,挖幾代也挖不出最徹底的革命階級貧農階層。最好的是中農,其他都是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居多,才感到多少有些彼此彼此,拉近了距離。
反正大家都很小很幼稚,沒那麼多複雜思維。也是這個大眼睛的女同學,說他爺爺在山東街上走,撿了一塊金條,後來買了土地,成了地主,大家都很惋惜,要是他爺爺學習雷鋒,拾金不眛就好了。但他爸爸在大學入了地下黨,成了幹部,跟黨走,我們都相信了。那時最應該作的事情就是背叛剝削階級家庭和父母,跟黨走上光明大道,可是他父親走著走著就自殺了,都怪這個叫楊獻珍的大人物引導的。這位同學年齡太小,也沒說出什麼所以然來,從一個人人喜歡的小姑娘,經常在一起打桌球的隊友,逐漸變得生疏起來,幾乎陌如路人。
照片中另一個女孩一直很紅,來自高幹家庭,他哥哥和我哥哥是高中同學,在1964年北京男四中爆發學生整人運動時,她的哥哥因為和一般子弟關係較好,還被批評為階級立場不鮮明,受到批評教育。以前他經常在我家玩,也看了很多老照片,幾十年後才從我哥哥口中得知,那時為了入党進步,這位相熟的同學居然想當然地匯報說我外公是國民黨中將,結果謠言不攻自破,可見那個時代的風氣,就連十幾歲的中學生也學會邀功請賞,也會捕風捉影,也會隨時出賣友人。
他的妹妹和我在一個年級,不在一個班上,但住校在一起,不在一間宿舍里,基本沒有接觸,似乎有一道無形防線,我倆誰也沒有提過彼此的哥哥是同校同班同學,還相當熟悉經常互相走動過。我覺得她不是一個鋒芒畢露的兇巴巴女孩,雖然帶著紅袖章,在學校的紅衛兵隊伍中倒很默默無聞低調得很,或許一夜之間也會從幹部子女變成黑幫子弟,這種例子周圍比比皆是,我倒沒有上下起伏榮辱變幻之感,始終如一保持不紅不黑的家庭政治身份。
1964年,北京幾所中學高幹子弟發起整學生的「四清」運動,其實就是紅衛兵運動的前奏。「我們的父輩在馬背上打下了天下,我們不接班誰接,難道讓那些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階級異己分子的子弟通過上大學,騎在我們的頭上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吼聲雄壯,氣吞山河,矛頭直指校長教師,側目蔑視一般子弟,目的就是要整得一批品學兼優卻出身非無產階級的同代人失去上大學資格,不整得這些在學業上比他們優秀,往往得到民國教育出來的教師校長們青睞的好學生低人一等決不罷休。
我哥哥的幾個同班同學在十六七歲的年齡都成了犧牲品。一個縣城裡考來的狀元是地主出身,平素兢兢業業,只能埋頭讀書,從不敢說一句出格的話,還是被挑了出來,作為學校扶植的白專典型,大批特批,整得精神失常,退學回家。另一個父親去了台灣,他是初中畢業保送四中的銀質獎章獲得者,一表人才,謙遜有禮,他喜歡俄國普希金詩歌,模仿著寫了一首眺望大海的自由詩,被批為資產階級和蔣匪敵特子女,盼望蔣介石打回大陸,夢想變天,基本上就定了性,上大學沒門了。
另外在他不慎丟失了的日記本里,他為好朋友十一歲的妹妹寫了一首詩,也被張貼在牆壁上供全校批判,引來圍觀,這還得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流氓品質,道德敗壞,大帽子全來了,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宣判死亡,絕對喪失了上大學資格。後來見到他,瘦削慘白,完全失去花季少年的風采,一兩年後才恢復了往常神態。我並不知道他十六歲時被批得體無完膚的那首小詩是為我而寫的,他是我哥哥朋友之一,我都沒和他說過話。多年後我才知道,怪不得他從此羞於來我家玩,可能也覺得自己犯了彌天大罪。
「在她那無邪的雙眸里,在那銀鈴般的笑聲中,我找到了久已尋求的光……」
多麼清純的男孩子,如此簡樸的思念,在那個一切都被批判的扭曲環境裡,正常的人類思維是無法容身的。一時間這首「為朋友曹小平十一歲妹妹而作」的小詩被張貼在教室里,傳到校園中。幾個帶頭批判熱心階級鬥爭的積極分子,主動提出幫助我哥哥挖掘源頭,改造思想,尋找機會想來我家窺視一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被我哥哥支到其他嚴肅的地方接受他們的幫助。那時我住校,周日才回家,於是我有一次下午特地提前回校,我哥哥乘此就邀請他們全體來家中談思想。我至今記得我哥哥背後的國罵,說這幫傢伙,假模假式的,裝得很革命,其實虛偽透頂,從骨子裡就想高人一頭,從小就想著整人,整的同學都是有才學有外貌的,糊弄他們一下覺得很解氣。
文革前臭名昭著的中學「四清」運動,發生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幾所學校,殃及一般平民子弟的一段歷史,早已載入研究文革前首都中學生極左思潮的文獻中。海內外的學者專家們和當事人都作過研究,以此證實文革中的極左思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潛伏在部分青少年思想中由來已久。帶頭人之一就是宋彬彬(宋要武)的哥哥宋某某(宋任窮之子),邱會作之子邱某某,沈圖之子沈某某,還有很多高幹兒子,這幾人恰好都在我哥哥班上,後來這幾人1965年都考上清華北大。
我哥哥高二時也被他們用莫須有的罪名整了一年之久,但因為成績優秀家庭歷史清楚有體育特長而僥倖在1965年被清華大學錄取,離他們仍然很近。1966年文革開始,他們幾個人又想把在中學整我哥哥的事件重提,說他寫過反動詩篇,並報告給他的班幹部,但清華有眾多一般子弟,從全國考上來,並不全是來自天子腳下金童玉女們的御用學府。他們告訴我哥哥,這批高幹子弟太狂妄了,不要理他們。他們在中學可以興風作浪,在大學名校不得不收斂幾分。
1960年代的名牌大學裡,在不公正地排擠了大部分被標為黑五類賤民階層的子弟後,在有限的機會之下,普通人民的子弟憑著自身的才學和努力,與這些既得利益者也曾平分秋色,各不相關,各走各路,而下面的老三屆就完全不同命運了,一樣被遣上山下鄉,卻和中國當年的自行車一樣,分為「永久牌」的,「飛鴿牌」的,那是另一篇文章故事了。
我哥哥自幼喜歡古典詩詞,雖然是工科出身,退休之年在溫哥華還出版了一千首古典詩詞集。可是當年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卻因為酷愛詩詞,差點斷送前程,而引起這批黨員學生注意和大肆批判的兩首小詩,卻與政治社會毫無關聯。可怕的指責純屬牽強附會,在中學生里搞文字獄,在日記信件文字裡嗅出弦外之音。這是當年風行一時的社會習氣,鷹犬處處。從文革前夜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燕山夜話的大社會環境,就可了解這種風氣對青少年的巨大影響和毒害。
我十七歲上高二的哥哥被批的灰頭土臉的兩首詩如下。
其一:
清明冷雨落千家,
弄殘庭前桃李花。
勸君莫因暫晴走,
村路泥濘石橋滑。
(朋友到家中玩,天降豪雨,臨走時學古人寫詩相贈,時年十六有餘,高一中學生)結果成了瘋狂抵制上山下鄉運動,與社會上口號「光榮一時,受苦一世」遙相呼應,攻擊偉大領袖號召,諷刺邢燕子等人戴上大紅花,結果「受苦一世」。多麼豐富的想像力,多麼強大的邏輯,令人百口難辨呀。
其二:
萬壽山上有危樓,
滿園翠色眼底收。
好笑誰家年少客,
偏愛黃昏帶雨游。
(他和少年宮一批兵乓好友,一同游頤和園,夏日遇雨,煙籠昆明湖水,站在萬壽山佛香閣高處,聊發少年狂,信筆寫來,卻闖大禍,如是成人,必遭滅頂之災。)
危言聳聽,上綱上線,批判他形容社會主義大廈岌岌可危,隨時塌倒,與世界上帝修反同唱喪曲,結合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背景,明明祖國如噴薄而出的紅日,在他筆下卻是黃昏,要在黃昏中迎接反革命暴風雨的到來。
真不知是什麼教育使得這些青少年,不懂文學,沒有情調,整天就是繃著階級鬥爭緊緊的一根弦,瞪著火眼金睛,到處深挖敵人,雞蛋里挑骨頭,偌大中國,到處都是人民的敵人。要是文革發生時這批人還在中學,肯定是紅衛兵打手,急先鋒。血統論絕非一日之寒,文革前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據說幾十年後,邱會作兒子從牢獄中出來後,班上聚會時他對當年他整的很兇的同學鞠躬道歉,他們這些傢伙,害得人家半世挫折,失去深造機會,被指責與黨不同心同德同路,成為不可信任的人。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死黨後,他的兒子自己也成為階下囚,區區幾十年,活活現世報。他能低首道歉,同學們也就一笑泯冤讎,也算是無奈中的現實,還能怎樣?
從海外圖書館偶然發現的舊雜誌里看到1960年代照片引出這一段回憶,我們都是那瘋狂年代的見證人,雖然才小小年齡,已經被風寒侵蝕,體驗風雨交加,這場文革,傷害了多少家庭和個人,它的遺毒何時能真正肅清?

曹小平年輕時照片,風華正茂時還曾是名冠京城的桌球好手。他們跑到北京市少年宮,讓莊正芳教練開除曹小平,說他犯了嚴重錯誤,寫反動詩,就是文中所提的那兩首詩,莊教授培養了世界冠軍莊則棟等少年青年國手,豈能讓這些紅色小將隨意指揮,他還是非常關愛自己的徒弟,難能可貴的長輩。我哥哥和少年宮認識的球友們保持著終生友情。
多年後在朋友家,1980年代曹小平和莊則棟師兄以及其他桌球朋友們聚會,筆者即將移民加拿大,也有幸在座見到莊則棟最後一面。小時候看他來少年宮指導少年運動員時,筆者還是小女孩,聚精會神在台旁看的目不轉睛,他為國爭光,三聯蟬世界冠軍,是我們一代人的英雄,當日《北京晚報》還報導,教練從人群中叫出一位少年曹小平,他起初有些羞澀,誰想揮舞起球拍,猶如小老虎出山。曹小平不僅拿下北京城中學生冠軍桂冠,後來也成為清華大學桌球主力。

前排左四莊則棟、右一曹小平,筆者站在莊則棟身後,我先生蘇阿冠為我們攝於1983年
最近我一邊看這張照片,一邊感嘆寫下感想「人生得意須臾盡,借人博弈上青雲。榮華隕落桂冠去,落魄方知少年誼。」
1964年我剛上中學,積極要求進步,在一所重點學校里被評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三好學生,可是我的哥哥卻在全市最有名的男四中備受煎熬,全家人的生活上空是一片黑雲籠罩,不知還有什麼挖三代成分,查海外關係的下一步,父母祖輩都沒有過硬的背景,而且隨時會被上綱上線胡亂連結上資產階級官僚階級的家庭烙印,還有早已不敢再聯繫也不可能聯繫的海外香港台灣親屬們,也會被挖出來印證他寫詩的反黨反社會的必然性。
1965年初,春寒料峭,我陪著我哥哥在天安門廣場散心,他說恐怕當年高考無望了,進工廠可能都沒機會,班上整他們的小頭頭學生已經暗示他們挨整學生應當學習邢燕子董加耕,到廣闊農村去煉紅心,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工農相結合,那時國家的口號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看來是只有一種準備了,我們都氣憤非常,1964年很多優秀中學生被摒棄在大學校門之外,主要是家庭出身所致。那時北京天津的學生去寧夏,南京上海學生去新疆,怎麼會這樣呢,社會潮流浩蕩,不是我們中小學生能理解的。
幸運的是,北京市委派來的工作組還是具有一定政治水平的,記得有一位女幹部對我哥哥這位驚魂失措的中學生講,你不要有包袱,應該積極準備功課高考,你很有才華,但不要傲氣,要接近那些共青團員,幹部子弟,他們在政治上雖然敏感,有驕嬌二氣,但在政治覺悟上還是比你們一般子弟強的,要相信黨的政策水平。
1965年,曹小平作為男四中挨整學生中唯一考上大學,而且還是最高學府的清華,不能不說是幸運者。他不敢再學文科,畢業後成為大學的理工科教學骨幹,一輩子與文學詩詞再無交集,也就躲過了文字之災,一生基本順利,但還是深深體驗了「早歲哪知世事艱」的文字獄大環境。
曹小平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熱愛終身未忘。19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海外後,近十五年來,重拾舊好,嘔心瀝血,寫出很多古體詩詞,最近出版的這本詩集一千首,《柳上惠詩詞集》在十幾個國家上網出版。
完稿於加拿大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