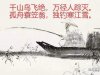十年時間對於世間萬物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改不了青山依舊,變不了綠水長流,但對於人生來說卻是一場巨大的變化,正如窗外紅了櫻桃,頭上也白了青發,如此光陰、如此歲月。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杜牧《遣懷》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十年光景對於杜牧而言不過是場南柯一夢。夢中他應牛僧孺相邀來到揚州任幕僚,見到了二十四橋明月夜,見到了春風十里揚州路,夢外卻是不得志的,他的剛正果直,得不到晚唐一干人等的歡喜,被排擠,被貶謫,故此他不願醒來。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杭州自來便令人津津樂道,但那都是宋朝的事兒了,在唐朝揚州才是唐朝人的嚮往之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揚一益二」都是他們對於揚州至高無上的讚譽。
杜公子風流,在揚州,每日飲酒作樂,喝的是最好的酒,酒香醇厚,入口甘甜;看的是最美的景,三月揚州,煙花瀰漫;攬著的是最美的人,秦樓楚館,纖細腰身,天下之樂,他一人就已享盡。可是如果夢太好了,往往就顯得不是很真實,十年光景,轉瞬即逝,到頭來杜牧自己也記不得這些年他到底做了什麼,終究是一事無成,只落得個青樓薄倖名。其實,杜牧在揚州並未待至十年,但是揚州的種種在他心頭卻始終擱置不了,多情人,多情地,都在揚州。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
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黃庭堅《寄黃幾復》
「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首著名的以作聊表友誼的詩篇從古至今都很令人感動,范曄與陸凱雖相隔千里,一在杏花春雨江南處,一為荒漠秋風塞北天,卻依靠一枝梅跨越山河尋得幾分安慰,總算沒有辜負。可黃庭堅與黃幾復卻不一樣,黃庭堅在這首詩的跋中曾言「幾復在廣州四會,予在德州德平鎮,皆海濱也。」正如他所說的北海南海,當時的他們一個在山東那裡,一個在廣州那邊,山高水長不過如此了,若有書信寄送倒也不至於太過孤寂,哪成想雁兒不願傳遞那薄薄的尺素,它也嫌棄路途遙遠,它也嫌棄地域艱苦,雁亦如此,置人何處?
十年光景這般,曾經兩人那可是在春日溶溶里,欹靠著柔情春風,對著山河表里,嗅著桃李清香,互相飲酒,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十年已逝,走遍江湖,嘗盡人間酸苦,摯友不在身邊,秋雨梧桐夜落時,一豆孤燈,人影幢幢,思念如酒,辛辣入喉。古人的分別可能就是此生不見,如此天南地北,足跡丈量也需數載光陰,且廣州在古代便是嶺南瘴癘地,潮濕悶熱,草蟲繁殖,不適人長期居住,想幾復去此,不知何時歸來。況且他做官清廉,家徒四壁,生活困難,又常多病,十年也未改變什麼,只不過是早先的春風得意變成現如今的青發已白。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李益《喜見外弟又言別》
曾於書中覓得商人重利輕別離之句,生意歸來,往往不識子女,對視陌生,無甚感情。但李益此篇卻令我們知曉另一種別樣分離,再見也仿似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之人,那就是戰亂。唐朝的前期一直在攀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在朝著蓬勃大融合的方向發展,可是安史之亂的介入,卻讓這風平浪靜的水面開始泛起漣漪,無數人在這場戰亂中失去親人,哀鴻遍野,無人關心。古人曾說四喜,其二是他鄉遇故知,但我卻覺得是戰亂遇舊識。李益與表弟自小便因戰亂而分離,十年時光,戰火紛起,難尋家書,自是不知互相消息。再次相逢時,已是十年後,兒時的夥伴早就成人,雖是親屬,也因十年光陰難以辨認。
想當初二子年歲尚小,只知庭院枇杷熟透否,何日可摘取?現如今歷經戰亂磨練,昔日的稚童在時光的推搡下慢慢長大,面容有異,相見竟都不識,得知名字後才憶起曾經無憂歲月,循著顱內印象,相互交談。太陽西昃,影子拉長,林中傳來沉重鐘聲,悠遠,迴蕩於天地間,晚霞漫延,猶如塞外烽煙,紅的似血、黑的似墨,遮擋一襲天地。種種痕跡都在提示二人該分離了,一日如何能夠訴盡十年情,此後表弟踏上巴陵路途,洞庭水波一一風荷,隔著千山萬水,不知何日又能相見。李益見到表弟無疑是喜的,只是可惜以往的稚子一瞬間變成了識盡愁滋味的少年郎了,歲月不待人總是如此。

銀床淅瀝青梧老,屧粉秋蛩掃。
采香行處蹙連錢,拾得翠翹何恨不能言。
迴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
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
——納蘭性德《虞美人·銀床淅瀝青梧老》
人生如飄雨,散去總無情。我曾聽說人的死亡有三步,三步過後,此人一生的所有印記皆空。第一步,生物死亡,呼吸驟停,與世無爭;第二步,社會死亡,入土為安,親人淒悲;第三步,意義死亡,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因為沒有人會記得此人留存於世的所有印記,曾經的春風得意,曾經的笑語晏晏都無人記得。盧氏雖死,奈何納蘭容若一腔愛意始終割據不下,哪怕十年光陰過去依舊記得曾經的相濡以沫、舉案齊眉,故盧氏還存留於世上不算真的死去。但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死者已逝,未亡人猶在,獨居世上,也是種折磨。
秋雨蕭瑟,昔日蔥蘢的梧桐不堪此風霜,漸漸老去,而以往與愛人常常流連之處,早已經蒼苔生起,蟋蟀鳴叫,不辨故人蹤跡,哪怕在此拾起故人遺落的飾品,也無人可分享。我們可以想像到,納蘭容若看見故人的翠翹時,起初該是歡喜的,因為終於找到曾經的回憶,他輕輕拍去上面的綠苔雜草,露出以往光閃之色,翠翹依舊動人,不變當初模樣。然後四顧盼望,無人可言,唯秋風乍起,暗香盈袖,淚布滿那張皺紋生起的臉,順著溝壑流下再不是少年模樣。納蘭若是無情之人,他倒不至於如此,可他天生便是長情之人,守著天明,對盧氏的感情還是如少年時候,愈發灼烈,哪怕十年過去,初見依舊一眼傾心。半世浮萍隨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世事若太好,也無人會珍惜了。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
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
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
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柳宗元《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柳宗元與劉禹錫的人生歷程用紀錄片的方式來看就是無休止的被貶、被貶仍舊貶,為什麼呢?是兩人沒有才華嗎?是兩人沒有情商嗎?都不是,他們兩人只是生錯了時代,因為他們的個性都太直了,在那個宦官當道的社會上,放棄阿諛奉承,不與之同謀合污,卻與一干人等進行「永貞革新」,想要打擊宦官勢力,想要掃清朝廷腐朽黑暗。但是唐玄宗之後,宦官的權力太大,他們已經壓制不了這股邪惡力量,只得被其反噬鞭打,故此革新只進行了一百多天便以失敗的結局告終,柳宗元淌水過山去永州,劉禹錫舟車勞頓赴朗州,兩地在古代都是窮山惡窮鄉僻壤之地,二人離自己的夢想越發遙遠。想當初,二人差不多弱冠之年便進士及第,比那個「十七人中最少年」的白居易還要耀眼,現如今卻因時代不公而成為權力壓迫下的炮灰,柳宗元自己也無可奈何。
十年歸來,終至長安,沒有衣錦還鄉的驕傲,沒有春風得意的疾跑,只有無盡的憔悴以及痛心,永州的時光磨去了他最風華正茂的年歲,老母親不忍永州環境,撒手人寰,柳宗元不堪永州氣候,多病多災。適應了漠北狂沙的男人一時間如何能夠接受南方的潮濕,水不容火亦是此理。接著我也不忍寫下,當他回到長安後,本以為萬事已定,還能從頭來過,等待他的卻是被貶柳州的消息,十年一去如風雨,不留溫情予宗元。不過他沒有下一個十年了,他的身影永遠停留在了嶺外,塞北的漢子再也找不到家了。
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詞「十年世界雖不及變換乾坤,歲月多少平添些許皺紋」,才十年呢,能改變什麼,但是就那一點點十年卻在人身上刻下了難以抹去的痕跡。這十年裡,我們經歷了太多,也看得太多,我們看到了他們思念家鄉、思念親人,遙遠的連近鄉情怯都做不到,因為回不來,吟「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也看到了他們因為戰亂找不到自己的至親骨血,字字泣淚,卻無能為力,述「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還看到了他們因為室邇人遠,妝奩積灰,無處可言,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我們總以為十年很長,哪成想「十年一別流光速」再見已是「白首相逢」。
我們總以為十年改變不了什麼,哪成想「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白雲依舊空悠悠,歲月不再當年初。
我們總以為人生有很多個十年,哪成想「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過去了的春風得意,總會和後面的十年人間不一樣,畢竟積攢過的十年早已邁不開腳去追尋以往的時光了,長安花也等不回孟郊了。
我們不是青山,也不是綠水,我們總會變的,所以杜秋娘的話又來了「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