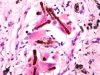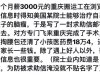導讀:塵肺病是礦工生命健康的一大「殺手」。在中國,礦工多出身於低收入家庭,他們是家庭頂樑柱,一旦患上塵肺,一家人生計無著,更別說承擔孩子的教育支出。塵肺的孩子,就是那些因塵肺病面臨失學的礦工子弟。
詩人陳年喜在確證塵肺病後,走訪記錄了許多因塵肺陷入絕境的家庭。他發現,即使這些家庭貧病交加,仍然在盡全力供養孩子讀書。這些患病礦工們,不希望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
背著制氧機去打工
李書啟有一半肺失去了功能。為了供小兒子念書,他不得不背著制氧機去外地打工。
51歲的李書啟比同齡人顯老一些,頭髮花白,額頭和眼角布滿皺紋。指甲里清不掉的黑泥是十幾年礦工生涯留下的印記,除此之外,還有塵肺病和肺氣腫。
一張2019年的職業病診斷書上寫著:1999年至2015年在河南省靈寶金礦從事打鑽,接觸粉塵。綜合治療,禁忌粉塵作業。
實際上,他從2014年就查出了塵肺,而後又去礦上打了一年雜,直到病情嚴重,才走下礦山。現在,他每走一步呼吸都會變得困難,上完廁所站起來,要喘好一會兒才能動。
在西安,李書啟的工作是給一家卡車停車場看大門,每月1200元工資。雖然賺得不多,好歹是個營生。老闆提供的住處不報銷電費,一度電一塊錢,咳嗽厲害時他才捨得打開制氧機,吸著氧睡覺。
一管止咳噴霧他從不離身,二十多塊錢,別人送的。關鍵時刻能救命。
自打李書啟得了塵肺,家裡的經濟來源就斷了。妻子開始去飯店洗碗,端盤子。26歲的大兒子高中輟學,給一家鍋巴廠送貨,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用李書啟的話說:「文化程度不行,只能靠雙手。」
眼下,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把正在讀高二的小兒子供出來。

圖51歲的李書啟頭髮花白
礦工詩人陳年喜和李書啟同歲,近20年在礦上搏命,他見證了無數悲劇和死亡。有人在爆炸聲中跑成一蓬血霧,有人被飛濺的石塊削成兩半。
因為在礦上寫詩,陳年喜被媒體發掘,出了書,上過央視,還受邀去哈佛大學演講。但這並不是多數礦友能享有的關注。
從2020年開始,他加入塵肺病公益組織「大愛清塵」成為志願者,走訪了許多和李書啟類似的家庭。他僅有的一支筆,要為同病相憐的工友作傳。
如今,陳年喜的兒子正在西安一所專科院校上學。他知道,對於這些塵肺病家庭來說,孩子是支撐他們最後的力量。在新書《活著就是沖天一喊》的《父子書》中,他這樣寫道:
說真的,我一輩子失敗,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
二被塵肺拖垮的家庭
2020年3月23日,陳年喜在一陣劇烈咳嗽中醒來。他對妻子說:「今天無論如何都得去醫院了,不然我得咳死。」
幹了16年爆破工,他一共做過不下10次胸部X光片,都沒問題。命運的無力感從這天才真正來臨。丹鳳縣中醫院,大夫仔細看了看片子,非常肯定:是塵肺!
本以為能逃過一劫的陳年喜,「仿佛五雷轟頂,一下子懵掉了。」
買藥看病是一筆不小的花銷。為了儘快見到現錢,陳年喜從出版社進了一批自己寫的書,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售賣。
他一本一本親自簽名,打包,發快遞,當客服。忙活一年多,賣出來4000多塊錢。作家袁凌勸他,現在正是創作的好時期,別把時間浪費在這種事上,抓緊把新書寫完。
2021年9月2日早晨,陝西商洛市陝州區夜村鎮,陳年喜在貧困戶移民區的樓下見到了李書啟。
幾天裡雨水不斷,多處山路發生坍塌。李書啟回不了白草嶺村,只好暫住在鎮上的親戚家。他的兩個侄女和三個外甥女都住在同一個小區——2016年,政府扶持貧困戶,每人給20平方米的免費面積,她們搬進了鎮上的樓房。
但李書啟並沒有搬遷指標。因為20年前,他老家的房子翻修過一次,看著太新了,沒評上貧困戶。他告訴陳年喜,那年大雨導致山體滑坡,衝下來的石塊砸倒了房牆,不修根本沒法住。

圖李書啟老家的房子
那張職業病證明書讓李書啟拿到了最低檔的低保。一家五口人,一個季度一共能領2800元錢。但遠不夠用來治病。
除了每月買藥的五六百,每隔兩三個月,李書啟都要住一次院。有次住了半個月,花出去16000,去掉低保報銷的部分,自己又拿了7000多。全家長期入不敷出。
李書啟沒法說清在塵肺上花了多少錢,「一邊借一邊還,算不清了」。最多一次,他跟親戚借了5000塊錢,半年才還上。
得病之後,不到逢年過節,家里根本不敢吃肉。除了面需要買,粗糧和菜就自己種。每到深更半夜,70歲肢體殘疾的老父親就會從床上爬起來,一瘸一拐走到莊稼旁,點上篝火,大聲呵退前來拱玉米的野豬。
前陣子,「大愛清塵」有補助,叫李書啟去咸陽的醫院治療,只需交2000塊錢。錢不好湊,他沒去。他覺得塵肺這個東西,「醫院也沒啥效果」。
據統計,截至2019年,中國塵肺病患者高達600萬人,位居職業病榜首。在陳年喜老家陝西丹鳳縣桃坪鎮金灣村,方圓一百里內,光他知道的塵肺病患者,就有七八十人。他們貧困,文化程度低,年輕時為掙錢下礦,不知道什麼是塵肺。
粉塵吸進肺里,滯留在細支氣管和肺泡中,逐漸導致肺部纖維化。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陳年喜見過,有人的肺管最後完全堵住,肺泡炸裂,活活憋死了。
無數家庭就在這樣的過程里,慢慢被拖垮。
三無法掙脫的命運
車進了山區,導航就失靈了。手機屏幕上差兩毫米,往往要多繞出七八公里路。
張秋勇家就住在商洛市山陽縣戶家塬鎮黃龍村,破敗的老房子卡在山坡上。得知陳年喜來探訪,遺孀程玉霞早早站在塌方的路前等著,臉上帶著抱歉和羞澀。
一張藍色「農村低保戶」牌子掛在門框上,給了這個家庭最粗糙的註解。房屋空曠潮濕,只有兩張方桌,一個木櫃,一張裂了口子的布面沙發。
最鮮艷的顏色來自滿牆的獎狀,這是小女兒女張慧馨從小學到初中收穫的榮譽。全年級800多人,她的成績排名前五,常年班級第一。

圖陳年喜走訪張秋勇家
曾經的男主人已經不在,只有摩托車還停在牆角。雖沒人騎,但擦得乾淨。
程玉霞記得丈夫病危的那天。那是2019年3月15號,醫生剛從病房出去,洗了個什麼東西,一回來就看見張秋勇趴在床上,喘不上氣了。他連忙把人抱起來,打了一針,沒見效果,又插了管子——此前張秋勇肺泡破裂,在胸部開了個洞,靠管子連接機器才能吸氧。
狀況依然沒有好轉。醫生對程玉霞說,救不了了,拉回家吧。程玉霞撲通跪在地上:」不行啊,我的孩子還小,一定救救他啊。」隨後,張秋勇被轉到了重症加護病房。
程玉霞打電話告訴大兒子,你爸不行了,快回來吧。當時大兒子正在給書店送書,從沒上過高速的他,一路開著老闆的車,從西安趕到了山陽縣人民醫院。全程158公里。他跪在地上,不斷給父親擦掉臉上的汗珠。汗珠有樹葉那麼大。
小女兒張慧馨也被姑姑從學校接到了醫院,她拉著父親的手,一句話說不出來,只是哭。
第三天,張秋勇醒了。這三天裡,程玉霞一口飯沒吃,一口水沒喝。在重症加護病房住了26天,張秋勇回到了普通病房,妻子和女兒輪班照顧著。遇到咳不出痰,倆人一拍就是三小時。
有時候在病房待久了,程玉霞心裡覺得悶,就跟丈夫說:「你給我放會兒假吧,讓我出去透透風吧。」可剛下樓沒多久,丈夫又打電話讓她回來。形成依賴了。

圖張秋勇住院時期
就像是某種預兆,五月份時,張秋勇不顧醫生勸阻,非要回家看看。妻子把他接回來住了十幾天,又送到了醫院。
2020年1月11號,離過年還有13天,剛過完46歲生日的張秋勇,在醫院裡去世了。
程玉霞說,自2017年丈夫因塵肺病長期住院,受了太多的罪: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下不了地;肺上插著管子,睡覺只能靠著,躺不下;睡十幾分鐘,就憋醒一次;體重從135斤,瘦到了85斤……說著說著,眼眶濕了。
比張秋勇大十歲的親哥哥也是塵肺病患者。九十年代,兄弟倆雙雙輟學進了礦山,打鑽和出渣。「一放炮(爆破)人就得進去,粉塵相當的大。」
哥哥就住在張秋勇家隔壁,一台由「大愛清塵」捐贈的制氧機24小時開著,把他牢牢拴在了床上。家裡全靠嫂子照顧。
兩口子沒有經濟來源,為了治病和生活,他們曾向信用社借了十萬塊錢貸款,利息一萬七。低保補助一發下來,沒等到手就被銀行划走了。
今年,嫂子體檢時查出了宮頸癌,晚期。她沒做任何治療,一見到錢就給丈夫買藥,「他不吃藥馬上就不行。」在哥哥居住的屋子裡,一口棺材被麻袋蓋著。他們已經為可見的未來做了準備。
張秋勇下葬那天,人們打喪鼓,唱孝歌,大兒子幾步一磕頭,小女兒年紀小,默默跟在後面。墳頭就在離家不遠的山坡上,沒有墓碑,也沒有牌樓,只是幾塊石頭壘了個包。旁邊睡著張秋勇的父母。

圖程玉霞和小女兒給張秋勇上墳
住院的幾年,丈夫身邊離不開人,程玉霞沒再出去打工。即便貧窮,她還是給丈夫用最好的藥治療。丈夫去世後,她又回到西安,到處找工地打零工賺錢,供女兒念書。
這是一趟艱難的走訪。陳年喜只能告訴程玉霞:「家裡有孩子,日子就有希望。」
四不敢說出口的希望
張慧馨上初三前一天,程玉霞剛給她交了學費,一學期700多。
要想在縣城上學,必須得在那有房、租房或者工作。這幾樣對程玉霞來說,哪個也不容易。政府扶持搬遷的時候,她們家拿不出1萬的裝修費,房子被收回了。
最後,程玉霞在縣裡找人辦了個工作證明,這才把女兒送進了三中。
之所以是山陽縣三中,而不是教學質量更好的一中和二中,原因很簡單——三中供吃住。至於其他私立學校,想都不用想,學費太貴。
張慧馨皮膚黝黑,戴一副金屬框眼鏡,性格靦腆,聲音細小。在班裡,她兼任物理、政治、歷史課代表。唯獨數學不太好,滿分120,她考90多。身高一米六的她,坐在教室第一排,通常情況,這是班主任對好學生的「特殊照顧」。
班主任是個女老師,教語文,家長會結束,她跟程玉霞這樣評價張慧馨:「這孩子你啥也不用管,有事跟我說就行。」

圖張慧馨
每到周末放假,張慧馨就在姑姑家寄宿。她懂事,主動提做家務,姑姑從來不讓,怕耽誤學習。
對張慧馨管教最嚴的是她的哥哥,「考不好會打我」。因為父親生病,哥哥高二就輟學了。那時候家裡勸他,還有一年畢業,好歹把高中上完。哥哥脾氣倔,說什麼也不念了。
程玉霞知道,別的同學該吃吃,該花花,他連飯都吃不飽,自尊心受不了。
張慧馨對陳年喜說,自己最大的夢想就是考個好大學,以後報答母親和那些幫助過她的人。提到上大學,程玉霞嘆了口氣,「我既想她考上大學,又害怕她考上大學。」畢竟,家裡還有幾萬的外債沒還。
最近剛給孩子交完學費的,還有李書啟。他不想讓下一代和自己走同樣的路。
這也是大多數礦工的想法。當初,他們就是因為文化水平低,才去礦上幹活,一輩子交代給了塵肺。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娃供出來,成了這些礦工餘生最後的任務。
對於礦上的經歷和自己的病情,李書啟從不跟小兒子說,仿佛這樣就能將兩人的命運永遠隔絕開來。
小兒子初中畢業那年,一所高職院校想錄取他,學消防。李書啟說什麼也不同意,「文化程度太淺了,還得考個大學。」他希望小兒子以後能找個「辦公室的工作」。
如今上高二了,除了1600的學雜費,李書啟又給孩子拿了600塊錢,這是他半個月的伙食費和零用錢。周末學校放假,兒子就在李書啟的兩個侄女和三個外甥女家打游擊。
眼下,這是他能給孩子提供的所有。制氧機工作一天,他便也工作一天,能否挨到兒子上大學,也無法多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