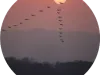題圖當代水墨,作者:@禿頭倔人(李曉強)
程益中與李承鵬交惡,看樣子進入了第二個回合,李撰寫了一篇長文,使用了他那些標誌性的表達技術,狠狠地討伐了程。這些討伐中,有不留情面的嘲弄,也有接近於謾罵的成分。顯然在李承鵬那裡,已將程益中列入他一系列"炮轟"目標清單。
這次交惡的導火線,是程益中對李承鵬言論方式的論斷。儘管程益中後來解釋有"嘲諷"的意思,但他的論斷不僅粗暴,也在某種意義上觸及一位評論人的基本立場。當然,程李交惡不是陡然發生的,兩下怨氣經過日積月累,終於衝破禮節性控制的限度。
自從程益中熔斷其在 大陸與香港的媒體生涯後,他以幾乎無所忌憚的態度發出批判意見。如果了解程益中為人,會發現他20年來的認識框架與言說方式沒有變化。在他的身上,完整保存著報紙黃金時代的價值觀念,那種建立在個人與公權二分法之上的站位。
李承鵬同樣是紙媒黃金年代的產物,他以體育評論建立最初的聲名,而後在那個年代的言論類型中,匯入龔曉躍開拓的體育評論泛時政化的論說方式。在其後來的職業生涯中,體育評論與時事評論在其筆下此消彼長,延續了紙媒時代個人筆陣的知名招牌。
程益中與李承鵬有著即使是他們自己也難以推脫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市場化報紙的弄潮兒,是從前輿論時代走出來的人物。正因為此,他們在共享某個時代身份的同時,卻也有著很大的差異,表現在知識背景、角色、經歷等方面。
儘管二人都可算得上是"報人",但李承鵬更傾向於是一位具體執筆者,是那麼多b報業從業者中微觀的記錄者;而程益中在媒體生涯的主要時期,都作為報紙的操盤手而聞名,是宏觀的感知者與策劃人。身份下的角色差異,導致二位的旨趣不同。
在紙媒時代,甚至是後輿論時代的前期,程李二人旨趣上的差異,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妨礙他們有惺惺相惜之感。但隨著形勢變遷,不僅紙媒時代戛然而止,國內入口網站、社交媒體等以此開啟並形成後輿論時代,兩人在社交空間的旨趣重估在所難免。
程益中"警告"李承鵬的"炮轟"方式,只是一個激發事件,實際上導致兩人交惡的背景原因,是在評價川普上暗結的埋怨。程益中對川普持有全面否定的看法,而李承鵬等人則對川普抱有好感。更要命的是,程益中對這些好評川普的人加以猛烈批評。
在川普選舉落敗前後,可以想見程益中與李承鵬之間的裂痕就已經造成,此間矛盾在兩下或明或暗的表達中不斷激化、擴大。川普敗選、拜登上台已經過相當長的時日,可這種觀點之爭依舊在發酵,終於在如何評價高曉松這個話題上,矛盾公開化。
這是程益中和李承鵬之爭的背景之一,在如何理解這個背景上,還可以多說幾句。兩下對川普的態度差別,都代表一定數量的人,都有代表性。他們並不是在如何解讀國際新聞上產生了分歧,實質上是在如何看待時局及未來上,在方法論上出現牴牾。
歡喜川普的人,並不是真的喜歡這個人,而是寄望於他能以外力的形式給國內帶來變化。所以當程益中不憚以刻薄言語羞辱川普的中國支持者(權且這麼說吧)時,後者在乎的不是觀點不同,而是傷感於他們的絕望未被理解,進而不忿程益中的表達。
在川普一事上重新打量對方,重估友情是否有必要存續,是當時知識分子群體中暗涌的心結與心思。許多像程益中與李承鵬這樣的矛盾面,已經解開曾經綁縛友誼小舟的價值鎖鏈,提起三觀之錨,分道揚鑣,不出惡言,相忘于于江湖已屬難得。
而像程益中與李承鵬這樣,沒有簡潔地互道一聲"傻逼",反而將交惡的終局拉長,當屬少見。因為川普的勝敗對知識群體造成的擾動,一種本應早就發生的割席事件延遲到現在發生,一種暗中疏遠的同儕友誼終於張揚著決裂,這就是程李交惡的核心。
至於李承鵬的輿論策應者所持的陰謀論,所謂程益中要以李承鵬作"投名狀"、"程益中是大外宣"云云,從邏輯和事實上看,都是誇大的不實之詞,只是為了渲染程益中的非正義,而加諸於他的輿論審判。很遺憾,這些論調大大降低了割席事件的倫理含量。
程益中已經解釋了他的"炮轟"說,但在兩人的交惡中,有一個不平衡的地方是:程益中顯然不是長篇論述的愛好者,而李承鵬則更加擅長此道,以致於程益中的簡短解釋與李承鵬的長篇檄文,無法交集交流,只能在兩人各自的支持者那裡獲得反響。
這是程李二人割席交惡的時代背景,觸發點是川普引發國內知識人的分裂,導致在前輿論時代的同路人重估價值觀結盟的歷史,選擇拉黑或警戒對方,來堵塞三觀地圖上出現的裂縫。通過這種切除變質社交關係網的方法,來保證三觀不致於崩解。
除了這一大的背景,程益中與李承鵬的交惡,還涉及對前輿論時代那條言論中心原則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立論選擇。人們驚訝於程益中那樣批評李承鵬,實際上,如果仔細了解程的職業生涯與道德觀點,會發現他不過是重複了一直堅持的道德立場。
程益中始終堅持的一點是,絕對不去評價個人的私德問題。即使是對李承鵬抨擊的、在輿論場中被劃入另冊的左派人士,程益中也不認為需要評判他們的道德。程益中以容易冒犯輿論陣營的堅持,認為道德只是自我要求的荊棘,而不是砸向別人的板磚。
也就是說,在程益中的道德視野中,李承鵬的批評對象不是敵人,只是大時代影響下的個人,雖然表現不如人意,但關鍵是這些人之外的公權力最應成為批評標靶。而在李承鵬那裡,無論是他的寫作習慣,還是雜文化的風格,乃至於其性情,都不接受這樣的說辭。
惡猜公權,善待個人,是程益中的道德原則,但在李承鵬那裡,他選擇個人作為突破口,是惡猜個人。從評論技術上來說,如此選擇,可能是李承鵬的時評模式使然,他的行文屬於雜文一類,"惡猜個人"更容易發揮他嬉笑怒罵的文風。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觀感,就是成熟作者採取最自如的評論文體,在形成他自有的言論風格時,也將在批評對象、批評方式上形成一定的束縛。自然,這些文本上的結構原理,並不妨礙讀者反覆接受這樣的論述模式,反而能塑造言論作者的魅力。
換句話說,程益中之所以那樣"警告",是因為他一以貫之的道德立場,他也認為言論作者應該有這樣的倫理自覺。但對李承鵬來說,這種"警告"已經構成字面上的蔑視與冒犯,他也不可能為了程益中放棄自覺或不自居形成的憤怒風格——這种放棄約等於讓他成為另外一個人。
不像大多數驚詫於程益中"警惕"說的人,通過上述分析,其實能看到不管是程益中還是李承鵬,都沒有變。不存在一個靠求變來收穫"投名狀"的程益中,也不存在一個願意商榷"惡猜個人"原則的李承鵬。二位爺割席憑的是觸之叮噹響的道德分野,沒什麼陰謀陽謀。
到底是惡猜什麼,善待什麼,這是另外一個宏大的話題了。對此,個人有一點理中客的看法。對於在美國的程益中來說,他不必沉浸在日夜湧來的輿論環境中,而李承鵬無法超脫。因為感同身受的程度不同,選擇詞鋒所向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
也或者說,李承鵬之所以選擇惡猜個人,是因為個人與公權不可分割,區分沒有必要沒有意義。而程益中經歷了職業生涯的熔斷,他親身經歷的那些歲月,養成他無法磨蝕的價值觀的底色,即使形勢變化,也願意始終堅持,哪怕要發出孤憤的嘲弄。
這就是對程益中與李承鵬交惡一事的理解。從效果上說,本次割席事件為程益中的公共形象首次公開抹上了一層負面評價。想必他不會在乎這一點。相應地,李承鵬對程益中施加了相當程度的懲罰,而他的尊嚴會否因此有損失,也還有不確定之處。
若說最私人的感受,是在討伐程益中的短暫狂歡中,激憤折衝孤憤:割席當事人的過去並未被清楚地了解,更未被公道地評價,一旦憑價值觀支撐的膚淺社交關係破裂,標籤化的污名操作就難以避免。即使這種操作是為捍衛清譽之人,也還是不妥當。